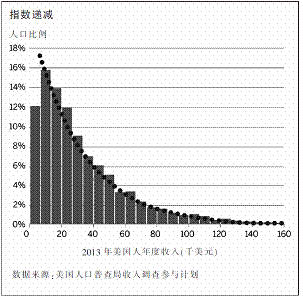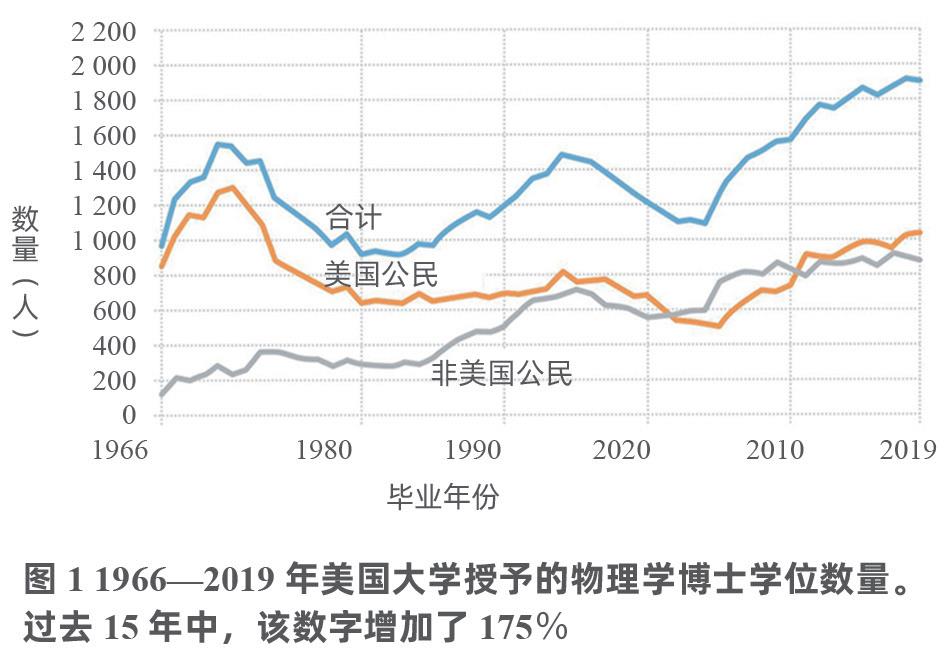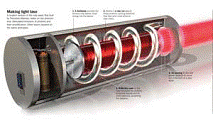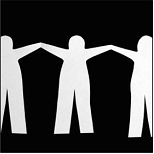我按照预定计划,将进行一次强制性配对转移。
命令中说:尽快办妥,她已经被给予足够的警告。
“是当宿主还是跟班?”公共身躯商店的接待员一边好奇地问道,一边抽出一张空白的入住表格。
“他们告诉我,是当跟班。”我嘟囔道,“但我记得以前是叫 ‘宿主还是寄生体’才对吧?”
“以前是那样。”她证实道,对这套过时的术语略感恼怒,“我们收到了塔楼那边的投诉。”
“老天不容。”我摆出面无表情的脸庞,心里知道那些老家伙多么喜欢他们的漂亮话。漂亮的话语掩藏了各种各样的罪恶。
接待员伸出手来取命令文件,我顺从地——现在不是反抗的时候——举起被手铐锁在一起的双手,使得金属链条彼此碰撞,叮当作响。
响声吸引了接待员的注意,她更加仔细地看了我一眼。她认出我的身份,眼睛睁得大大的。是钦佩吗?但说起来,她留给我的印象并不像个革命者——穿着过时的羊毛衫,眼角好些皱纹,头发灰白,一对眼睛从眼镜上方打量着外界。她是典型的中年妇女模样,已过韶华之年。这年头,我们所有人不都是这样?
“你是那个他们以毁坏财物罪名送入监狱的人。”
毁坏财物罪,刺杀未遂……
女接待员若有所思地说道:“让我吃惊的是,他们竟然给你第二次机会。”
“实际上是第五次机会。”我纠正了她,“但我是首批童子中的一员,他们出于内疚而没有对我一了百了地处以死刑。”
“啊哈,”她的眼睛里透出一丝同情,“我一直好奇他们怎么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
“活得如鱼得水。”我揶揄道。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一些画面,那些肤色晒成完美古铜色、体格健美的年轻身躯懒洋洋地躺在塔楼上粼粼的泳池四周,宛如欢度节日的希腊众神,畅饮着一罐罐的石榴玛格丽塔鸡尾酒,享受窃取的永生。
相比之下,我的双手有着深深的皱纹,布满老人斑。我说话时声音哆嗦。过去30年里,我所栖身的躯壳全都在中年以上。30年前,我还是个8岁小孩,依然有着海藻一般翠绿的眼眸,而不是眼下这对冰蓝色的眼睛……
回首30年前,地球人满为患,濒临崩溃。星球上有太多的人,却无处可去。人类只剩下两个选择——对人类进行大清洗,或者配对转移。没人喜欢第一个选择。
万人冢的观感可不好。
执政者决定,将最年长的那批人的意识灌入到最年轻的身躯里,好比占据一个乘客座位,那么做最公平,年轻人依然会做出所有决定,有机会度过完整的人生,但长者们会继续人生,作为“跟班”(或者说是寄生体)享受第二趟人生。
而这些全都是骗人的鬼话……
我记得总统女士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冰蓝色的眼眸中渗出酷似眼泪的液体,珍重地告诉全世界:“……随着老人们后退一步,成为我们下一代的良心之声,这对年轻人和老人来说,是一个相互学习的机会……”
十足的漂亮话。她的讲话中充满了高尚的牺牲以及人类种族的韧性。
我那时太过年幼,大多数事情都没明白,甚至当那些人将我从父母亲身边拖走,领着我走进一条散发漂白水气味的通道,我也没醒悟过来。护士告诉我,我的身躯很快会容纳总统女士卓越的头脑,我被选中承担这光荣任务是何等幸运!但是,当我事后醒转时,我举起的双手不再是我自己的双手。我看着那个曾经是我的小女孩从房间对面的椅子里蹦下来,向个头足足是她三倍大的军人厉声下令:“带她下楼,带下一个进来。总理正等着呢。”
我那时八岁。我并不愚蠢。他们压根不是在配对转移!明明就是在交换躯壳。用我的身体交换了她的身体。
“别担心,小家伙,”总统女士说道,用我的双眼看着我,以我的声音讲道,“我确信你很快就能和某个更年轻的人配对。”
漂亮的谎言。这些老家伙窃取合适的身体之后,统统归隐到塔楼里,囤积大量资源,抛下剩余的人类成员——等待他们的只有暴乱、饥馑和定量配给的一点儿口粮。
老家伙们在塔楼里依然过得好好的,发号施令,只要他们窃取的身体开始磨损变旧,他们就将老迈的身体换成新的身躯。他们不再掩藏真正的企图。剩下的人类之中,只有极少数人还有反抗的意志。
这天早上,他们在花园里抓住我之后,总统女士轻拍我皱纹密布的面颊,用18岁少女的柔顺嗓音轻轻说道(这是她最近窃取的躯壳):“小家伙,我们打算永远活下去。”然后,她命令卫兵将我拖走。
“他们想让我将你的意识灌入一具至少有90岁的躯壳里,”女接待员阅读命令的内文,几乎是用道歉的语气,“……最好是久病缠身。”
“真让人吃惊。”我答道。
显然,这一点也不让我吃惊。但接下来发生的事肯定就……出人意料了。
“我想,这具身躯也许更加合适,你认为呢?”女接待员朝我眨眨眼,将一份文件转向我这边,“是最近从塔楼里替换下来的躯壳。”
呃,现在不一样了。也许这个衣着过时、戴眼镜的女接待员终究还是倾向于闹革命。
文件上列出潜在配对转移对象的年龄为38岁。仍然这么年轻!但是以塔楼的标准来说,已经又老又旧了。这具躯壳看起来十分眼熟,有着一对海藻般翠绿的眼眸。
“哦,好的,请吧。”我嘟囔着,突然感觉自己受到众神的庇佑,真讽刺啊。当然,我得要说服眼下栖身在我的旧日身体里的那个人,让他或她加入我舍生取义的任务,但我自信地认为,对方会加入的。
没人轻易忘怀自己被窃取的身体。我在30年后仍然心怀怨恨。只有等到我向几个想要永生的老家伙们表明,永生是条死胡同后,我的怨恨才会得到满足。
关键词是“死”。
拿回我自己的面庞会挺好的。尤其是一张长久以来被塔楼内被大家熟知为“总统女士”、受人爱戴的面庞,这张脸庞也许能骗过一些老家伙——那些在泳池边痛饮石榴玛格丽塔鸡尾酒,喝得醉醺醺的老家伙——让他们放我从后门进去。
人类的韧性和复仇的韧性相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资料来源 Nature
——————
本文作者格蕾琴·特斯默(Gretchen Tessmer)是一位律师,也是一位作家,生活在纽约州北部圣罗伦斯县的小镇加弗努尔。本篇是继《被吞入黑洞的飞船》《逃离星球》等作品之后,她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的第五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