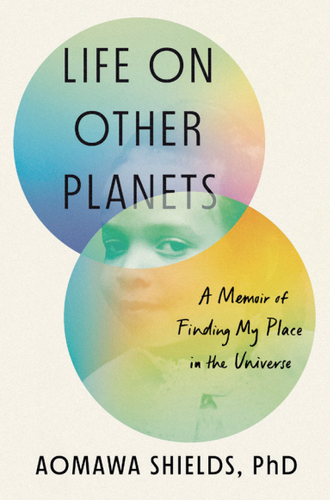奥玛瓦 · 谢尔兹(Aomawa Shields)在《其他星球的生命》(Life on Other Planets)一书中讲述她身为一位接受过古典训练的演员和少数几位从事天文学工作的黑人女性搜寻宜居系外行星的故事。
《其他星球的生命》,奥玛瓦·谢尔兹著,2023年7月出版
20世纪90年代,奥玛瓦 · 谢尔兹短暂离开天文学界去剧院开启一段崭新职业生涯之时,还没有人知道太阳系之外是否存在行星。等到她11年后重回学术圈时,人类已经发现了上千颗系外行星。如今,望远镜和各种探测手段日新月异、飞速前进,我们发现的系外行星数量已经接近6 000。
谢尔兹现在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的天体生物学家,运用计算机模型研究那些遥远的世界,估算它们的气候,评估它们的环境是否适宜外星生命生存并发展。在第二段学术生涯期间,谢尔兹39岁时完成了博士学业,且之后生了一个女儿。谢尔兹被提名为2015年TED研究员,获得过美国宇航局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颁发的多项资助和荣誉,她还是“冉冉升起的观星女孩”项目的创始人和总负责人,这个项目旨在鼓励各种肤色的女孩通过剧作、写作、视觉艺术等形式认识宇宙。
谢尔兹在她近期发售的新书《其他星球的生命》中探讨了她的科研工作、她作为少数几位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的黑人女性之一的亲身经历以及她身为一位接受过古典训练的演员的感受。另外,她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拿到了视觉艺术的学位。
谢尔兹身上有体现宗教精神的一面,而这是许多科学家避而不谈的。她在全书中旁征博引地分享了她对人类为什么要寻找外星生命这个问题的看法。她写道:“在知晓有其他生命形式与人类一同分享这个宇宙之前,我不认为我会真的接受或是理解宇宙的浩瀚。一旦知道了这点,天空就不再是一个雪球,而是一扇窗户。我在夜晚凝望的星系、宇宙,也在回望着我。”
本文是《连线》与谢尔兹之间的一次正式访谈。
为什么你觉得搜寻宇宙中的其他生命很重要?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从那时起,我的脑海里就始终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那里有什么?”于是,等到我回到天文科研界后,就决定要拿到天体生物学博士学位,进而探索其他宇宙生命究竟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行星是搜寻这类宇宙生命的最佳候选者。
我现在从事这项研究的具体方式是借助计算机模型。一旦发现了新系外行星,我就会着手研究它们的宜居性究竟有多高——因为我们对这些地球大小的系外行星确实知之甚少。在计算机模型中,我们可以输入已经掌握的目标行星环境信息,且可以通过计算机自动填补空白。没错,我们不知道它的大气究竟是什么样子,但什么样的大气可以让它的表面支持液态水的长期存在?什么样的表面——在和母恒星的光发生相互作用时——会产生温暖到足以维持液态水但又不会过热到把水蒸发到空间中的气候?
根据上述问题,我们先划定所有大气和表面条件(甚至还有轨道情况)符合要求的备选行星范围。然后再在这个范围中认证那些看上去最为宜居的。这些行星就是我们希望下一代望远镜对准、跟踪、寻找生命迹象的目标。
如果我们发现了一颗与地球类似的系外行星,那么我们能不能分辨它是否宜居——甚至已经有生命居住?
这个任务很棘手,因为我们首先得确定要在目标行星大气中寻找哪些信号。我们把这些信号称为生物标记,也即表征生物对行星大气或表面产生了全球性影响的迹象。一旦我们在地球上远远地观测到了这些生物标记,我们就明确地知道目标行星上有生命存在。
生物标记可不只是氧。虽然我们知道地球上的许多生命都需要氧,但并非所有生命都需要。另外,火山活动等非生物过程也可以产生氧。二氧化碳进入大气被阳光分解后也会产生氧气。因此,如果目标行星大气中有很多氧,而我们又把氧作为判定存在生命的唯一标准,那就可能会出现假阳性。
因此,我们思忖的生物标记是一整套与生命相关的大气气体,甚至可能还会把星球表面的情况囊括进来。如果我们能在星球表面找到液体发出的闪光——用酷炫一点的词来说就是“镜面反射”——就知道目标星球上存在液体。不过,这种液体并不一定就是水。土星卫星泰坦就是一个例子。“卡西尼”探测器的确探测到泰坦上有液体闪光,但这种闪光来自由液态甲烷和乙烷构成的湖泊。
其他行星的气候和天气可以受到诸多因素影响。我们现在使用的模型原本是根据历史记录预测地球气候和天气的,具体来说就是预测22世纪的地球气候变化效应。现在,我们用这些模型预测系外行星的气候。我们改变了母恒星,改变了大气条件,改变了行星表面状况,然后再基于我们已经掌握的目标行星信息预测它们的气候究竟会是什么样。
我们认为,宜居系外行星的大气不应该太厚,否则就会变成类似金星那样的星球,强烈的温室效应炙烤整个世界。不过,大气也不应该太薄,否则就无法支持星球表面维持液态水,也就是变成类似火星那样的星球——由于大气太过稀薄,如今的火星表面没有任何液态水流动。
像地球这样的大气就恰到好处,但也和行星与母恒星的距离以及母恒星的种类有关,因为恒星会发出各种波长的光,而银河系中大部分恒星其实都与我们的太阳不一样。大部分恒星都温度较低、体积较小、偏红色。相比太阳发出的可见光,这类恒星发出的近红外光与大气气体和水冰发生相互作用的方式可以完全不同,而这种相互作用又可以影响行星气候。
你觉得什么时候你和你的天体生物学家同行最终会说出:“我们认为这颗行星有百分之X的概率宜居?”
我们早晚会说这样的话。我对此很有信心。其实只要找到一颗我们能够发现并且计算其大小的行星就可以了。尤其是开普勒望远镜的继任者凌星系外行星勘测卫星(TESS)发现的那种离我们不远的行星。这颗巡查全天空的卫星搜寻的目标是正好从其母恒星面前经过的行星,此时,在卫星“看”来,母恒星因为受到行星的遮挡会变暗一些。如果目标系外行星小到和地球差不多,那它就更有可能是一颗岩石行星,因而更有可能拥有可供生物“站立”且容纳海洋的表面。
目标行星离我们越近,就越有可能被像詹姆斯 · 韦布空间望远镜这样的设备追踪到——当然,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还有大型紫外线和红外线勘探器(LUVOIR)及宜居系外行星成像天文台(HabEx)这样的下一代空间望远镜。如果其中有一个项目最后成真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些系外行星的宜居性有更精准的百分比估测了。
假设你或者其他天文学家最终发现了一颗看上去不仅宜居而且确实有生命居住的系外星球,人类知晓了这样的发现会有什么想法?
那简直不可思议,那种震撼将是压倒一切的。当然,如果我本人参与了发现过程,肯定会更加高兴。
我的研究对象是系外行星,所以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思考我们自身所在的太阳系的情况。要知道,我们完全有可能最后在自家花园里发现生命。虽然谁都不敢打保票,但可能性的确存在:土星的卫星恩克拉多斯、木星的卫星欧罗巴都有可能栖息着生命。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些太阳系行星卫星的了解肯定要比系外行星卫星多得多。我们最后发现地外生命的地点既可能是系外行星,也可能是自家后花园。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有朝一日前往欧罗巴,钻穿它表面的冰层,然后拽上来一些那颗星球的微生物。到了那时,我们就会确定生命有多种起源方式。无论再接下去要做什么,这种认知都会极大程度改变人类历史。
你是怎么做到同时对演艺和天文学感兴趣的?
一开始,我认为这两者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说很难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天文学是我的初恋,我很享受抬头仰望星空、畅想宙中有什么的感觉。后来,我在上高中的时候被拉去参加《钢铁茉莉》(Steel Magnolias)的试镜,而且最后被选中了。后来就开始参演更多作品,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意识到原来演艺和天文学这两件事都可以让我很享受。
这两者是不是就像你自己的两面一样,或者说它们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从某些方面来说,演艺和天文学确实像是我自己的两面。我热爱扮演不同角色,热爱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感。而且,我最早无法在科学领域找到满足这种热爱的方法。而现在,我意识到它们其实真的互相联系。我对研究对象的感受会直接决定我是否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它的研究中去。我想我是在修研究生课程、必须选择一个论文课题时意识到这点的:这个课题必须是让我觉得有所联系的。我发现演艺也是这样,饰演的角色在故事中表现出的感受和情感与他们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直接相关,与我个人的情感直接相关,与我开展研究的方式以及科学发现的方式直接相关。
是什么促使你撰写了《其他星球的生命》这部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同时拥有天文学和演艺这两种爱好实在是太奇怪了。”而且,当我告诉别人我的这两种爱好时,总会得到像“哇,你是怎么做到的”“那好像很奇怪哎”这样的回答。于是,我把这个问题记在了心里。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努力解决内心感受到的冲突:我应该选这个,我应该选那个,而不是同时爱上这两者。后来,我意识到只要不再思考这个问题,不再强迫自己做这样的抉择,把这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爱好结合到一起的可能性就自动出现了。于是,我写下了这本书。我发现,演艺与天文学并不互相排斥,实际上还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同时爱上它们,让我变成了一个更优秀的专业人士、更优秀的科学家、更优秀的演员。从那时起,神奇的事情便发生了。
在最近几年里,我发现像我这样的人并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稀有。许多人都和我一样,同时对科学和艺术领域感兴趣,并且对如何把两者结合在一起相当茫然。因此,我这本书的一大读者群体就是那些不只拥有一个终生爱好(或许也不止两个)并且不确定如何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人。如果你因为个人、经济、物质保障方面的原因觉得现在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或职业生涯为时已晚,那就应该看看我这本书。作为一个在年纪较大时重归学业的过来人,我之前也曾经想过:“现在才去读博士实在太晚了,毕业时都要40岁了。”但后来我就意识到——幸好意识到了——无论怎么样我都会步入40岁的,因此,如果我真的想要拿到博士学位,最好还是大胆去做吧。
另外,主要在白人世界中工作、生活的有色群体,也是我这本书的重要受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即便身处白人世界,我们也有很多方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和奋斗路径,进而成为自己的榜样。
即便现在已经是2023年了,美国的天文学圈子里白人仍旧占到了绝大多数,至于有色女性在这个领域内就更是凤毛麟角了。你能否谈谈是怎么在书中阐述自己作为一名黑人女性在天文学研究领域内的从业经历的?
毫无疑问,在这个圈子里,我轻易就能感受到自己与大家的不同,因为在很多方面的确就是这样。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我是一个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圈子中的黑人女性;二,我是一个在年纪较大时才回归学业的学生;三,我还是个受过古典训练的演员。因此,我身上肯定具有冒充者综合征的所有要素。正是这个寻找少数社群——不只是黑人社群,而且还是囊括了所有有色人种的少数社群——并在多数社群中积极寻找同伴的过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价值。我可以不是受系统问题影响的受害者,反而可以成为变革的推动者。单单是我存在于这个圈子内,这本身就会对这个行业产生影响,埋下变革的种子。
另外,这也让我能够以在其他圈子中实现不了的方式更好地照顾自己。身为白人占绝大多数的圈子中的有色人种女性,业内会请我们做很多事情,邀请我们加入各种委员会,让我们成为行业多元化的一种象征。无论如何,这都激发了我的责任感:为了下一代,为了以后从事这个行当的千千万万有色人种女性,我必须扛起这一切,成为大家期待的榜样。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明白,只要照顾好自己——无论是身体上、精神上,还是情感上——让自己在这个领域内过得好好的,这本身就是变革。因此,我可以大胆去做那些有利于我成为榜样的事,力争在这个领域内待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对行业本身产生更多变革性影响。如果我过度牺牲,以至于什么都剩不下,反而会损害整个大环境,损害我希望积极改变的行业现状。因此,我也需要在付出与过度牺牲之间做到平衡。
从你个人的经历来看,在你的职业生涯中,黑人女性——或者,更广泛地说,所有有色人种——在这个领域内的境况是否发生了很大变化?
不同肤色群体的统计数据不同。在物理学和天文学界,我们看到拉丁裔女性从业人员数量上升的幅度远高于非洲裔美国女性。很遗憾,非洲裔美国女性从事物理学和天文学研究的人数与20世纪90年代初相比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变化。
而且,这还只是学士学位的状况。到了博士阶段,这个数字还要更低。杰米 · 瓦伦丁(Jami Valentine)等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创办了一个网站,我是那个网站建立以来注册的26位获得天文学相关学科博士学位的黑人女性之一。所以,确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不过,最近几年,尤其是自“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以新形式开展以来,我清楚地看到,我们这些少数群体获得了比之前更多的支持。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叫作“黑人在天文学”的组织,在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创建了社群,在美国天文学会、美国物理学会也有组织和项目。我们获得了诸多国家组织、专业组织的支持、授权,他们投入了大量资源支持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社群积极投身天文学事业。线上的支持就更多了。1997年,我第一次攻读博士学位时很多项目还不存在,而现在都有了。因此,我绝对相信,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投身到天文学研究领域中来。
资料来源 Wired
——————
本文作者拉明·斯基巴(Ramin Skibba)是《连线》(Wired)杂志太空栏目的作者。他的报道涵盖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空间科学家、空间环境保护运动、空间政治、空间冲突、太空产业以及火箭发射、再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