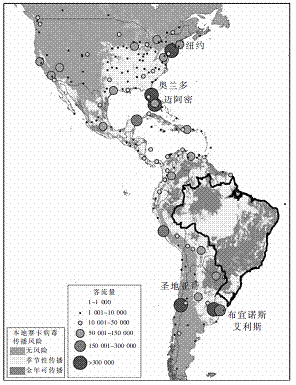寨卡病毒肆虐之时,很少有人讨论全球新发传染病增加背后的问题。

2015年,巴西的医务工作者注意到寨卡病毒感染病例数有所升高,原以为只是轻微升高,9个月后却遭遇了新生婴儿小头畸形症惊人的增长,而小头畸形症正是大脑发育异常的结果。上图为巴西累西腓市一家医院中,丹尼尔·克鲁兹(Danielle Cruz)医师对鲁汉德拉――一名两月大的小头畸形症新生婴儿――进行检查。累西腓市是有着最多脑神经失调症病历记录的城市
大多数流行病都是悄然蔓延起来的。从2015年开始,巴西的医务工作者就注意到一种相对温和且无显著特征的感染病例数有所升高,该感染疑似由寨卡病毒通过蚊子传播引起。2015年5月7日,泛美健康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颁布了一项流行病学警报,该警报平静地陈述道:“目前,巴西公共卫生部门正在该国东北部调查寨卡病毒可能的传播途径。”此次疫情似乎只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新发传染病之战中的又一场小冲突而已。
然而,到了2015年秋季,科学家开始意识到寨卡病毒不仅仅是一场小打小闹的流行病。此次病毒疫情有着潜在的可怕后果,因为出生时有着异常小脑袋的孩子突然以惊人的频率出现在巴西东北部,差不多正好是寨卡病毒感染发生率出现飙升的报道后的38周。在巴西巴伊亚州,在妊娠早期感染上寨卡病毒的女性生出小头畸形症患儿的概率从0.02%上升到了0.88%~13.2%之间。
截至笔者撰文之时,美洲已经报道了超过406 755例寨卡病毒感染疑似病例,其中56 685例已经确诊。作为众人熟知的登革热、黄热病和西尼罗热病毒的“表亲”,寨卡病毒一直被忽略和无视,直到最近突然变得令人异常瞩目。随着疾病的不断蔓延,许多惊慌失措的父母开始为患有严重神经损伤类疾病的新生儿担心。
寨卡病毒的确值得关注。这不仅是因为这种疾病让人类付出高昂代价,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甚至是终生代价;而且这次疫情暴发揭示了人类与传染性病原体不断斗争中新的弱点与优势。与此同时,此次疫情暴发也强化了我们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的重要性。当人们日益对全球化缺乏信任,跨国合作被描绘成有损国家利益的时刻,此次疫情提醒我们,大家其实是同舟共济的。这次寨卡疫情的暴发本身十分重要,但它同时也是时而隐藏的更大模式的一部分。越来越频繁的全球疾病大暴发需要共同应对。比起在接踵而至的危机中蹒跚前行、关闭边境、指责移民,我们更需要持续支持对传染性疾病进行监控和应对的国际社会和机构。
为何聚焦寨卡病毒?
自从1947年发现了寨卡病毒以来,寨卡病毒只是偶尔在非洲(或其他地方)被检测到,1981年之前仅有不足20例感染病例的报道。实际的感染病例数肯定更高一些,但是,仅会引发轻度和非常普通临床症状的病毒的确很容易被忽视,其感染病例数也容易被低估。对非洲的部分人群进行的更详细和专注的调查发现,个体采样中有38%的人体内有寨卡病毒抗体,这表明广泛存在着未确诊或无症状的接触者。
病毒迅速蔓延,而我们(病毒的宿主)却毫无知觉。这种状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得到了改善。2007年,雅浦的小密克罗尼西亚群岛上报道了108例寨卡病毒感染病例,73%的3周岁以上岛内居民均接触到病毒。2013年,病毒席卷了法属波利尼西亚,多达32 000人被感染。一年以后,一名好像是从太平洋岛屿去往巴西的游客成为病毒的“不知情”携带者,该病毒从未在美洲出现过。
此次疫情仍处于初期阶段,疫情尚未达到顶峰。病毒已经从巴西东北的爆发中心向远处蔓延,向南席卷了其他南美洲国家,向北侵袭了美国。2015年以来,已有47个国家首次报道了寨卡病毒的传播。这次事件的严重性需要合理的解释:本次事件有何不同之处?是什么因素导致这样一种名不见经传的病毒变成了全球大敌?
答案并非十分明确。流行病学有三要素――宿主、传染源和传染途径――三者均处于运动状态。在过去的20年中,人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自身重塑成了适宜传染病传播的状态。全球人口持续以每年超过1.1%的速率增长,扩大了易感人群的数量。现今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中,增加了任何传染病的传播概率。平均算来,每天有超过800万人在飞行,更多人处于运动状态,使潜在病原体在全球各地迅速传播。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为有利的传染病传播条件。迄今为止,美国有934例寨卡病毒感染疑似病例均可直接追溯到从感染高发国家来的旅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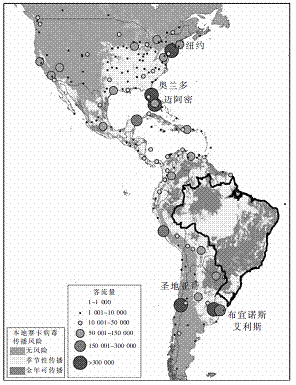
病原载体和宿主协同扩散为新的传染病创造了理想条件。这张地图显示了巴西――当前寨卡病毒疫情中心地带――以外人类运动带来的联合效应以及病毒的蚊媒传播范围。其结果显示,美洲南部、中部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目前均有着寨卡病毒季节性或全年性传播的潜在风险
然而这样的流行趋势并不新奇,也不是寨卡病毒所特有的。虽然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旅行的确――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不断增长的新发传染病病例,但是仅靠这些变化因素本身仍无法解释清楚这次的疫情。寨卡病毒本身也因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而迅速进化。与其他病毒把自己的遗传信息以RNA形式储存起来一样,寨卡病毒不断改变自己的“名片”。在这些RNA病毒中,负责将遗传信息进行复制和传递的机制非常不明确。
我们尚无法精确找出病毒基因组确切的变化位点,正是这种变化使得20世纪50年代相对温和的寨卡病毒变成了21世纪初感染能力较强的寨卡病毒。自从该病毒被发现以来,历经数千代的变化,这种病毒提升了自己的能力,它们利用细胞表面一种丰富存在的受体,可以直接定位于神经干细胞(即胎儿大脑的祖细胞),继而进入细胞内部控制细胞的生理技能。寨卡病毒还进化出了将自己隐蔽在母源抗体中,以便在孕期穿过胎盘屏障的能力。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编码在寨卡病毒基因组中的哪些确切信息使得病毒的诡计得逞,但是一系列基因突变还是能解答一部分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寨卡病毒可以通过性传播方式进行传播的可能性已成为焦点。这种途径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间接的。少数寨卡病毒感染病例的个体并未在病毒和其蚊媒所在地生活过或旅行过,这就只能解释为他们与近期去寨卡病毒流行地区旅行过的人有过性接触。
然而,并未在被感染者的精液中发现有效浓度的活性寨卡病毒。这种病毒利用了男性生殖系统的特殊状态,在这里免疫监视作用被弱化以确保精子细胞能够生存。聚集在这样的保护区中的病毒可能进化出了新的传播途径,在该过程中病毒摆脱了对蚊媒的依赖。承认这种新型传播途径的重要性为时尚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病原体,尤其是病毒,已经把他们的命运与持久而广泛的性交传播无缝结合,令人毛骨悚然。
传播载体
然而,当前寨卡病毒的大流行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其惊人的进化速度。作为流行病传播三要素中的最后一员,蚊子对寨卡病毒的流行居功至伟。蚊子是传染病的丛林飞行员,它们将形形色色的病原体从一个宿主投放到另一个宿主。然而蚊子似乎并没有从这一肮脏的工作中获得多少进化收益:病原体只需简单进化,就能搭乘蚊子这个有效的传播途径。蚊子并不知道从宿主体内吸食的血液,正是血源性病原体短暂但不可或缺的藏身之所。蚊子日常进食过程中不经意摄入的寨卡病毒,在接下来的10天内从它们的肠道转移到循环系统,并最终迁移到唾液腺,一旦它们再次叮咬新的宿主,病原体即被注射到宿主体内得以传播。
埃及伊蚊(Aedes aegypti)和白纹伊蚊(Aedes albopictus)这两个入侵物种似乎是寨卡病毒在美洲蔓延的罪魁祸首。它们在生态习性上各有差异,埃及伊蚊属于昼出夜伏型的户外进食者,喜欢跋涉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冒险。相较而言,白纹伊蚊在室内觅食,主要在早晨和夜间活动。两者在行为学上正好互补,充分利用人类起居习惯提供的机会,可以在我们日间的室内外活动时间里进行全天候无缝攻击。另外,这些蚊子也是极其讲究的食客:它们只喜欢浅尝辄止,不喜欢暴饮暴食,它们吸食众多宿主,而且每次只从宿主体内啜一小口血液。正是这样蜻蜓点水般的“少吃多餐”促进了病毒在众多宿主之间传播。
寨卡病毒利用其病原载体的生态特征得以大肆传播。然而,最应该令人恐慌的也许是两种蚊子的生活领域正在迅速扩大。在日益加剧的城市化、落后的卫生条件和气候变化的驱动下,蚊子的生存范围也在发生变化。15世纪以前,埃及伊蚊只生活在西非,近年却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赤道附近的热带;而现在,它们的阵地已延伸到北至弗吉尼亚区域。与之类似,在过去的75年中,白纹伊蚊也从其原产地南亚次大陆扩散到从巴塔哥尼亚到马萨诸塞州的新疆域。与之相伴随的正是寨卡病毒的大扩散。在美国,寨卡病毒的感染已经在过去几个月里从可能变为了现实。为了应对寨卡病毒的流行,人们正集中力量消灭感染区域和高危区域的蚊子。
尽管常规的灭蚊方法,诸如排干死水和使用杀虫剂,已被证明在减少蚊子数量上行之有效;但是想要通过这些手段完全消灭蚊子似乎不切实际。两类蚊子都适应了人类生活所提供的各种机会,它们可以把卵产到极其微小的水洼里。有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正试图使用最新的遗传技术消灭蚊子,该计划拟通过基因改造使蚊子具有自身破坏力,或让它们感染上沃尔巴克氏体属(Wolbachia)细菌,该细菌可以阻止寨卡病毒感染蚊子。另一方面,针对寨卡病毒的疫苗已经开发出来,现在正进行相关临床试验。总之,这些技术手段和医学突破将有助于人们在这场战斗中重新获得优势,但这些新技术距离实际应用尚需时日。可以预见,人类的群体免疫和聪明才智终将击退病毒,并送它们重回其野生宿主。然而,即便如此,人类仍应该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感染保持警惕。
高风险流行病
我们为何未能看到这次疫情的到来?过去的几十年其他流行病的暴发也是如此。毕竟,造成最近疫情的大部分传染源已经知道。流行病的基本因素――人口密度、贫穷、全球化――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关注并得到深入研究,越来越为人们所了解。尽管如此,我们似乎无法预测其发生,我们的应对措施也显得迟缓。难道我们遗漏了什么关键因素吗?
流行病学是一门高风险科学,上述问题也许可以部分归因于此。所有科学家得到的教育是:谨慎解读数据,仔细进行推理,小心结论快过证据。这些做法是科学成功的基础,这需要耐心、支持和时间。然而,公共卫生当局在应对疫情的时候,不会有耐心等到所有事实;反之,他们必须在不成熟的过早行动和过分谨慎的迟缓行动之间权衡利弊。反应太迅速,会造成大量资源的无益消耗;反应太迟钝,将导致本可避免的感染和死亡得不到有效预防。所以,流行病不适合胆小怯弱之人。
2016年2月1日,在巴西小头症病例攀升并成为世界焦点的几个星期后,世卫组织宣布寨卡病毒的流行已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受到国际关注。这一官方声明具有重要的监管、财政和政策后果,其目的在于将国际社会的注意力和努力集中到这一突发威胁上来。然而此时,寨卡病毒的暴发范围尚未厘清,病毒与神经系统缺陷之间的联系也没有研究透彻。世卫组织之所以选择此时发布警报,是因为等待确凿证据的过程太过漫长,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行动迟缓所可能导致的重大危险面前,每个科学家持有的谨慎和保守必须为之妥协。不过,做出这样的决定也是事出有因,该领域的特殊疫情已经为这一行动提供了支撑“证据”。
具有时间和空间的疫情是流行病学的基础资料。出于伦理和实践原因,流行病领域的证据很少直接来自实验室。在这种情况下,疫情的相关性就成了推论因果关系的间接证据。寨卡病毒引起小头症的证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不可能在常规意义上得到确定,尽管关于二者相关的证据正在增加。关于病毒感染后造成破坏性后果的分子、细胞和发育证据,将需要长期的工作积累来揭示。然而,我们需要倚重统计学的推断能力:至少目前的统计分析表明,流行病学家除了能推断出病毒感染与神经缺陷存在因果关系外,他们还不能解释寨卡病毒与小头症发病率的耦合上升。
流行病学挑战了“精确预测能力是任何真正科学的标志”这一错误理解。像宇宙学和进化生物学一样,在流行病学领域,历史和偶然性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肯定的是,该领域也力求精准预测:流行病学家试图预测疫情的严重性,希望能确定下一个疫情的确切地方,希望能衡量公共卫生干预对疫情的潜在影响。所有这些预测未来的方法都是基于过去的。当预测的现象受到多因素影响时,这种外推方法就是冒险的游戏。
影响疫情的所有因素――宿主、病原载体、传染源――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我们找不到两次完全相同的疫情。1947年,寨卡病毒首先在从一只乌干达恒河猴中分离出来,从此以后进化迅速。前两次寨卡病毒疫情(在雅浦和法属波利尼西亚)与此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后果都不尽相同。每次疫情都源于一系列不可重复的事件,因此,流行病学精准预测的能力必然受限。流行病学家挖掘这些独特事件,寻求其规律,深化了我们对人类和病原体关系的理解。
人类开始积极反抗
这一次,人类再次陷入与突发疫情的斗争,遗憾的是,截至目前,寨卡病毒似乎仍处于上风。通过早期的几次交手,我们了解到寨卡病毒能充分利用人类为之提供的每一个机会。寨卡病毒传染的后果差别很大:对于一些人来说,可能只是轻微的发烧和皮疹;然而对另一些人,可能会造成临时麻痹和其他严重的神经系统影响;对孕妇来说,则有可能生下小头症患儿。近乎残酷的是,这些症状似乎都是病毒进化所造成的偶然后果。
病原体和宿主之间的斗争历程和生命本身一样古老,在这一历程中,双方偶尔会签署一些临时停战协议。由此看来,我们与寨卡病毒之间的战争,只是人类与诸多疾病战争长河中的一个小战役。然而,这样的战役越来越普遍:新疫情的出现比以前更加频繁。我们与病原体的关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大多数传染病发生在局部范围,集中在一个或最多几个小范围人群,疫情会很快过去,留下死亡或免疫的幸存者。然而现在,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
随着宿主、病原载体和病原体在全球范围内快速迁移,我们可以将全人类看作一个单一的身体。当这个身体的任何局部受到感染时,其整体健康亦将受到威胁。同样,对局部新疫情的有效应对,可以将我们对疫情的监测、遏制和治疗转化为一种全球性的免疫反应。在全球化的世界中,我们应该对威胁健康的疫情保持永恒的警惕。
突发疫情所带来的恐慌,似乎表明我们此前在应对上的束手无策。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从移动电话到互联网搜索引擎等新技术,已经成为疫情的早期预警系统;新的诊断技术也使得流行病学家能够更快速、更精准发现传染源;导致疫情传播的各项因素正受到普通大众和专家群体的密切监控,这同样有助于我们发现早期疫情。疫情发现越早就能更好进行控制。通过区域范围和国际范围的通力合作,人类不再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积极的抵抗者。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岳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