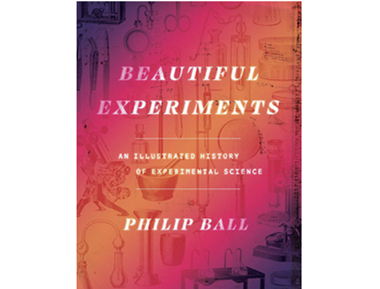我们在科学中发现美是永恒的,但不能让它蒙蔽我们的双眼。
17.1_副本
《美丽的实验:插图实验科学史》(Beautiful Experiment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of Experimental Science),菲利普·鲍尔著,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23年9月出版
许多人可能会惊讶地发现,“美”这个字眼在今天更有可能被科学家而非艺术家说出。当代艺术家和艺术理论家几乎认为这个词是不合适的,或许甚至不值得信赖。与此同时,科学家们却对“美丽的理论”以及美丽的实验赞不绝口。许多人声称,这种审美反应与艺术引发的审美反应没有什么不同,但要确切地定义它的内容,或是确定它如何被唤起,却很困难。
一些科学家将美与对称性联系在一起——对称性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核心特征——但他们无法调和这一观点与艺术中的美学理论。例如,伊曼纽尔 · 康德(Immanuel Kant)的宣言就对它提出了挑战:“所有僵硬的规律性(比如近似于数学规律性的那些)都有一些使人反感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对它的简单性感到厌倦。虽然一些科学家坚称,他们对美的概念是永恒、普遍的,但很少有人会对艺术下同样的断言。
一些哲学家认为,科学中的“美”仅仅是真理的代行:真理必然是美的。若果真如此,那么这种所谓的审美判断似乎有点肤浅,也很危险:我们可能会仅仅因为认为某个想法美丽而过分信任它。
然而,有些科学家为这种观点进行了辩护。例如,英国物理学家保罗 · 狄拉克(Paul Dirac)声称,一个理论是否美丽比它是否与实验相符更加重要,而爱因斯坦则表示,“我们唯一愿意接受的物理理论就是那些美丽的理论”。另一些人则对美的认知是否能够指引真实表示怀疑,动物学家托马斯 · 亨利 · 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说,“科学的伟大悲剧”在于“一个美丽的假设被一个丑陋的事实抹杀”。
为什么“美”在被视为客观的科学领域会是一个有效的描述词?一种论点认为,科学家的审美反应刺激的神经通路似乎与那些对艺术的审美反应相同。但这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有说服力。毕竟,性、食物和音乐都会激活大脑中相同的奖赏回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同的活动,也不意味着其中一个可以替代另一个。没有证据表明我们的大脑拥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神经层面的“美之回路”。
与“美丽的理论”这种观念相比 (这个评价常常被用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实验结果就不那么经常被评价为“美”了。倒不如说,它往往是在得出结果前进行的判断,而且更多地针对实验程序中体现的设计和逻辑。正如法国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皮埃尔 · 迪昂(Pierre Duhem)所说,实验可以被视为具体的假设——而且,能够高效、毫不含糊地转译假设的实验对人们有一种吸引力,比如欧内斯特 · 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对α粒子的研究中的实验。就算如此,那些通常被认为美丽的实验,它们的“美”也多半有一部分要归功于事后的辩护。可能有许多计划周密、执行完善的实验因为没有出结果、结果不够好,或是无法被轻易解释而被遗忘。
有了这个前提,实验被赋予的美更多地在于它的执行,而非结果。它与对某盘国际象棋的(专家级)鉴赏有一些共同之处,后者源于行棋之恰当、策略之优雅,以及迫使对手出某一手的选择。
虽然17世纪的弗朗西斯 · 培根(Francis Bacon)曾发表过知名言论,称实验在一定程度上即对自然的胁迫,但按爱因斯坦所言,一次优雅的实验看起来更像是实验者与自然合作揭示“某些深藏的事物”。一个美丽的实验会整合可用的资源,揭示随意检查无法发现的事物。许多生物学家之所以认为揭示了DNA复制机制的梅瑟生-史达(Meselsohn-Stahl)实验是他们学科中最美的实验,是因为它将一个看似不可能的难题——区分看起来结果相同的可能性——变成一个可解决的问题。
美作为一种学习和探索的手段
在实验中,有许多潜在的美学要素:概念之美、仪器设计之美(尤其是经济性)、两者之间的适宜性和经济性,以及解释结果时的推理之美。
这些都是需要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特质——它们没有定规。有些科学家似乎天生就擅长设计在美学上令人愉悦的实验,卢瑟福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比起在理论中,这类优点也许更容易在实验中发现,因为它们往往不需要深奥的知识,而且明确地内置于实验中。
2015年著作《美丽之问:宇宙万物的大设计》的作者、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弗兰克 · 维尔切克(Frank Wilczek)认为,当一个科学观点的“输出超过了你的投入”,那它所蕴含的美就会显现出来:这个观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新东西,揭示了超出预期的内容。
这一观点在应用到实验上时变得十分有趣,因为与理论相比,实验的“可交付成果”更加明确:它的答案通常是一个简单的是/否或这个/那个。然而,人们也可以在实验的答案中找到极为丰富的内容。比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1953年引导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解决了DNA分子结构的晶体学研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双螺旋结构本身就很美——克里克和沃森都使用过这个字眼,尽管传统上禁止在书面文章中使用它——但正如两人在他们的发现论文中狡黠地提到的那样,它也展示了细胞分裂时DNA可能的复制方式。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结构也会给后面这个问题提供如此显而易见的答案。
工作中的艺术家 新西兰物理学家欧内斯特·卢瑟福发现的α粒子来自一系列具有长久不衰的效率之美的实验
也许我们不应该太过努力地确定美在科学中的概念:试图让它变成一个可量化、可测量的参数可能会杀死它,就像活体解剖会杀死不幸的实验室动物那样。无论如何,美丽的实验就如美丽的理论,很可能会拥有更强的说服力:当然,自然就是这样的!这里有点危险——我们不应该被美丽蒙蔽。但是从定义上讲,美丽的实验几乎就是好的实验:它们清晰、明确,并且以一种合乎逻辑和有序的方式使用可用的手段。这无疑是实验者应当努力追求的工作方式:美在这里也具有教学功能。所有的科学都必须与其时代相符,而好的科学能够产生、也确实产生了会在后来被修正和取代的答案。
什么才算一个好的实验?
科学总是被错误或未经证实的实验结论困扰。例如,1988年,由法国免疫学家雅克 · 本分尼斯特(Jacques Benveniste)领导的科学家报告说,一种生物制剂的化学溶液即使稀释到完全不再有活跃分子的程度,仍然显示出了生物活性。本分尼斯特认为,这表明水具有“记忆”——保留了溶解在其中的分子的印迹。尽管这份报告是真诚的,但其结果永远无法复制,如今,它被认为是美国化学家欧文 · 朗缪尔(Irving Langmuir)所谓的“病态科学”的例证之一。
更好的做法或许是将这些结果视为糟糕的实验。它们的设计方式排除了产生明确结果的可能性。有太多可能会影响结果的不可控因素。科学实验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在于使其具有辨别力:你需要找到一个可以严格探究你的假设、并可能将其彻底排除的方案。
科学家们经常声称,他们的实践受到“科学方法”的指导,这指的是由一个人提出一个假设,做出预测,然后设计一个实验来对其进行测试。但这是一种现代观点,它是在20世纪初由约翰 · 杜威(John Dewey)和查尔斯 · 桑德斯 · 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为首的“实用主义”哲学家们定下的。后来的科学哲学家,如保罗 · 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质疑曾经的科学是否也如此公式化,并认为科学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同样依赖于修辞技巧和说服,而不仅仅是逻辑和论证。
这让一些科学家感到不安,他们坚持认为“经验”——观察和实验——是真理的终极裁决者。然而,尽管从长远来看,与实验观察反复发生冲突的理论无法生存下去,但从短期而言,面对明显的矛盾,理论家们坚持自己的观点或许是正确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对立理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就某个实验的解释产生争论。其中一方之所以能够获胜,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解释正确,而是因为他们更善于陈述自己的观点。或者,一位科学家可能仅仅是因为提出了错误的问题,而从一个正确甚至优雅的实验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这一切都使得科学事业变得复杂、模糊、具有了社会性,但同时也使得它更加丰富、更具创造性、更辉煌地展现了人性。
资料来源 Nautilus
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是一位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