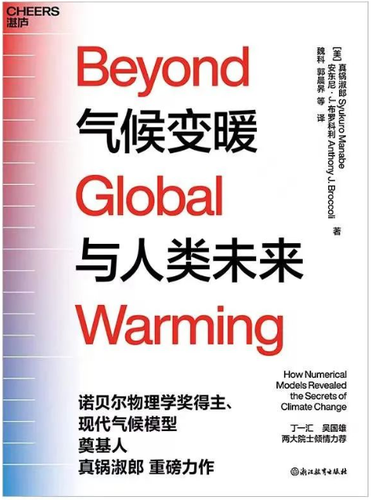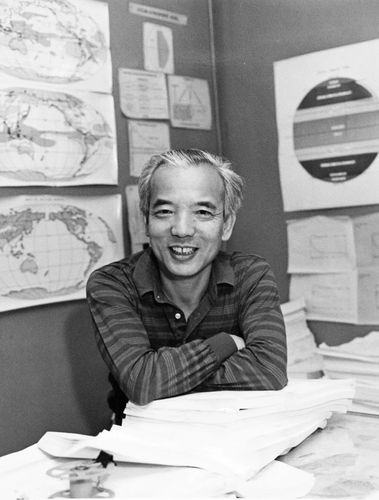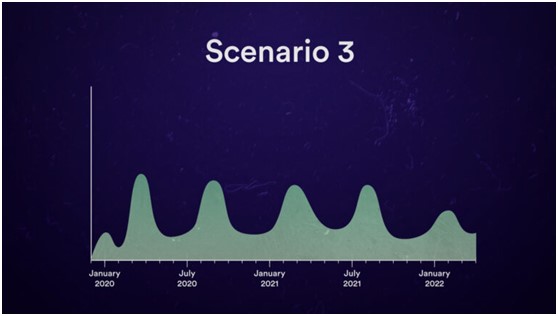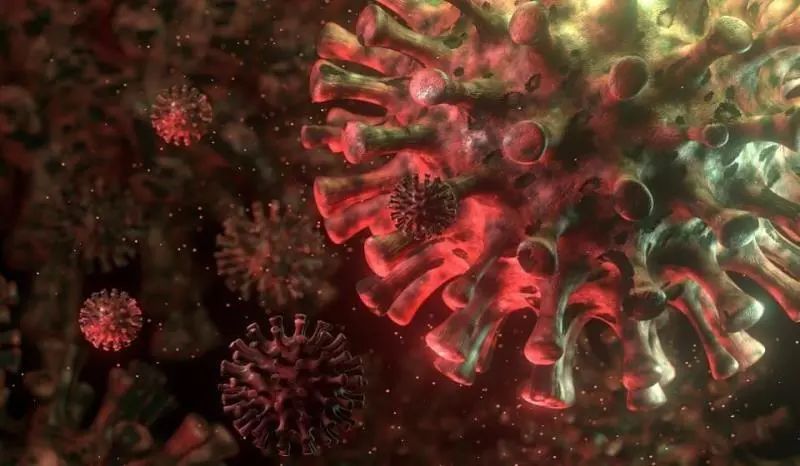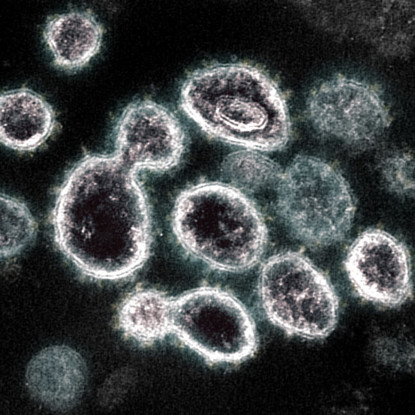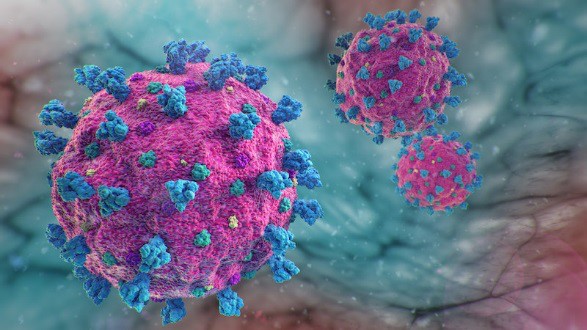202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日裔气候学家真锅淑郎(Syukuro Manab) 开创了关于地球气候的物理模型,也首次明确证明了二氧化碳浓度对气候的影响。正因他的工作,我们才开始了解地球气候,了解自己对气候产生的影响,开始关注全球变暖问题。
最近,真锅淑郎所著的新书《气候变暖与人类未来》出版。书中主要内容源自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的课程。这位现代气候模型先驱希望通过书籍,让更多人了解气候如何变化、变化为何发生,以及未来会有怎样的变化。
中国科学院院士、气候动力学家吴国雄为此书作序,讲述了自己与真锅淑郎的交集,对他的印象,以及他为中国气候学界提供的帮助。
真锅淑郎
1989年到1991年,我以高级访问教授的身份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气和海洋项目是其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GFDL)合作的产物。对于国外访问人员,普林斯顿大学会安排一个顾问负责联系与沟通和合作,真锅淑郎当时是我的顾问。中国有好几位气象学家都在那里访问过,像曾庆存先生、巢纪平先生等,叶笃正先生是第一个去的。叶先生在美国气象界的名气很大,他是芝加哥学派领袖卡尔—古斯塔夫·罗斯贝(Carl-Gustaf Rossby)的高徒。罗斯贝曾在1949年专门为叶先生发表的关于大气频散的论文写过评语,说他的数学基础非常好之类。叶先生那篇动力学的论文非常著名,他和约瑟夫·斯马戈林斯基(Joseph Smagorinsky)还是好朋友。斯马戈林斯基也是位传奇科学家,他参与了全球第一次数值天气预报,是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创立者和领导人。1981年,斯马戈林斯基特地邀请叶先生访问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叶先生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所长。1982年叶先生在访问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期间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所以他没有完成访问就回国上任了。
真锅淑郎对叶先生也非常崇敬,两位大师可以说是相互欣赏,经常切磋交流。叶先生思路非常开阔。当时大家对海洋的记忆及其对气候的延迟响应已经有所了解。叶先生提出土壤记忆的问题,他与真锅淑郎、托马斯·德尔沃斯(Thomas Delworth)合作写了一篇文章,利用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模式,在初始时把全球的土壤都灌满水,看看陆面对气候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结果发现土壤也有记忆,记忆时间大概是几个月。这项工作是非常早的研究,也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后来英国科学家贾森·朗特里(Jason Rowntree)做了类似的工作,证实了土壤记忆约为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们研究青藏高原如何影响东亚夏季风,也证实了土壤记忆的时长。
科学家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很勤奋的科学家,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每天早起上班,晚上加班,非常勤奋和辛苦;一种是依靠天赋和思维敏锐度的科学家。真锅淑郎属于后一种类型,他当时几乎每天下午要游泳和跑步,生活非常有规律,花在运动和生活上的时间确实不少。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两三个人花个把小时。中午我们吃完饭,从校园到食堂要散步一段路。
真锅淑郎是思维非常敏锐的科学家,靠的是高效率。在普林斯顿几乎每周有一次学术报告,要么是来访的学者,要么是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的科学家做报告。他每次都要参加,并坐在第一排,经常斜靠着椅背,有时候闭着眼睛,看着像在睡觉。实际上不是,他一直在专注地听。他在睁开眼睛问问题时思维会非常敏锐,此时往往是普林斯顿大学学术讨论的高潮和精华。
在气象模式的发展中,积云对流是其中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因为气象模式是格点化的,当时网格距达到100千米的数值模式精度已经是非常高了,大多数只有几百千米。积云对流尺度小,局地对流发展造成降水,模式根本分辨不出来。大家都在想办法,但最早提出解决方案的就是真锅淑郎,这说明他很聪明。他把极其复杂的过程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一般在大气中决定降水和对流的一个重要因子是相当位温θe。一般来说随着高度增加,当水汽很多的时候,θe减小,用气象学术语来说叫作对流不稳定。对流不稳定就会形成一朵朵云,绵延几十米、几百米甚至几千米,台风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云包。在网格上百千米模式里怎么表示积云对流?
真锅淑郎想了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对流不是源自大气底下的气流不稳定吗?θe随高度增加本来应当增加,但对流的时候变成了随高度增加而减小。这说明底下的水汽太多了,于是大气调整自身达到稳定,一层一层往上调,不稳定的大气就把过多的水汽释放出来形成降雨。随着一层一层调整,上面的θe增加了,直到上面稳定了,降水就停了,这被称为对流调整方案。这方案到现在有的模式还在用,我们的模式早期也用过,其结果比很多对流参数化的效果还好。这个例子说明真锅淑郎考虑问题能抓住本质,简洁明了。
1989年,我到地球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从事访问研究是由叶笃正先生推荐的,当时我刚从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回国不久,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时任主任伦纳特·本特森(Lennart Bengtsson)也推荐了我。1991年我从普林斯顿大学回来,随即我们邀请了荒川昭夫来访问。1993年真锅淑郎和英国的约翰·格林(John Green)来我们的实验室讲课,那是真锅淑郎第一次来中国访问。大家对他们的到来感到很兴奋。格林和真锅淑郎两个人都很活跃,跟中国的科学家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2000年,我们在上海主办了一个气候环境的国际会议,邀请真锅淑郎来大会主讲。最重要的一次是2005年,当时我作为国际气象学和大气科学协会(IAMAS)的副主席,筹备了该协会在北京召开的科学大会。这次科学大会被公认为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大会,我们邀请了很多国际著名的科学家,像罗伯特·E.迪金森(Robert E. Dickinson)、麦文建、廖国男、布赖恩·J.霍斯金斯(Brian J.Hoskins)、真锅淑郎等。那一年正好是叶笃正先生90寿辰,所以我们专门开了一个特别分会庆祝叶笃正先生的成就,请各个领域的科学家来交流。当时这个分会的主题就是“从大气环流到气候变化”(From General Circulation to Global Change),正是叶笃正先生的两大贡献。在北京期间,真锅淑郎专门做了几个报告:IAMAS 科学大会报告、给叶先生祝寿的报告、大气科学和地球流体力学数值模拟国家重点实验室(LASG)成立20周年的报告(1985—2005年)。会议期间叶先生还专门邀请真锅淑郎和霍斯金斯到家里做客,真锅淑郎跟我们是关系很好的朋友。
真锅淑郎的访问也确实推动了我国大气科学的发展。
例如,在模式发展方面,我在1989年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跟他讨论了当时由LASG最早自主发展的一个包含两层大气和4层海洋的耦合模式,该模式参与了最早的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的模拟。他表示能够独立创造非常好,建议我们要发展几个有特色的模式,特别是海洋模式。国际上当时都是海洋表面具有大气强迫的刚盖模式,LASG的科学家把这种模式改成了自由表面模式,即海洋表面随时间变化而变化,这个工作做得很不错。
真锅淑郎建议还是要发展多层模式。我告诉他关键是没有计算机,因为当时美国和巴黎统筹委员会在高科技方面对中国严加控制,我们买不到像Cray 1这样的计算机,甚至连要报废处理的Cray 1都买不到。他说你们要克服困难,两层模式尽管很有研究价值,但是用两层资料来表示地(海)表信息很不准确,你们将来要搞海气耦合和陆气耦合就存在比较大的困难,多层模式反而比较容易。真锅淑郎还建议,你们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除当时两层的格点模式以外,还应当发展谱模式。我1991年回国后,跟叶先生和LASG的时任主任曾庆存先生都汇报了,他们也表示支持。LASG从此开始发展多层模式,开始做GAMIL和SAMIL,其中GAMIL是格点模式,SAMIL是谱模式。
真锅淑郎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学术顾问,除了访问和讲课,他在具体的数值模式发展上,也曾经给我们一些好建议。在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专家跟我们的交流为我们实验室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真锅淑郎先生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确实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大气科学算是物理学科里的一个小分支,但诺贝尔物理学奖竟然授给了两位气候学家——日裔美籍的真锅淑郎和德国的克劳斯·哈塞尔曼(Klaus Hasselmann),这说明了现在社会对气候学的重视。大气科学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已经导致了全球气候变暖,这不仅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诺贝尔奖授给两位气候学家,既肯定了他们在气候数值模拟研究这个复杂科学领域里的贡献,也向我们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为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努力。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报纸曾经把真锅淑郎称为“温室气体之父”,那个时候“全球变暖”这个词还没有那么流行,甚至80年代有一段时间“核冬天”这个词还流行过。真锅淑郎的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讨论的是二氧化碳浓度增高产生的气候影响。二氧化碳能够吸收地面发射的长波辐射,像大被子一样盖住地面,使得地球无法释放长波辐射能量,从而导致底层大气变暖,真锅淑郎的理论就是用长波辐射的理论来研究的。真锅淑郎的长项是长波辐射研究,他在日本的时候跟他的导师正野重方做了不少这方面的工作,他这方面的基础很牢固。现在的气候模式还是利用二氧化碳的这些吸收特性,这种模式就基本上出自真锅淑郎最早提出的理论,区别在于现在的模式不止是单柱的,还要受到平流过程的影响。平流过程在各个模式之间有差异,这就造成了不确定性,不过总体结果与真锅淑郎早期的单柱模式结果非常接近。理论上讲,他得出的2.5℃左右的气候敏感度的数值在单柱模式里是有严格标准的,但受到大气环流的影响后,有的效应比它低一点,有的效应比它高一点,不过都在这个范围内,因此结果比较一致。
真锅淑郎强调科研中的好奇心,我非常赞同这点。我也经常跟学生讲,在对科学的追求上,好奇心和求知欲非常重要。如果对一个问题有好奇心和求知欲,你就有动力去解决它。好奇心是激发科学家探索发现的驱动力。我前面提到的积云对流很复杂,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谜题,是很难啃的骨头,但真锅淑郎偏要去啃。后来想想答案也很简单,不稳定不就是因为底下水汽太多了吗!让大气抬升凝结降雨,降掉多余水汽以后就变稳定了,能量释放出来,大气又被加热,所以就一层一层往上调。在描述马登—朱利安振荡(MJO)这样的低频振荡的过程中,水汽也是从底下释放的,这对低空的加热效果很强,对MJO的形成很重要。
好奇心给你一种信念,你就有一个动力去做事。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小的时候我听母亲和老人讲一些故事,如关于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等,觉得很神奇,觉得非常奇妙,所以上中学的时候参加气象小组,到气象站去看百叶箱。那时候我在小县城看到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如温度计、百叶箱里头的仪器等,觉得很神奇,一直认为研究气象会有很多乐趣,后来报了三个气象志愿,最终走上了气象研究之路。“目标始终如一。”《自白》中马克思对其女儿以此形容他自己的特点。有了好奇心以后,任何诱惑都不会使你放弃最初的追求。
大气科学是地球科学中理论方面较成熟的领域,这是因为从20世纪初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气象观测站形成了全世界的气象观测网,充足的资料和数据使大气科学在20世纪迅猛发展起来。然而最近这些年,其他地球科学领域也快速成熟起来,而大气科学领域的发展缓慢。这一现象正在改变,大气科学引入化学领域产生了大气化学,引入辐射领域产生了大气物理学;同时,经济学领域也在讨论气候变化。大气科学领域的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最近地质领域在讨论生物地质学(地质生物学),生物地质学推动了地质科学的发展,现在很多年轻科学家在研究地质的演化过程中生物到底起到什么作用、生物对地球气候起到什么作用。生物气候也正是真锅淑郎感兴趣的领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谜题,它与人的健康密切相关,那就是PM 2.5对我们的呼吸有什么影响。气候模式里有生物气溶胶,微生物跟气溶胶都是微观的,而气象是宏观的,当两者紧密联系时,生物过程就会通过环境影响到绿色植物,影响到动物的演化过程,从而对气候产生影响。
真锅淑郎提到未来生物气候可能大有发展,我认为大有发展的范围可能更广泛一些,不管是天气、气候还是大气环境,都可以和生物学很好地结合起来。希望未来在生物气象学领域也有人获得诺贝尔奖。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