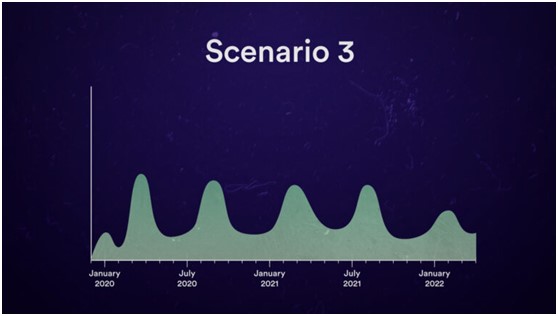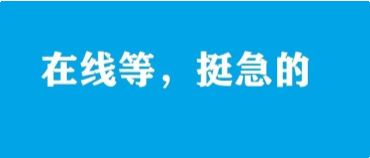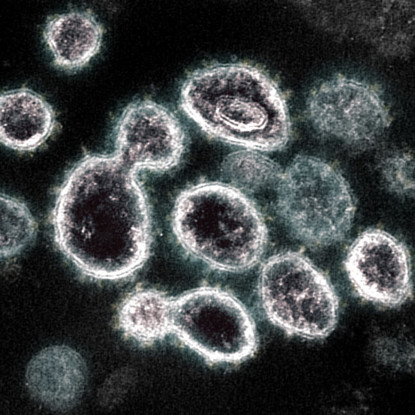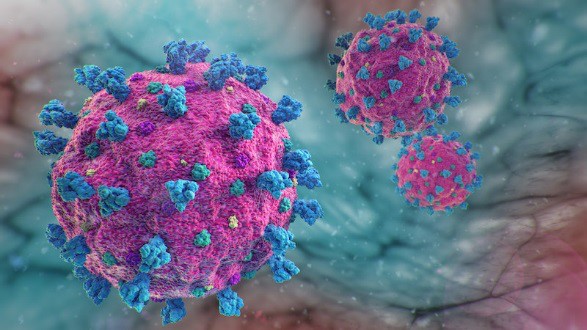如果有人跟你描述这样一套交通服务体系:
乘客要打车,司机要接客,乘客通过平台远程召唤司机,平台通过基于时间、距离和运载量的复杂算法在行程开始前向乘客和司机同步显示费用。这套系统代表了创新商业模式,承诺提供高效服务并降低费用,有望打破传统出租车垄断局面,其高度透明的计价机制……
你大概会马上想到滴滴或Uber——两大全球知名、崛起于2010年代初的网约车平台。
但你想的并不对,因为这套自动化出租车调度系统的原型诞生于1975年,是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械工程师德怀特 · 鲍曼(Dwight Baumann,已故)与其学生们的创意,旨在复兴一家已倒闭的出租车公司。
鲍曼等人创作的电话叫车服务也是卡内基梅隆大学创业发展中心(CED)扶持的11个企业项目之一。CED得到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大力资助,其定位为“创新孵化器”,其使命包括:
· 挑战科研与高等教育的传统范式
· 培养具有冒险精神且专注于用市场化技术方案解决社会问题的校园初创企业
· 重塑美国科学界以满足国家需求
如今,像CED这样高校背景的创新孵化器已遍地开花。它们都致力于将创意转化为商业,将发现转化为应用,将课堂作业转化为收益,将师生转化为创业者。
大学是创新引擎的理念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想当然地觉得本就如此。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去追溯历史上第一批创新孵化器的孵化历程,或许能从中读出更多启发。
创新者是天上掉的还是后天造的?
冷战期间,美国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培养模式服务于线性创新机制:科学家在大学和联邦实验室从事“基础”发现;工程型科学家也在校园里(但并不与前者在一起)进行“应用”研究;工程师在洛克希德、波音等企业的庞大团队中实现创意;研究管理人员则监督统筹整个过程。
此模式主导了那时美国的国家科学政策,将科学家推升至超越政治、追求真理的英雄高度,也为高等教育导入亿万美元资金。在实践中,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界限其实模糊不清,但这种在理念上泾渭分明的层级划分,却是NSF及其所培育的大学科研文化不可或缺的基石。
1960年代末,这套战后形成的学术科研体系开始显现裂痕。科学技术被视为环境破坏、越南战争、失业问题以及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的根源。与此同时,国家科学政策领域也面临类似“审判”——激进批评家抨击科学家与军工复合体的共谋关系,保守派则谴责象牙塔内的科研经费浪费。
在反叛传统的浪潮中,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及加州和马萨诸塞州这些科技蓬勃发展之地的创新专家开始将创新者视作变革推动者,因为这些人与美国科学界的传统权威截然不同。
最终,从官僚、发明家、学者、商界领袖到工程师,各界人士达成共识:创新者驱动国家进步,而培养创新者的任务完全可以通过大学教育达成。
问题在于:该如何培养?大学又是否愿意自我革新以支持创新?
于是,开发出能培养这类敢于冒险的“社会技术专家”(sociotechnologist)的成功模式,成为NSF的使命。
NSF的创新实验
1972年,NSF主任H · 盖福德 · 斯蒂弗(H. Guyford Stever)创立了实验性研发激励办公室(Office of Experimental R&D Incentives),旨在通过研究“政府如何最有效地加速新技术向生产型企业转移”来为国家需求激励创新。
斯蒂弗特别强调新计划的实验性质,因为当时有包括NSF内部成员在内的众多科学界人士都抵制目标导向型研究;而所谓的“创新”,本就自带利润和社会变革的内涵,更令人质疑。
斯蒂弗任命联合飞机公司(United Aircraft Corp.)研究经理C · B · 史密斯(C.B. Smith)领导该项目。史密斯随后引进一批具有工业经验的工程师,包括汽车工程师罗伯特 · 科尔顿(Robert Colton,已故)。正是科尔顿当时主持的大学创新中心实验,后来催生了卡内基梅隆大学的CED。
NSF的创新中心大计划精选了四所代表不同创新孵化路径的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通过正式课程和创新合作教育项目聚焦本科生培养,帮助他们把创意转化为产品
· 俄勒冈大学负责评估来自全美车库发明家的创意。车库发明家这一文化现象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并在二战后的科技创业浪潮中而广为人知,其最鲜明的特征是个人或小团队在非正式、低成本的环境下,例如自己家的车库或地下室内,做出技术创新
· 犹他大学致力于围绕其实验室孵化的生物技术与计算机图形学初创企业打造创新生态
· 卡内基梅隆大学成立非营利公司以支持研究生创业。前文介绍的电话叫车服务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在麻省理工学院由NSF资助的创新中心,科技达人格伦·达什(Glen Dash)设计了低成本的视频游戏
在犹他创新中心,工程系学生约翰·德容(John DeJong)和道格拉斯·基姆(Douglas Kihm)正研究可编程电子面包板
卡内基梅隆大学:首批大学孵化器的诞生地
卡内基梅隆大学(CMU)具备当时公认的创新必备要素:强大的工程实力、顶尖的商学院、聚焦社区需求的城市规划新理念、工业设计与实用艺术的悠久传统。校方领导层更宣称,相比麻省理工学院,CMU规模更小、更年轻、学科交叉性更强、更具灵活性。
但CMU能成为NSF创新中心之一的关键在于其负责人德怀特 · 鲍曼(Dwight Baumann),一位“教育家-创业者”身份的创新典范。
从北达科他州立大学毕业后,鲍曼赴MIT攻读机械工程博士学位,期间发现了自己对教学事业的热爱;他也是位极具创造力并因此赢得美誉的工程师,热衷于解决与人类需求相关的技术难题。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鲍曼先后以MIT学生和教授的身份参与开发了最早的计算机辅助设计程序之一,为视障人士设计了计算机交互系统,还打造了全美首个电话预约式辅助客运系统。这些成就为他日后领导CMU创新中心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鲍曼对MIT以国防科研和工程科学为主导的学术氛围感到失望,于是在1970年辞去终身教职,转赴CMU继续开展交通系统方面的研究。
CMU时期的他主导创建由NSF资助的非营利组织CED,以一美元价格收购破产的人民出租车公司(Peoples Cab Co.),说服校方将一处废弃停车场作为创新孵化器的空间,还与多个学院合作设立了工程设计硕士项目。
CMU创业发展中心主任德怀特·鲍曼认为,现代大学应该提供创业教育
鲍曼的愿景是将创业教育确立为现代理工大学的核心功能。他并不那么关注盈利,也不太在意全球竞争。他公开宣称的目标是释放人类创造力。“没有围墙的工作室,松散关联的一群人,彼此交流、需要时互相帮助的团体”。
CED的使命是为处于创新初期、渴求空间和种子资金的创业者提供支持。它给了学生们一个可以犯“一连串非致命错误”的成长环境,让他们能在失败中积累应对创业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自信。CED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已接受过高级科学与工程训练、具备可行创业构想的研究生。
这座创新中心在成立后的五年内共孵化了11个项目。除了重启的匹兹堡人民出租车公司,还有血氧仪、计算机硬件公司和报纸印刷技术等方面的尝试,但许多项目都失败了。
创始人健康出现问题,专利纠纷不断,竞争对手指控CED项目仰仗CMU的影响力获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CMU的电话叫车服务复制了人民出租车公司的模式,后者曾为匹兹堡的黑人社区提供出租车服务
CED把各种经验教训提炼总结为宣传手册和公开研讨会上的内容,教师们则将其融入新课程中。有一份包含十条要点的“准备评估表”强调,预备创业的人在开展任何针对技术或市场的评估前,应先作自我反思。
准备评估表的第一条准则明确指出:“只有当你发自内心地决定投入时间与精力,并理解牺牲和风险不可避免时,才应考虑踏上创业之路。”
也有部分CED学员创业成功。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故事是电气工程博士生罗梅什 · 瓦德瓦尼(Romesh Wadhwani,来自印度)与克里希纳哈迪 · 普里巴德(Krishnahadi Pribad,来自印度尼西亚)共同建立Compuguard公司。
二人耗时18个月研发出一款利用无线信号保护高危行业从业者的安全手环。虽然原型设计未能变为实用产品,但他们选择转向,开发出适用于学校、监狱和仓库的安全与能源监控系统。
在CED助力下,Compuguard拿到政府合同和数百万美元的风险投资,员工规模突破百人,其首个大客户是洛杉矶联合学区。两位创始人后来以现象级的投资回报率出售公司。瓦德瓦尼成为连续创业者,如今更是硅谷首屈一指的亿万富翁慈善家,他创立的基金会支持全球创新创业教育,尤其关注新兴经济体。
1978年,NSF给CED的资金耗尽,长期积压的矛盾集中爆发。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围绕鲍曼的个人崇拜,他粗放草率的行事风格背离了CMU的雄心壮志,后者想的是抗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等机构的新兴科技创业项目。
1983年,鲍曼的昔日搭档杰克 · 索恩(Jack Thorne)主导成立新机构“企业公司”(Enterprise Corp.),旨在帮助匹兹堡的创业者筹集风险投资。鲍曼甚至被逐出他惯用的车库办公场地方便为计划腾空间。
鲍曼将CED迁至废弃的基督教青年会大楼,尝试帮助失业技术工人转型为创新者,但收效甚微。
随着CMU的教职员工持续就“大学创新的正确定位是什么”与“谁有权教授创新课程”争论不休,这座曾经辉煌的创新中心日渐式微。
创新实验成功吗?
到1970年代末,美国的大学创新中心实验结束,NSF通过一系列报告、会议和文章自我表扬:“创新中心的最终效应,将是美国经济体系中发明、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一次新生。”
NSF还声称,这场实验催生了数十家新企业,总营收达2000万美元,创造近800个就业岗位,产生400万美元税收。不过截至1979年,知识产权许可收益仅累积10万美元。
以CED为代表的创新中心引来多方强烈关注。美国的一些知名商学院也走上类似的科技创新道路;来自加拿大、瑞典和英国的考察团希望复制该模式。
研究生弗里茨·福尔哈伯(Fritz Faulhaber)手持1970年代CMU学生在匹兹堡出租车上安装的无线电耦合计价器
当然,也有来自反对派的批评声。
例如,威斯康星州参议员威廉 · 普罗克斯迈尔的抨击称:创新中心资助的香蕉剥皮机、电子游戏和运动装备等项目简直“浪费联邦资金”,它们“对美国纳税人的益处值得商榷”。
非洲裔的美国化学家格兰特 · 维纳拉布尔(Grant Venerable)则批判该计划将创新狭隘地定义为精英大学白人男性的专属领域。
可以说,NSF创新中心实验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的。那个年代的许多教授和管理者仍倾向于认为此类项目轻浮、非学术、不值得投资。
但今时今日的美国人都能清楚看到,NSF实验的遗产几乎帮助着每所大学校园。它用制度化、系统性的力量整合了科学家、创新者和创业者的多重角色,把他们变成既精通热力学定律又深谙资本运作且还敢闯敢拼的冒险者。另一方面,创新中心的故事确立了创新教育的根本目的——不只为培养赢家,所有学生,包括那些从未打算将创意商业化或建立初创企业的人,都能从学习创业中受益。
可以说,NSF开辟了一条新路,使“创新”这一在二战前几乎不被视为文化标杆的概念,最终深深植根于美国人的制度体系、教育模式乃至自我认知之中。
资料来源: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ITY AS INNOVATION INCUBATOR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