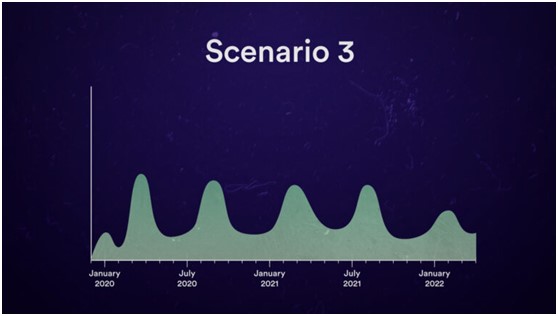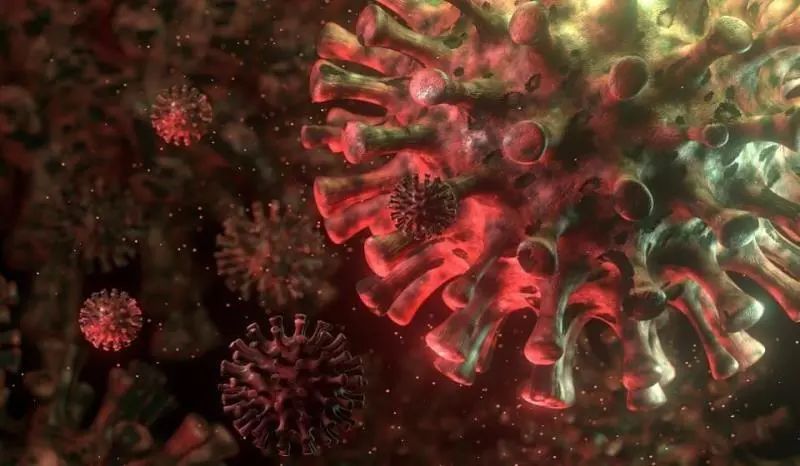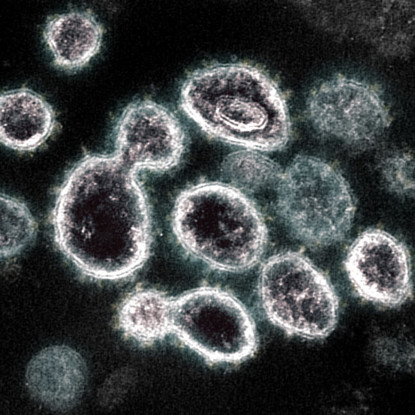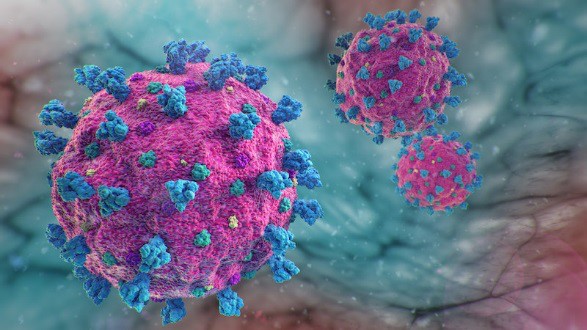古人类学是一门相当去中心化的学科。
不必围着某台稀缺科研重器打转,也不要求有组织、大规模的通力协作,古人类学者们总向四面八方探寻化石,也向四面八方发散思路。因此,给这门学科作年度进展大盘点,容易盘得太散漫太琐碎,或太笼统太粗疏。
撰写本文的科学记者迈克尔 · 马歇尔(Michael Marshall)反复思量、深刻提炼,围绕三个话题回顾了2025年古人类学的重大新发现、新理论——
神秘的丹尼索瓦人显露了一系列令人震撼的真相;
史前人类在制造使用工具方面有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故事和经验;
关于人类与万物不同的思想,我们应以怎样的思想去解读那些思想?
丹尼索瓦人研究井喷之年
2025年是丹尼索瓦人被科学界发现的第十五个年头。
这种适应能力非凡、足迹遍布亚洲的神秘古人类令无数研究者着迷,而今年涌现的一系列迷人发现揭下了他的面纱,开拓了他的领地,暴增了他的年纪,也引出了更多关于他身份的谜题……
丹尼索瓦人是首个主要通过分子证据确认的古人类族群。其为人所知的第一块化石是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穴里的一小节指骨,即“丹尼索瓦3号”(Denisova 3)。该样本因太小而无法用以辨认身份,不过在2010年被提取出了DNA。
基因分析显示,丹尼索瓦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姊妹族群,也曾跟智人(也就是现代人类)产生基因交流。如今生活于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人群,其基因组保留着现代人里最高比例的丹尼索瓦人DNA。
从小指骨开始,学界大力探寻更多丹人遗存,不过起初进展缓慢,直到2019年才确认第二块化石:来自甘肃夏河白石崖溶洞的下颌骨。
再往后的五年间,又有少量新化石提供线索:丹人似乎体型高大,且作为如此晚近的古人类,其牙齿显得太过粗大了。
2025年迎来了新发现的井喷。
4月,科学家明确了一块2008年从澎湖海域打捞出的“澎湖一号”(Penghu 1)下颌骨的身份。没错,正如此前学界普遍猜测的,化石主人就是曾抵达中国台湾地区的丹尼索瓦人,核心证据是化石内保存的古蛋白质信息。
此发现将丹尼索瓦人的已知栖息地向东南大幅扩张——这也与当前丹人基因痕迹的地理分布相吻合。
6月,我们首次目睹了丹尼索瓦人的相貌。严格来说,我们早就见过这幅骨相。2021年公诸于世的哈尔滨头骨完整了展现人属新物种“龙人”(Homo longi)的模样,而付巧妹团队证实“龙人即丹人”。(实际上学界早已根据体型等人特征推测该头骨化石属于丹尼索瓦人。)
付巧妹与同事从骨骼里提取蛋白质,还从牙齿的牙结石处获得了线粒体DNA;两方面分析都显示,曾扎根中国东北的龙人与丹尼索瓦人同属一族。(详见:防止被日本抢走而藏入废井的那颗古人头骨,如今身份暴露…)
上述进展相当重磅,不过合乎大家对丹人的既有印象。而下半年的两项新发现则超乎认知。
9月的《科学》(Science)杂志报道称,出土自湖北省郧县的破碎头骨“郧县人2号”(Yunxian Man 2?)经复原后,被确认属于早期丹尼索瓦人。因为这块化石有百万年历史,所以丹人一下“老”了至少几十万岁。此外,这也意味着,丹尼索瓦人、尼安德特人与我们现代人类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至少一百万年前——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古老。
10月,有遗传学家发表预印本文章称,他们从丹尼索瓦洞穴一颗20万年前的牙齿里提取出第二份完整、高质量的丹尼索瓦人基因组。其中关键在于,这第二份相比2010年取自丹尼索瓦3号的第一份基因组,差异相当显著;而且它也不同于与现代人携带的丹人DNA。
研究团队由此推测,丹尼索瓦人大家庭内至少存在3个小群体:一个较早期的支系,一个较晚期的支系,还有一个与智人杂交过的支系。其中第三个在考古学层面仍属未解之谜。
工具创始之路
制造和使用工具并非人类独有技能,许多动物都会操纵工具,今年离世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珍 · 古道尔更是证明了黑猩猩也能制造工具。人类从史前脱颖而出的关键在于:所用工具种类纷繁多样,所造工具结构精巧复杂,对工具的依赖无以复加。
通过探寻化石,我们不断向前追溯古人类的工具史。
今年3月,《自然》(Nature)报道了坦桑尼亚的考古发现:原来早在150万年前,就有一种身份不明的古人类定期地制造骨制工具;此前公认的骨器普及时代要比这晚百万年以上。
3月发表的另一项研究指出,过去学界认为象牙制品始于5万年前,但近期乌克兰出土有40万年历史的猛犸象牙加工碎片。
关于石器工具的考古成果往往年代久远(可能部分原因是石器更易保存),比如肯尼亚洛梅奎(Lomekwi)遗址出土的部分石器极为粗陋,诞生自330万年前。11月,有研究团队撰文介绍了来自肯尼亚纳莫罗图库南(Namorotukunan)遗址的发现:从275万前到244万年前,那里的古人类持续制造着同类型的奥杜威石器,这似乎表明工具制造那时已成常态。
我们往往无法确定工具的制造者,因为工具出土时鲜少伴有人类遗骨。大家习惯将其归功于人属成员,或是比人属(Homo)更古老的祖先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不过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傍人属(Paranthropus)作为同样由南猿演化而来但走向另一分化道路的人属表亲,也掌握制造技艺,至少能造出奥杜威石器这类简单器具。
傍人脑容量较小而牙齿粗大,曾于非洲生活数十万年。两年前,肯尼亚出土了一批伴有两颗傍人牙齿的奥杜威石器。由此学界开始大胆设想。今年10月再现力证。科学家首次获得了傍人手部骨骼的化石样本,分析结果显示其兼具大猩猩级力量与出色灵巧性,有能力完成制作石器所需的精准抓握动作。
或许会有人好奇:远古人类最初如何萌生了制造工具的念头?
考古学家梅廷 · 埃伦(Metin Eren)等人今年提出一种假说:工具并非起源于主动创造,环境中本就天然存在许多类似工具的石材,比如因霜冻崩裂的岩石,又如因大型动物踩踏而形成的碎石块。这些所谓的“天然石器”(naturaliths)最初只是被先辈运用,而后人摸索出了复制它们的方法。
随着所造工具越发复杂,掌握工艺所需的认知门槛也不断提高。制造难度越大,知识传播的重要性越发凸显——这可能就是推动语言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今年发表的一项工作考察了各类技能的学习难度,其中评判难易的标准包括是否需要近距离观察、单次教学是否足够、是否需要重复练习等。研究作者由此发现文化传播的两大转折,并指出此二者都可能与技术发展存在关联。
人类的独特性是多元复杂且自相矛盾的
从生物演化的视角看,人类是如何被造就为如此独特的存在的?现代人思考这个问题时总要面对三重挑战。
首先,人类的独特性是多元复杂且自相矛盾的。
今年7月,社会科学家乔纳森 · R · 古德曼(Jonathan R. Goodman)撰文提出,人类在演化过程中被塑造得既良善又凶残、既真诚又虚伪——这一刻道德君子,下一秒阴险狡诈。任何试图简化人性为“本善”或“本恶”的论调都是谬论。
其次,我们关于“人类为何独特”的认知深受社会环境影响。
举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在当前这个由男性主导的世界,大家对历史的解读几乎都着眼于男性。虽然也有女性主义运动试图推动改变,但道阻且长。科学记者劳拉 · 斯宾尼(Laura Spinney)今年发表过关于史前女性的专题报道,并根据一系列考古证据总结称:“她们曾担任统治者、战士、猎手和巫师。”
第三个挑战在于现代人几乎不可能还原古人类的真实想法。
比如,远古人类最初怎么想到要埋葬死者或举办某些丧葬仪式?又如,驯化犬类的过程是如何开始的?实际上,今年有专家就这两方面话题表达了新见解。以埋葬行为来说,科学家发现那些脑容量仅为人类1/3的南非纳莱迪人(Homo Naledi)竟能通过一系列复杂仪式将逝者埋入洞穴深处、难以进入的“墓室”。但关于此类行为的动机和起点,我们真的难做判断。
关于人类大脑与智能的演化,有两种理论值得大家探讨。
其一是胎盘性激素可能发挥关键作用。子宫内的胎儿会接触胎盘性激素,这些激素或可影响大脑发育,赋予人类独特神经能力以应对异常复杂的社会生活。
另一个有趣的假说认为:驱动智力提升的基因变异,可能也同时导致人类易患精神疾病。根据今年8月发布的研究结果,当我们的史前祖先获得改变智力的变异后,精神疾病相关突变接踵而至。
资料来源:
2025 was chock full of exciting discoveries in human evolutio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