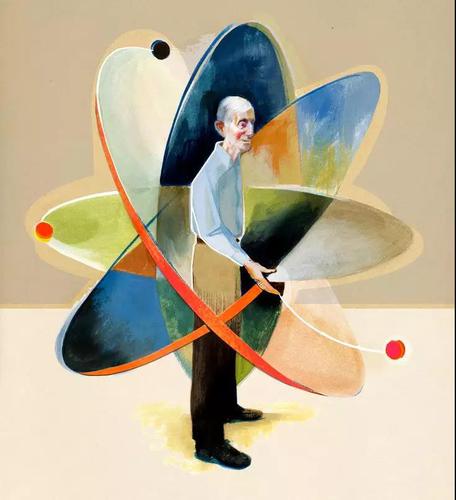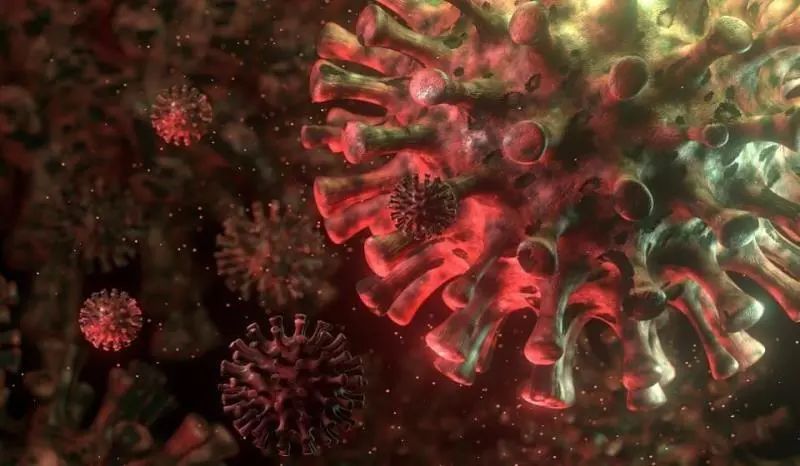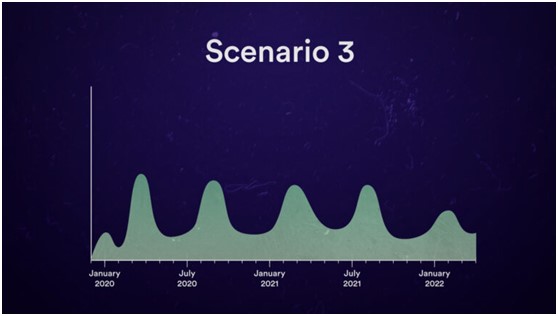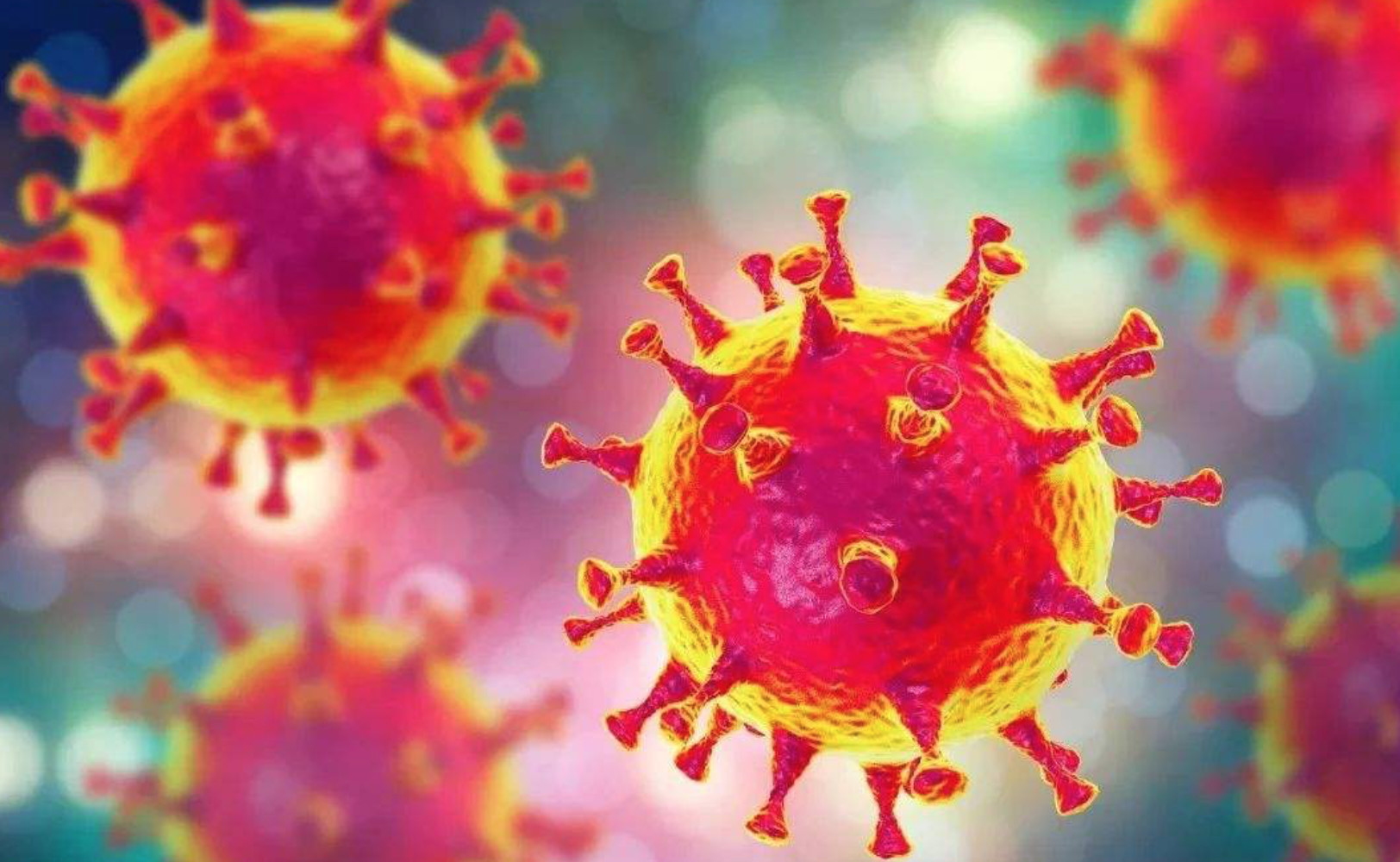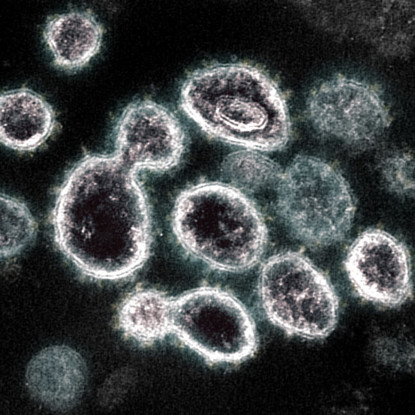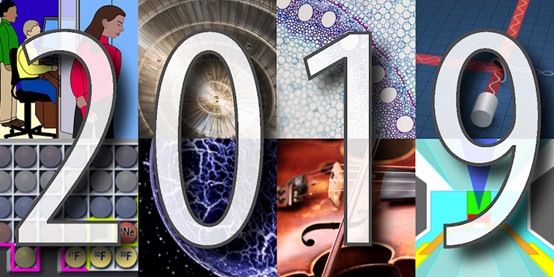戴森是科学界最伟大的圣贤之一,现年96岁的他曾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取得各项科学突破。如果你想了解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方向,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或许是你可以请教的最佳人选。
20世纪许多物理学巨匠都是他的朋友和同事:汉斯•贝特(Hans Bethe)、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
戴森在英国长大,从小擅长数字和计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与英国皇家空军合作,确定了在德国的轰炸目标。战后,他搬到了美国,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
和那个时代的诸多科学家一样,对原子弹的兴趣帮助他开启了物理学的职业生涯。后来,他梦想建造一支由核弹驱动的宇宙飞船舰队,环绕太阳系航行。
戴森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书写了他60余年的研究生涯。现如今的他虽然不再活跃,但仍紧跟着科技发展。他认为那些从一个研究项目跳到另一个研究项目的科学家能获得更多乐趣。因为他自己就乐于对宇宙不断解密。迄今为止的物理学未能统一恒星的经典世界和原子的量子世界,这在我们看来是遗憾,但在戴森眼里却是乐事。
以下是史蒂夫•保尔森(Steve Paulson)和弗里曼•戴森的访谈对话。在保尔森提出的近二十个问题和戴森的回答中,我们窥见了这位科学巨匠的生平,和他同时代的那些巨人们的剪影,以及他对宇宙、人类和世界的态度。
小时候,你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科学家或数学家吗?
没错。当时我更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数学家,不过我读了很多优秀的科普书籍。我读过阿瑟•爱丁顿(Arthur Eddington)和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当然还有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G.Wells)的作品。这些书籍使科学具有吸引力。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我大概8岁左右时,读到他的著作《赫克托•塞瓦达克》(Hector Servadac)——内容是关于一个星球的探险,当时我以为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当后来发现这只是一个故事时,我感到非常失望。
你上大学为什么要学物理呢?为什么不继续学习数学呢?
部分原因是原子弹。战争期间我一直在英国。我们对原子弹一无所知,然后突然间,广岛被投下原子弹,战争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激这些以某种方式结束了战争的物理学家们,我认为了解这些人以及他们在做什么是很有趣的。
有科学家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吗?
有啊。其中之一是霍尔丹(J.B.S.Haldane)——著有多本畅销书的生物学家,他也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我在剑桥大学结识的人——哈代(Hardy)、利特尔伍德(Littlewood)和贝西科维奇(Besicovitch),都是伟大的数学家。他们大部分业余时间都在打台球。贝西科维奇有一张很棒的台球桌。幸运的是,我父亲在我小时候买了一张台球桌。所以在剑桥我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小圈子。如果我想和伟大的数学家交谈,我就会和他们一起打台球,然后话题就会转向数学。
二战后,你到康奈尔大学读研究生,后来和物理学领域的一位杰出人物汉斯•贝特(Hans Bethe)一起工作。他是你的导师吗?
是的,我非常喜欢他,他是非常棒的导师。他和学生相处得很好。他有很多学生,他总是为每个学生找到恰当的研究问题——刚好有足够的难度,但又不是太难。他是一个理想的导师,教给了我很多。
当时你的研究问题是什么?
是关于量子分子动力学的,在那个时候该研究领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哥伦比亚大学的一组实验人员一直利用他们在战争期间开发的工具研究氢原子。这个工具就是微波,它是精确研究量子力学所需要的。
威利斯•兰姆(Willis Lamb)是首席研究人员,他非常精确地测量氢原子的能级。结果证明,标准量子理论给出了错误的答案,所以需要一些新的东西——贝特知道究竟需要什么。如果你把原子辐射场的反应加到量子力学研究中,就会有正确的答案。
贝特有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做一些非常草率但大致正确的简单计算。然后他给我的任务就是做这种计算,我计算出了更准确的结果。
然后你遇到了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和他一起研究量子电动力学。
我从未和费曼合作过,但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
当时,他是个年轻的教授,而我只是个学生,所以我听从费曼的教导。当然他是个天才,也是一个极有表演欲的人,所以他总是需要观众。我很高兴能成为他的观众。
费曼与其他科学家有什么不同?
他极具独创性。他有一套自己与众不同的科学研究方法。这也是别人与他沟通有困难的原因。
大多数物理学家都会写下一个方程,然后找到解,但费曼不是这样做的,他只写解而不写方程。因为他用图像而不是方程来思考问题。他脑子里有很多图像,然后他在纸上画出来,但没有人明白是什么意思。我的工作是把费曼的语言“翻译”成其他人能理解的语言。
当时普林斯顿有很多著名的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他也没有鼓励年轻人去认识他。他从不参加研讨会,也从不与人一道吃午饭。我们总是看见他每天经过,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每天找他的人络绎不绝。重要人士来拜访他,所以他没有时间和年轻人们打招呼。
但听起来他好像不想打招呼。与青年科学家交流难道不是他事业的一部分吗?
的确不是。他不喜欢教书。对他来说有两件重要的事。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他一直在继续着,然后就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公共活动,他做得非常好。在国际事务中,他是一名非常认真的参与者,而且发挥得很好。
你刚来普林斯顿的时候,对爱因斯坦有什么看法?
当然,我非常钦佩他——无论是作为科学家还是公众人物。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我们也认为他有很多地方做得不合适。他对科学领域正在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就我们而言,我们没有什么可向他学习的,他可能对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经常拜访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你认识他吗?
认识。玻尔和爱因斯坦年龄相仿,但完全不同。我与玻尔的联系要密切得多。他和每个人都有交流;他对什么都感兴趣,见多识广,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他绝对是我们物理界的一份子。他来参加研讨会。他和我们共进午餐。我们和他有很多互动。
还有其他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曾任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你认识沃尔夫冈•泡利(Wolfgang Pauli)吗?
我和他很熟,我们俩是在瑞士认识的。他是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首席教授。我在苏黎世住了半年,所以每天都能见到他。我们成了好朋友。他喜欢午饭后散步,他通常会邀请我一起去,所以我和他谈了很多。他有很多故事,也是一个很有表现欲的人,而且心态非常年轻,跟上了年轻人的步伐。
是什么使泡利成为一名与众不同的科学家?
他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说话尖酸刻薄。每个人都害怕他。他几乎对每个人都说过些难听的话。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上。他和一群人谈论刚刚来到瑞士的朱利安•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施温格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青年才俊,做了一些非常出色的工作,甚至可以和费曼相匹敌——他们两个都是天才。
泡利的意思是,施温格讲的所有这些都是有道理的,而不像戴森一直在写那些废话。就在那时,我和我的朋友马库斯•菲尔兹(Markus Fierz)走了过来,他也是一位瑞士科学家。菲尔兹眼睛一亮,走到泡利面前说:“请允许我把你介绍给我的朋友弗里曼•戴森。”泡利说:“哦,没关系。他不懂德语。”我当然懂德语。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是朋友。
你还认识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后不久来到普林斯顿。我听说他是一个真正有天赋的领导者,至少在他主持曼哈顿计划的时候是这样,而且他可能是一个很优秀的管理者。这是真的吗?
我也说不清楚是不是真的。他在科学上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黑洞理论。他真的发现了黑洞,而黑洞后来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那是1939年他和他的学生哈特兰•斯奈德(Hartland Snyder)一起发现的。他们提出了黑洞理论——黑洞存在的原因,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奥本海默把相关一切都搞清楚了。从本质上说,他是黑洞概念的鼻祖,他关于黑洞的预言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令人遗憾的是,奥本海默的这篇论文发表于1939年9月1日,也就是希特勒进入波兰的那一天。所以全世界都在关注波兰,而不是奥本海默。
那篇论文不知怎么就被遗忘了,奥本海默本人也对它失去了兴趣,后来再也没有回过头去看它。它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了,这真的很遗憾。他本可以用它做更多的事,但可惜20年后一切都得重新做。他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奇怪的是,他所做的真正伟大的事情并不是他想做的。他想研究粒子物理学,对天文学不感兴趣。但不管怎样,很多事情都是命里注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因为什么而出名。
我们在物理学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有恒星和行星的经典世界,然后有原子和电子的量子世界。没有人能够把这两种现实结合在一个理论模型中,这让你感到困扰吗?
对一些人来说确实会感到困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更喜欢两个宇宙而不是一个。我认为经典世界是真实的,量子世界也是真实的。最美妙的事情是,即使它们完全不同,也能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喜欢这种不同。我一直希望它们不会统一,但大自然最终会做出决定。
这些年来你结识了许多伟大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是否具备某些共同的个人品质或智力特征呢?
这很难定义的。他们都是不同的。我想说的是,当他们老了的时候,他们有点变得疯狂的倾向,让人有种失去平衡的感觉。而这正是玻尔与众不同的地方,他一直保持着他的平衡感。
你需要冒着名誉受损的风险去追求疯狂的想法吗?这是取得重大突破的原因吗?
首先,无知是有帮助的。我研究做得最好的时候就是我最无知的时候。知道得太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如果你已经教了几年书,事情就会在你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你不可能跳出框框去思考。我很幸运,没有上过任何物理课程就投身于物理学。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
伟大的科学家天生具有颠覆性吗?
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为了创造新的东西,你必须摧毁现存的一切。当然,你需要好的直觉,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摧毁”,那是无济于事的。
你认识很多研究原子弹的人。洛斯阿拉莫斯的许多人都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然而,一个深刻的讽刺是,他们的工作造成了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破坏。
的确如此。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我一生都在努力处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我不做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也在担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是长期存在的,而在20世纪30年代时尤其糟糕。
战争让我们自相残杀,但我也发现,多元的文化和语言是我们社会的基础,这本身是非常好的。正是这种多样性使人类如此富有创造力。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协调。
本文作者史蒂夫•保尔森(Steve Paulson)是威斯康辛公共广播电台全国联合节目《据我们所知》的执行制片人。著有《原子与伊甸园:宗教与科学对话》一书。
资料来源:
My Life With the Physics Dream Te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