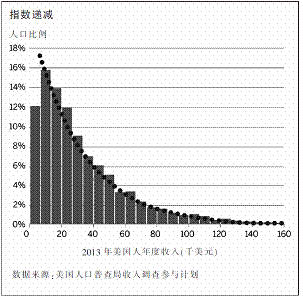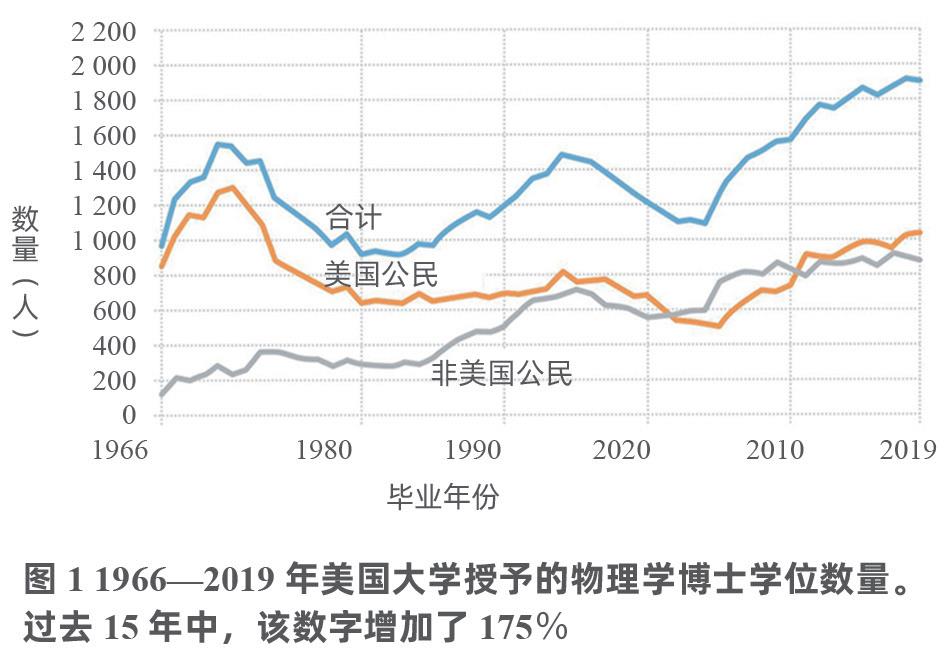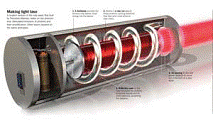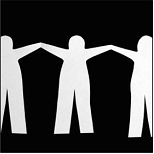无需谴责农业,“不平等”在资源富集的狩猎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庞贝壁画里1%罗马富人的美好生活
公元79年,被维苏威火山毁掉的庞贝城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里上演着“双城记”:一边是最富有的家庭坐拥多层的海景大厦,奴隶成群,其中有一座比半个白宫还要大。他们在装饰着昂贵壁画的餐厅用餐、在花园中漫步、在私人浴室中沐浴。另一边,超过1/3的庞贝家庭迫于生计,住在作坊后面的货仓、黑暗的维修间和小房子中。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这样的经济差距在罗马帝国时代很平常,公元二世纪中后期,1.5%的贵族家庭掌握着20%的经济收入。
不平等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然而如果以现有的传统社会为导向,我们采集狩猎的祖先通常主张平等主义,当时社会的一些成员是何时,又是如何开始聚集财富的呢?
长期以来,农业为不平等的蔓延饱受诟病。根据来自近东的研究证据,研究人员认为,最早的精英阶层出现在10 500年前之后,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成功地种植作物、驯养家畜,并定居在大型的永久村庄里。这种观点看来,农业生产带来了产品剩余,出现的管理者、工匠和专业人才,最终得以控制这些额外的资源。
目前,对考古遗址的分析以及传统社会民族志研究正在刻画一幅更复杂的图景,表明一些古代狩猎者通过控制被集中的散在猎物积累财富和政治影响。是这种小型的资源丰富地区的所有权――使得他们繁衍后代相对容易――培育了不平等,而不是农业使然。
从平等主义向经济竞争和不平等成为社会常态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近250万年来最关键的分水岭”,加拿大西蒙佛雷泽大学考古学家布莱恩·海登(Brian Hayden)说,随着时间流逝,它为“酋长权利、国家和最终的工业帝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前农业社会
考古学家已经在地中海东部纳图夫人,第一批向农业进行漫长跃迁的原住民那里找到了不平等的一丝线索。大约从14 500年前开始,纳图夫人依靠丰富的食物资源,部分时间可以在小村落里定居,靠野味、水果、坚果和野生谷物充饥――这种生活方式最终走向农业。
纳图夫人给考古学家留下了不平等的遗迹。两位考古学家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的T·道格拉斯·普赖斯(T.Douglas Price)和哈佛大学的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调查了25个大约在15 000―8 000年前纳图夫人遗址的出版报告,他们寻找着不平等的考古学标准标记:墓穴在大小、陪葬品和死者饰物上的差异。在10 500-8 200年前,不平等的标记变得寻常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早期的农民已经开始播种培植的单粒小麦和其他作物,饲养驯化的绵羊和山羊。
普赖斯和巴尔-约瑟夫在2010卷报告中提到,在14 500-12 800年前,虽然早期的纳图夫人仍然狩猎和采集,但初期的不平等信号出现得比这要早。一些早期纳图夫人遗骸装饰华丽,其他绝大多数则并非如此。例如,8%的富有者佩戴饰有从400公里之外进口或贸易得来的象牙贝之类海洋贝壳的项链。在一处遗址,三具男性遗骸的随葬品为象牙贝冠巾,流苏边饰镶着贝壳――暴富者的炫耀令人印象深刻。
调查结果显示了人们是如何在通向不平等的道路上迈开尝试性第一步的。纳图夫人生活在物质充裕的环境中,森林里密集的小块土地上,野生作物生长茂盛、猎物众多。普赖斯指出,纳图夫人显然“正在收获大量的野生作物,完全有理由进行谷物储存”。他认为,这些被储存的野生谷物剩余给一些纳图夫狩猎采集者带来了超过其他人的优势,“这些剩余允许人们通过赠送食物进行操纵,建立起支配行为。”
持有财富
其他充足的耐储存的野生食物也会带来盈余,这些自然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推进不平等,生成一种新的“反平等主义”的采集狩猎者社会。
以加拿大西北高原凯特里溪一个古村落为例,在2 500-1 100年前之间被采集狩猎者占有,这个村庄有超过115座房屋遗址,残存着原木和瓦屋顶的半地下结构,呈现出多达1 500人的峰值人口。西蒙佛雷泽大学海登领导的考古队发现,房屋尺寸呈戏剧性的大小不一,建筑面积从微型单间到类似当前中等尺寸房屋大小。
为了理解这种差异,海登和他的同事调查了这个地区历史上著名原住民社会的民族志档案,原住民被划分为贵族、平民和奴隶。地位最高的家庭拥有一定的资源并传递到下一代:猎鹿用的陷阱栅栏,特别是延伸至佛雷泽河中的捕鱼礁石,与世界上最丰富的鲑鱼群洄游相遇,拥有者凭借这些礁石搭建捕鱼平台,可以在大鲑鱼群游过的深水区捕鱼。地位较低的家庭只能沿着河堤的公共区域用抄网捕鱼,也只能捕到一些小鱼。最后,每家每户把捕到的鱼风干储存起来。

罗马人时代,精英们开始囤积黄金聚集财富
为了弄明白这种资源的私人所有制有没有适时拓展,海登的团队分析了大小不等的房屋遗址里的鱼脊骨,大房子中差不多75%的鱼骨来源于4-5年生的丰腴的大切努克鲑和红鲑,两处最小的房屋中100%的鱼骨来源于很可能是沿着河堤捕捞的2-3年生的鲑鱼。
调查结果显示,凯特里溪的不平等大约始于2 500年前,当时一些野心勃勃的进取之士靠着鲑鱼的馈赠进行资本积累,海登说。希望比邻居们获得更多食物的扩张者很可能在关键的捕鱼石上建立捕鱼平台并声称私人所有权。这些扩张者掌控着比别人更多的食物盈余,没有人阻止他们――因为当时食物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充足的,海登说,“从人类学上来说,巨大的不平等在西北高原多产的、能带来巨大盈余的捕鱼点产生绝非巧合。”
海登和他的团队还在凯特里溪大型烧烤坑遗址发现了一些证据,其中一个大到足以为500人烹调食物。这一证据显示凯特里溪的扩张者组织了类似历史上著名的夸富宴一类的宴席,在宴席上,酋长鼓动他的部落生产丰富的食物,获得象征名望的象牙贝之类的物品,这是人们所珍视的:他们从300公里以外买到这些贝壳,佩戴或者赠与竞争对手部落。这些公开举行的宴席体现了主人的财富与权力,或是与竞争部落的抗衡。夸富宴的客人们预计会献上价值更高的酬谢礼,准备不出礼物的家庭也会举债为之。
2011卷出版的一项名为“猜猜谁来参加晚宴:欧洲和近东史前社会的宴会礼仪”的研究,海登主张纳图夫人村庄里的精英也会采取相同的策略。像普赖斯一样,海登认为,在农业社会远未到来之前,纳图夫精英可能已经开始通过占领阿月浑子小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聚集地,或者通过建造捕猎瞪羚追逐线路来积聚大量的食物盈余。在一些纳图夫遗址上的烧烤坑和灶台也表明了这种宴席的传统。

在加拿大Keatley Creek,精英通过控制丰富的资源崛起
一些研究者认为,海登过分强调了进取的、有竞争力的个人在不平等起源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人口和资源压力所扮演的角色。米苏拉市蒙大拿大学的考古学家安娜·玛丽·普伦蒂斯(Anna Marie Prentiss)争论说,在加拿大其他一些西北高原的古村落中,是食品短缺而不是富足导致了不平等。她的团队挖掘布里奇河遗址得到的数据显示,第一批精英出现在鲑鱼洄流衰落的1 200年前,村庄人口骤然下降。这一报告发表在12月份的在线《人类考古学》期刊上。他们发现有些家庭通过封锁打猎和捕鱼的公共渠道应对稀缺,并在他们所剩无几的家中举办宴席,吸引人工,允诺他们将比邻居们获得更多的食物。布里奇河遗址的不平等,普伦蒂斯说,“是经济困难时期养活家庭的副产品。”
普伦蒂斯的发现提出了凯特里溪的精英到底何时出现的问题。西蒙佛雷泽大学凯特里溪考古研究项目主管苏珊娜·维尔纳夫(Suzanne Villeneuve)和她的团队开始对新的房屋遗址进行挖掘和分析,以重估遗址数据。但是海登坚持他的狩猎文化历史观,不管是加拿大还是海外,进取者构建剩余、积累财富物品,在食物丰富时举行宴席。“在食物短缺时,没有人能容忍他人囤积,”海登说,“多数人简单地获取其所需,仅因为生存取决于它。稀缺只能导致叛乱和更平等的需求。”相比之下,在好的时代――例如在中国这样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人民显得对不平等更加容忍。
为何富者愈富
研究加拿大西北地区的考古学家们探索着财富的起源,另一些研究者论证着如何一代一代地传承,形成永续的不平等。圣达菲研究所经济学家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研究人员莫尼可·博格霍夫·穆尔德(Monique Borgerhoff Mulder)领导了一个国际团队研究四种类型社会的继承机制:采集狩猎者社会、牧民社会、手工园艺师社会和运用农具及有机肥提高产量的农学家社会。
根据世界各地21个群体的历史学和人种学数据,该团队验证了三种财富:物质财富如不动产、表现性财富如体力、关系财富如个人社交网络中的人数。他们对每种类型的财富有多少可以传承进行统计分析。“我们对个人和其儿子们拥有的牲口数量进行计数;对其他形式的财富,比如猎人的握力可以用前臂的强壮度衡量。”鲍尔斯说。
他们发现,只有物质形式的财富,例如土地和牲畜可以很容易地传给下一代。“我可以把我的牛群传给儿子们,但是如果我有一些表型特征也在收入中占一些比例,比如身体强壮,就不太容易传给后代。”鲍尔斯说,其团队的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2009年《科学》上,并在《当代人类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文。
研究团队在园艺师和农艺师中间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差异。园艺师,在较为广大分散的土地上种植作物,在所有形式的财富传承上得分略高于采集狩猎者。这意味着仅仅农作物的驯化并不足以激起持久的不平等,而农民们在稀缺的可耕地上实施集约农业,则很容易把财富传给后代。这些农民能够控制他们土地的获取,并把它们留给后代,鲍尔斯说。
他认为资源的集中度是解释在农民之间以及古代的捕鲑渔民之间不平等的关键因素。“这些自然状态中的社会恰好是同一种资源集中,使得农业在各地发展成为可能,”鲍尔斯说,“农业极大地提高了小块土地和少量动物的生产力。”拥有肥沃农田的人们变得富有并传承财富就有如神助了,部分是缘于土地的可控性。
随着农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更多的阶层。演变成世袭的酋长制,最终产生王国。酋长和国王致力于积累盈余、集中财富和权力。许多酋长在贸易线路上制造经济瓶颈,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西北大学著名经济人类学家蒂莫西·厄尔(Timothy Earle)发表在2011年《社会演进与历史》杂志上的论文中写道,领袖们向商人收取线路安全通行保护费,利用财政盈余雇佣专业士兵,巩固和拓展其统治。物质文明也变得日益复杂,衍生出无数种高度集中且易于传继的形式多样的财富,从铜锭到黄金珠宝。所有这些趋势导致了更高层次的不平等。
到了罗马人时期,贫富差距已是天壤之别。加利福尼亚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和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圣经研究学者史蒂芬·弗里森(Steven Friesen)用历史数据计算出罗马帝国的基尼系数――现代社会不平等的计量标准,从零开始的人人平等,到一为止的一人独大。2009年《罗马研究》杂志上的一组报道称,罗马帝国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43,接近2010年美国税前收入基尼系数0.49的水平。事实上,罗马帝国超级富豪的财富相当于如今亿万富翁的规模。罗马三执政者之一的马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的收入相当于现在每年进账10亿。纽约城市大学卢森堡收入研究中心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同事在2007年发表的工作论文中报道说,这还赶不上比尔·盖茨超过20亿的年收入。
当今的复杂社会,再也回不到采集狩猎社会的平等主义,但是史前研究仍然可以提供一些降低1%的调控方法,鲍尔斯说,随着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财富增长依赖于专门技能、社会技巧和网络化――这些因素在代际传播的可能比土地和股票组合要难得多,他说,“所以我认为从长远来看,更加平等的未来是可以实现的。”
资料来源 Scienc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