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考古学一直受到殖民主义残留思想的影响,认为欧洲一定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即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精致的史前艺术曾是四万年前“创造大爆炸”的源头。据推测,这种观点可能是被某种变化所刺激,而该变化给予了欧洲人先进的认知力,而后,这种认知力以某种方式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区。
现在我们知道这是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在对非洲和亚洲考古学的全新评价后表明,文明是一种深厚久远的积淀。而且,欧洲的“创造大爆炸”与基因毫无关系,很可能是人口激增所引起的一种文化产物。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过分受制于上述观点。四万年前,欧洲的艺术文明无疑是非常辉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人的优越感是与生俱来的,只不过这是一种有趣的经验事实,但值得我们进一步的探研:探究导致其产生的社会过程是什么?只要不妨碍事实真相,避免旧的偏见就是一个崇高的目标。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发现艺术的存在有着数十万年的历史。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很久以前唤醒了人类的创造性思维呢?
卡斯蒂略洞穴探秘
当我告别了明媚的阳光,走进位于西班牙北部阴暗的卡斯蒂略洞穴想追溯15万年前的时光。刚进入洞穴,就看到一堵高20米的废墟墙,这是洞穴居住者留下的遗迹,接下来的行程就犹如置身于迷宫之中。
第一个洞穴非常大,墙面上绘有欧洲野牛和鹿,但我此行的目的是想看一些更神秘的东西:一系列的抽象符号,似乎是一种石器时代的代码。当进入一个很小密室中,只见墙面上布满了线和点构成的大矩形抽象艺术画:一个由小圆点组成的大十字架,和另一个由两个矩形叠加后构成的十字架。这些画的几何形状非常复杂,像是在传递着某种信息。
与我同行的考古学家兼向导、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热纳维耶芙·梵佩金格尔(Genevieve von Petzinger),他此行的目的是将这些抽象符号进行编目,试图了解其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是什么促使早期人类用赭石在洞穴中画出这些图像?他们是否具备了和我们现代人同类的思想?梵佩金格尔为此花费了大量时间在研究他们的思维。”
大约1.5万年前,这些符号在临近“创造大爆炸”晚期被绘制出来(“创造大爆炸”约始于4万年前)。这一时期的洞穴艺术、首饰珠宝和雕塑等手工艺品得到了迅猛发展。作为过渡,这一时期曾被认为是一个认知改变的标志,亦或是人类基因突变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人类现代心智的形成。
然而,从西班牙到中国,从南非到塞尔维亚,这些分散于世界各地的考古遗迹似乎在暗示,人类运用艺术和象征主义符号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更久远。“这些遗迹对于考古界来说是一个震撼,因为你看到了原本不应该出现在那里的艺术。”梵佩金格尔说。的确,在卡斯蒂略洞穴中的另一处,其绘画甚至不仅仅局限于物种。当其他研究者发现并发挥他们的想象时,或许能从中解读出这些标志所蕴含的意思,诸如石器时代的秘密最终将被揭开。
一些发现正在改写着交互式地图上的人类历史。在二十世纪末期,关于远古祖先的思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之后在法国、西班牙洞穴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叹的艺术品,似乎向我们展示了绘画者拥有完全成熟的现代心智。这些远古的艺术家被认为是缺乏基本的工具来表达他们的抽象或象征性的想法。正如颇具影响力的人类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于1989年所言,在“大跃进”之前,人类几乎只是个“美化的狒狒”而已。
不过,认知飞跃理论一直不乏反对者,因为它的发生似乎远远滞后于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的时间――大约10万年前。如果人类的认知飞跃确实由欧洲的基因突变所引起,那么在澳大利亚、亚洲和美洲的人类与欧洲的亲属失联后,基因突变又是如何渗透到这些地方的?更简单的解释是,在离开非洲之前,我们共同祖先的智力就已经在进化。但这种观点尚缺乏证据。
“并非真正的变革”
伴随着南非布隆伯斯洞穴中一系列有趣的发现,上述观点亦开始发生改变。洞穴中的鸵鸟蛋壳手工艺品和用赭石绘制出的各种几何图形,在时间上似乎比欧洲“创造大爆炸”还要早3万年。鉴于这些早期发现,人类学家莎莉·麦克布里雅蒂(Sally McBrearty)和艾莉森·布鲁克斯(Alison Brooks)于2000年发表了题为“并非真正的变革”的文章,抨击了欧洲中心论的人类起源观。
抨击促使考古学家开始反思。在过去十年中,他们对之前的发现重新进行了评估,同时也有了一些新的发现。其中,在南非迪克鲁夫岩窟中发现的刻有不同几何图案的鸵鸟蛋壳,距今至少有5.2万年的历史;在以色列卡夫泽洞穴、摩洛哥“鸽子”洞穴中发现的大量贝壳,则表明早在8万年前就有人开始收集个人饰品了;而在中国北京周口店山顶洞穴发现的一些首饰,大概也有3.4万年的历史,这些都表明了世界各地的人类群体都曾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沟通和打扮自己。
上述这些发现表明,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其抽象思维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考古学家甚至质疑这些艺术品、符号是否是人类所独有的。毕竟,尼安德特人具有与现代人几乎同等规模的大脑,而对此缺乏足够的证据可能要归咎于这些物种的文化属性。“也许当时使用的是羽毛或植物色素,所以没有留下痕迹。”法国波尔多大学的弗朗西斯·德埃里克(Francesco d'Errico)说。
当然,有一些暗示让人不得不去猜测早期人类曾尝试过艺术创作。比如,在卡斯蒂略洞穴中的墙上分布着红色圆点、野牛和手印的轮廓,其中有一个红色圆盘图案,几乎被掩盖在一层不透明的方解石下面(该图案至少绘制于4万年前),这是迄今在欧洲确认的最古老的绘画证据。由于那时现代人刚刚抵达欧洲,一些研究人员推断这可能起源于尼安德特人之手。
类似的,在法国佩奇德莱泽遗址发现了大量的锰颜料,而该遗址曾是尼安德特人的居住点。这些颜料的形状像似蜡笔,推测可能是用来在人体上绘制图案。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他们极有可能会在墙上绘制图案。”南非金山大学的克里斯托弗·罕什伍德(Christopher Henshilwood)说。也许最终他们在壁画中创作出了复杂的具象艺术。
这似乎与在法国Grotte du Renne洞穴中的发现相吻合。尼安德特人曾经在该洞穴居住。2011年报道,发现该洞穴有大量的饰品,包括可能用作项链的穿孔牙齿、颜料以及装饰过的骨制工具。尽管有批评者指出,这可能是尼安德特人模仿智人制造出的人工制品。
甚至更遥远的直立人也可能是“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在以色列,研究人员发掘出了距今23万年的贝列卡特蓝雕像。虽然该雕像比较粗糙,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形状适宜的卵石,但微观分析表明,该雕像的颈部有专门的雕刻痕迹。若是如此,时间和地点表明这应该是直立人的手工制品。该观点迄今仍有争议。不过有传言说,我们可能有望看到已经灭绝的祖先在象征行为方面更加显著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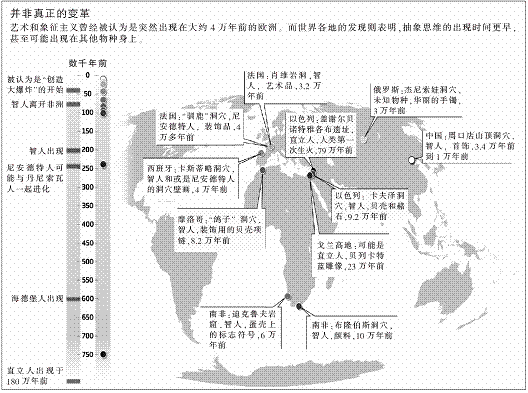
现代心智或出现在17万年前
目前,更多的与此有关联的证据也许可以充实我们的观点。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约翰·林德(Johan Lind)认为,一个行为或认知的改变要留下它的痕迹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总有办法会重现那个时期留下的印记。例如,研究人员通过软件来追寻不同生物体的遗传谱系,或根据考古发现和语言记录重现诸如婚姻等传统进化。
林德团队的研究非常广泛,涉及诸如FOXP2基因数据(该数据被认为与语言发展相关)、声道变化,以及火的使用和复杂工具等的考古线索,依赖于同样的“抽象”工具包,以循迹象征主义符号使用的缘由。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德团队估测现代心智至少出现于17万年前,或许早在50万年前的直立人就已经有了现代心智的雏形。林德说:“那些被看作是人类独有的特征深深根植于种系的发育之中。”
无论作出什么结论,很显然,早在我们的祖先离开非洲之前其抽象思维就已经隐约出现了。但这并不能解释“创造大爆炸”中关于具象艺术和神兽的秘密。是什么使我们的祖先从先前的努力中得到摆脱,大步跨越到错综复杂的创作中去呢?
一种可能是人口已增长到足够数量,从而以某种方式推动了创新。依据最近的研究,智人在刚抵达欧洲时就经历了人口爆炸。毕竟,先进文化是众多创新的综合结果,需要很多人通过历年的思维与创造汇聚而成。林德说:“创造一个新的文化,本身就融和了很多种文化。”就像林德所说的那样,如果上世纪七十年代将100名瑞典人带到月球上去,流行乐队“阿巴合唱团”恐怕就不会出现了(“阿巴合唱团”为七十年代瑞典最著名的流行乐队――译注)。
人口爆炸造就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环境,人们因此生活在更大的社会群体中,亦有着更广泛的社交网络。其结果产生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大,这就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创建一个共享的身份认同,用以协调更大的群体。德国图宾根大学的尼古拉斯·康纳德(Nicholas Conard)说:“这些象征性的行为艺术的发展是一种文化粘合剂,将人们联系在一起进行建设性的互动。”他在斯瓦比亚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发现了许多古代的手工艺品。“使用这些象征性符号的人在竞争方面往往表现得更好。”
理解这些变化甚至可以帮助我们重新解读这些艺术品的内涵。比方说,如果卡斯蒂略洞穴是不同群体的一个集会点,那么这种理解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解码洞穴墙上那些复杂的红色矩形图案。梵佩金格尔说,“它们的格式基本相同。开始是一个矩形,然后分割成几个部分,有的部分是交叉影线,有的是线或圆点;有的则是空白。”梵佩金格尔认为,不同的图案设置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家庭或群体。
在欧洲发现的洞穴中还包括其他不同形状的几何标志,梵佩金格尔正在研究。是否随着社会压力的增大,这些标志符号逐渐变得复杂,以此标记出不同的群体?她发现最早的标志往往不是按照特定的方式设置,但在约2万年前标志开始被组合在一起,例如,在参观椎瓜雷尼亚洞穴时,墙壁上画着排列整齐的三角图形。
迁徙产生了抽象艺术?
梵佩金格尔认为,这种行为上的变化可能与冰河期的气候有关。大约距今2.6万年到1.9万年前,寒冷的气候迫使人们向南迁移。突然间,人们彼此的居住点比之前更靠近了。也许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他们需要扩大自己的艺术词汇量。当然,也不能排除这些符号是被用来作为领地划分的标记,即一个新来的群体知道某个洞穴已被其他群体所占据。
同样,一种有争议的方法也许可以阐明旧石器时代那些刻在骨头和鹿角上的抽象标志――线条、V形图案和十字架。这些标志之前被解释为太阴周,或是一种统计系统。但剑桥大学的莎拉·埃文斯(Sarah Evans)从她建立的标志符号信息库中发现,这些符号通常与实际物体是一致的。例如,三个不同的线状群出现在“镘刀”上――一种用来打磨兽皮的骨制工具,但该图案从未出现在其他工具上。埃文斯据此认为,这种系统化的图案结构表明,它是人们彼此互相传递的一种传统。这种雕刻有可能是被用来计数的,但特定的图案结构也许对使用该图案的群体成员有所帮助。
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遇到了陌生人,他们携带的工具上面有类似的雕刻,你就会知道他们的背景与自己相似,可能会以相似的方式思考和行动,从而有助于彼此互动。埃文斯说:“社交网络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不敢说这些骨制工具就是那个时代的‘脸书’,但其开创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方式,使他们得以存活下来。”
当然,不同的因素驱使了不同地区的发展。德埃里克认为,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思维也在不断变化,包括洞穴壁画的兴起和衰落。“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模式。创新的出现或消失,主要取决于人类不断进行着的文化实验。”最近,他与罕什伍德一起建立了一个被称为“符号追踪”(Tracsymbols)的大型研究项目,研究气候是如何推动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行为创新,以及又是如何丧失的。例如,作为调查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探索7万年前非洲南部的气候变化是否使原本蓬勃发展的文化停滞不前。如果是这样,它可能类似于1.4万年前塔斯马尼亚岛发生的情况:海平面上升导致该岛与澳洲大陆分离,迫使岛上居民为了生存而放弃了创新。
近年来,我们对人类认知起源的了解有了很大提高,通过基因研究技术,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大的发展。康纳德说:“对此将不会有简单的答案。它会很复杂,但会更加使人兴奋。”
在卡斯蒂略洞穴里,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带有矩形标志符号的一个洞穴。远古艺术真的令人兴奋。廊道的墙上绘有一个红色的大圆盘――这会不会是路标呢?其他地方,岩层中刻着一个奇怪的直立野牛的雕像,当我们将火把贴近时,其轮廓似乎在洞穴中的墙上欢舞。一些研究人员解释说,这是一种皮影戏的形式。
最终,我从洞穴中走出,开车沿着海岸驶向毕尔巴鄂的路上,我突然想到,如果人类绘制抽象图案的能力没有不断得到发展,也许我周围的所有技术――我的车、手机、卫星导航系统都不会被发明出来。正如梵佩金格尔所说:“关于这些几何符号,还有很多的内容在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资料来源 Nsw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则 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艾莉森·乔治(Alison George),美国《新科学家》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