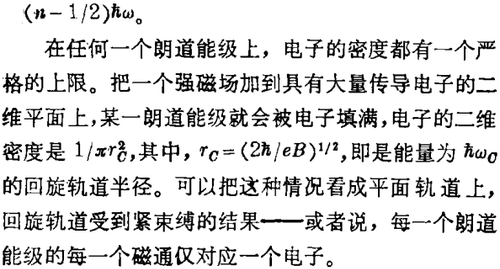瑞典皇家科学院把198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了斯图加特马克斯 · 普朗克固体物理研究所的一位主任克劳斯 · 冯 · 克利青(Klaus von Klitzing)。这项180万瑞典克朗(约合23万美元)的奖金是为了奖励他在1980年的重大发现——量子霍耳效应。冯 · 克利青曾经是海森伯在符兹堡大学的同事。量子霍耳效应是他在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与全德科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格勒诺布尔强磁场实验室发现的。
所谓量子霍耳效应,是指在低温条件下,二维电子系统受强磁场作用而出现的宏观量子效应。这一发现在过去五年里开创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实验和理论的活动领域。其惊人的重要标志是霍耳电导坪以e2/h的整数倍出现,而且其精确程度尤其令人惊讶,出乎理论工作者们的预料——还有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测量这一效应时,完全不用考虑半导体界面的缺陷和几何形状的不同。
冯 · 克利青在测量半导体载流子密度时偶然观察到电导坪现象,受到朗道填充理论的启发,他意识到量子霍耳效应可能开创一种精确地测量基本自然常数e2/h的途径,这样,人们就可以在与电子旋磁比完全无关的情况下,对这一精细结构常数作出更好的测定。量子霍耳效应不仅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一种量子电动力学的有力证据,也为应用物理学和工程技术部门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并很容易复现的电阻标准。以欧姆为单位,e2/h的值正好是25813欧姆。国际度量衡局IBWM正在考虑利用量子霍耳效应来重新定义欧姆标准。
冯 · 克利青还告诉人们,“在该理论中,e2/h是二维电导率的基本单位,但没有一个人认识到能够从霍耳效应去直接测量它——很可能,理论工作者们并不知道有一种测量霍耳效应而与样品的几何形状无关的方法。我的意思是说,要制造一种朗道能级完全被填满的样品,才能备行测量。”
就算是理论工作者们曾经考虑过上述的测量方法,但他们也无法预见到宽阔的电导坪的存在(它是今天才发现的),而与e2/h的误差几乎只有千万分之一。五年前,冯 · 克利青第一次发现量子霍耳效应的成果发表以后,他的同事哥哈持 · 多达(西门公司)和迈克尔 · 佩珀(剑桥大学)就抢先对下述情况给出理论解释:为什么测量某种充满缺陷的晶体界面时会得到如此惊人的与一个极其简明的理论精确地吻合的原因,根据这个理论可以很容易地忽略这些晶格缺陷。
冯 · 克利青看到霍耳电导坪的第一个迹象是在1978年,当时他正在测量载流子密度。起初,他认为这是一个无关重要、由样品而造成的效应。可是,当他注意到这种电导平台总是出现在同一值上时,他便开始将它与e2/h联系起来。后来,他把他的实验从格勒诺布尔带到符兹堡,并用精心校准过的标准电阻来检验这一效应的精确性。冯 · 克利青还说,他原先以为电导坪只是在百分之几的误差范围内与n · e2/h相一致。即使是在1980年他的报告发表时,他也没有预见到精确度竟高达百万分之一。
现在,那些对量子霍耳效应的数据已经理解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取得某些一致的见解。共同认为:晶体缺陷导致的电子局域状态正是所观察到的量子霍耳效应的关键因素,而绝不是起扰乱作用的复杂因素。理论工作者们还告诉我们,在完整的晶格的界面是肯定观察不到霍耳电导坪的。自从1974年次野 · 安多(东京大学)的理论提出以后(他理论主要是忽略局域性),人们就期望能通过霍耳电导率来测量填满朗道能级的电子密度。“但是,”利弗莫尔(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放射实验室所在地——译者注)的理论工作者罗伯特 · 劳弗林强调指出,“由于许多电子被晶格缺陷所固定,你绝不可能得到像测量量子密度那样的精密度。宽坪的出现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我们进行类似的测量都不受增添多少电子的影响。现在,我已确信,在量子霍耳效应中所测量到的只是电子自身的电荷。”
由于实验上的缘故,理论工作者们曾沉默了一段时间。1982年春天,贝尔实验室的丹尼尔 · 崔,豪斯 · 斯多默和阿瑟 · 戈萨德用一个稍有差异的装置重做了这一实验,除取得了和冯 · 克利青相同的结果外,还发现了某些很奇怪的现象——分数量子霍耳效应,这是量子霍耳效应在e2/h的非整数倍的延伸。它“把我们的下限都打掉了。”劳弗林回忆后这样说道。
分数量子霍耳效应给人们提出了一个比我们现在称之为冯 · 克利青整数量子霍耳效应更加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劳弗林继续说道,“在这方面,理论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已认为这是一种理论,但要进一步证实其正确性,我们还必须进行相当艰难的实验验证。”劳弗林的理论断言,人们在测量载流子电荷时,正如整数量子霍耳效应一样——在分数霍耳效应这种情况中,分数电荷处于被激发状态而产生奇异的量子流。
经典的霍耳效应是指在互相垂直的磁场和电场中,带电粒子向侧面漂移的现象。例如,把磁场垂直地加到载流导体上,洛仑兹力使运动的电子向导体的一个边缘聚集,并产生横向的“霍耳电压”,穿过导体的表面。在极端的情形中,例如在真空中,电子之间又无相互作用,则无任何损耗,只有在E×B方向有净运动。一般说来,电子以ωC=eB/m的回旋频率在回巡轨道上浇磁力线运动,而净运动是以“霍耳速度”E/B沿旋轮线的侧向漂移,平均值超过1/ωC好几倍。在无损耗碰撞的情况下,电场对电子不做功。
在量子霍耳效应中,当所有的传导电子都充满朗道能级时,即使在半导体晶体内部也会出现无损耗现象。在所有的量子霍耳实验中都包含有一个限制在界面的电子二维系统——在冯 · 克利青实验的情况中,当温度低于2K时,硅半导体中的反型层正好处于金属 - 氧化物 - 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的氧化物表面之下。低温条件保证所有的电子都处在硅表面所形成的势阱的基态。电子只能在反型层上自由移动。如果把一个磁场垂直地加到反型层上,这种基态就会被破坏,使电子进入朗道能级,就好像电子被送进了一个微小的回旋加速器平面轨道一样。一个电子进入第n阶朗道能级,它将获得一个回旋轨道的能量增量
对于任意选择的粒子密度和磁场,在低温情况下,所有底层的朗道能级都被电子填满,而某些最高朗道能级通常只是部分地被电子占据。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施加一个电场使反型层上产生电流流动,那么将看到一种不太引人注意的霍耳效应现象。电流将分为平行和垂直于电场的两个方向流动,其电导率可归纳为一个2×2的矩阵,它的非对角元素σxy即所谓的“霍耳电导率”,是电流密度除以相应的横向电场的分量。虽然,就像在对半导体试样进行详尽研究时测量其载流子密度一样,σxy可能还具有工艺上的重要意义,但由于它的复杂性取决于试样的自然本性和几何形状,我们只好放弃它。在通常情况下,它就显得不怎么重要了。
但是,冯 · 克利青所论证的,正是σxy实际上具有一种真正的最本质、而且不依赖于样品本身的性质,尤其是,当样品的最高朗道能级完全被电子填满的特殊状态下,σxy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上述情况——假定是在完整的界面上一一那么电流的流动必将是完全无损耗的。只有一种态,即未被电子填满的第一个朗道能级,移动的电子才能散射到上面去。但这样一来,就使得电子跃迁了一个hωC能隙,这在实验中所设置的低温和强磁场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很像是在真空中)。电子只是在平面上沿着垂直于某一电场的方向以“霍耳速度”E/B漂移。电流密度仅仅是第n阶被填满的朗道能级的电荷密度与霍耳速度之积的总和。再把它除以电场就可以得到霍尔电导率,略去对场力的各种依赖关系,就可以得出一个很简单的关系式:σxy=n · c2/h,它仅与基本物理常数有关,而与其他因素无关。剩下的问题是:在实际的有品格缺陷的界面(作为确定大量二维传导电子能量表面层的费米能级在此界面会出现奇点),人们将看到什么现象呢?
测量霍耳电导率的高精度是最直接的回答。冯 · 克利青在实验使用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MOSFET)是多达和佩珀所提供的有氧化物外罩的高迁移率的细长硅片(有多种几何形状)。在温度低于2K的条件下,让稳恒电流从源到漏流经长硅片(其典型的规格只有几百微米长)的表面变型层,用试探电极沿电流方向测量纵向电压降,并横过细长硅片测量横向霍耳电压降。在无损耗电流的情况中,σxy就是所测得的霍耳电阻的倒数。在符兹堡所做的实验中,冯 · 克利青采用了一个以布劳恩斯维格的联邦物理技术研究所所认可的标准检验过的10KΩ的参考电阻器来测量霍耳电阻,其结果非常精确。他测得的霍耳电导率精确度可达百万分之一左右。冯 · 克利青最初的发现是在格勒诺布尔强磁场实验室,使用的是一个强度为20忒斯拉的磁场。虽然在符兹堡只有强度为15忒斯拉的磁场可以应用,但这也可以满足这一系列高精度的测量了。
电导坪作为量子霍耳效应的特征出现在冯 · 克利青的实验中。实验的原理是:在一个恒磁场中,通过反型层里的传导电子数逐渐增多来填充各个朗道能级。要做到这一点,可以通过设置一个垂直于晶体界面的电场从而提高MOSFET管的栅压(栅压是用来给界面提供电场的)来实现。随着栅压的增高,二维电子的粒子数也连续不断地增长,费米能级也同时随之增大。当费米能级增大到填满某一个特殊的朗道能级时,霍耳电导率相对于栅压的增长,变成了平缓的不再有显著变化。而大概当第n个朗道能级完全被填满时,霍耳电导率突然拉平,形成一条宽带,即形成一个令人注目的平坦的电导坪,其值正好是n · e2/h,其精度可达千万分之一,直至电子开始填充下一个朗道能级,这个平台才有改变。
冯 · 克利青用各种各样的几何形状的MOSFET管重复了上述实验,没有发现结果有什么差异。当他改变纵向电压(沿电流方向)下降时,他发现,如同前面的理论预言的一样,每个霍耳电导坪之间纵向电阻下降几乎等于零。这就是说,当所有的朗道能级都被电子填满时,电流流动基本上没有损失。
此后不久,贝尔实验室的崔和戈萨德重复了冯 · 克利青的实验,但他们不用MOSFET管,而改用掺有GaAs/AlGaAs的异质结半导体器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他们的实验中,尽管界面上的运动电子被AlGaAs层的掺杂以及界面的导带限制在界面内,但实验的结果仍不变。因此,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小组不是改变栅压,而是改变附加磁场来改变朗道能级的填充状态。当磁场强度增加时,对于一定的粒子数,其回旋轨道变得更紧密了,这样,这个最大值便允许每个朗道能级上的粒子密度也相应地增加了。
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量子霍耳效应,GaAs异质结比Si-MOSFET管具有多方面的优点。因为在GaAs异质结中,电子的有效质量更小,每两个朗道能级之间的能隙与更加接近。因此,在较低的磁场强度(8T)和较高的温度(4K)的条件下,仍能观测到量子霍耳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在GaAs异质结上,其界面可以变得非常清洁。紧接着第二年,崔和斯多默在贝尔实验室发现了分数量子霍耳效应。但是,只有采用戈萨德和詹姆逊 · 黄所提供的非常整洁的异质结,才能观察到。由于这一偶然的发现,崔,斯多默和戈萨德被授均1984年奥利弗 · 巴克利凝聚态物理学奖。
在这一理论中,由于冯 · 克利青发现了阶梯似的霍耳电导坪而出现了一个难题。在每一个朗道能级上的电子可沿着霍耳场的等位线移动。在没有定域电子态时,所有的电子都被安排在各个朗道能级上,费米能级从一个朗道能级直接跳到另一个朗道能级,同时霍耳电导率仅仅在单个点上才等于n · e2/h。也许,电导坪的产生是由于晶格缺陷而产生的定域电子态使费米能级暂时被牵制在两个朗道能级之间。但是,如果认为这是由于杂质所引起的,那么应如何解释电导坪这个惊人的千万分之一的精确度?
在冯 · 克利青的发现之后,马里兰大学的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 · 普兰奇把晶格缺陷作为一个简单的、很强的δ - 函数散射体来处理,以此来解释量子霍耳效应的高度精确性。他断言,既然局部不纯状态并不从朗道能级带走电流,那么朗道能级所扩展的电子态正好是这些失掉的载流子的精确的补偿,它们所载的电流刚好保证了量子霍耳效应的精确度。
然而,他的计算结果对模型依赖性太强,而且他的模型又不切实际地忽略了电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朗道能级的扰动。不用赘言,一个如此普遍的现象必须由一个更普遍的原理来解释,劳弗林已经提出了一个不依赖于模型的方法来解释量子霍耳效应。劳弗林的理论是,最重要的根据就是规范不变性,目前看来,这比较能反映在这一领域工作的理论工作者们的一致见解,假定有一个头尾相接的封闭的环形体,在其上面有一股二维霍耳电流流过一个长导体片,此导体片又紧绕成一个电流圈,并让磁力穿过该电流圈。劳弗林问道:每一次绝热的增加一个磁通量子,将会发生什么现象呢?被限制在电流圈上所扩展的电子态将使由磁通增加而产生的电流再增大。但是由于这些电子态本身由于位相相干而互相依赖在一起的,因此,随着磁通的增加,这些磁通量仅能以整数个电子数从导体的一边传递到另一边。这样,就使冯 · 克利青的量子霍耳效应有如此高的精密度。其实,霍耳电导率从根本上说,测的就是电子的电荷。另一方面,局域的电子态在规范不变条件下可取任意位相,因此对霍耳电流无任何贡献。“在朗道能级充满之后,再增加电子就再没有什么作用了,”劳弗林解释说。“它们受到局域态的碰撞。'如果没有晶格缺陷造成的局域态,我们就根本看不到任何效应。事实上,量子霍耳效应就是局域态理论最重要的推论,这种局域态我们早已发现了。”
贝尔实验室的塞奇 · 路易和鲁道夫 · 凯赞里诺夫提出一个越来越诱人的深层渗透模型的解释理论,在他们的理论中,扩展电子态与局域电子态两者之间的区别仅具有拓扑学上的意义。两种函数都可认为是波函数沿等位线方向的延长线,但这样说仅仅是拓扑学上的“球形”状态,即它们就是全部所施加的电压。正如费米能级随着晶格缺陷所造成不均匀的势平面的改变而逐渐增大一样、这电导坪是由于地貌的拓扑形变而产生的,正如“陆地上的湖泊变成了海洋的岛屿”一样。路易还告诉我们,这种模式的优点之一就是,它并不需要高密度的晶格缺吃和完全的局域态,就解释了电导坪的成因。
可惜,在整数量子霍耳效应方面所做的理论工作未能给随后发现的分数量子霍耳效应以任何一点提示和说明。
冯 · 克利青认为,“我们仍需要寻找一个关子整数量子霍耳效应的微观理论。”他现在正在斯图加特马克斯 · 普朗克研究所从事薄层和量子阱现象的研究,他所采用的试样大部分是砷化镓(GaAs)异质结,虽然他本人并不参加培育这些异质结的工作,但他去年(1984年——译者注)冬离开慕尼黑工业大学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斯图阿特有分子束注入的设备。(他加入慕尼黑物理学会是在1980年他做完的历史性的实验之后。)
冯 · 克利青1972年在符兹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根据他发现量子霍耳效应,德国物理学会在1981年把固体物理研究的沃尔特 · 斯科特基奖授予他。“半导体物理学再一次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认可,对此我非常高兴,”他还告诉我们,“我希望这将导致——至少在德国——对固体物理学领域更多的支持。在德国还没有哪一个公司像人们所熟悉的贝尔实验室或IBM公司那样从事基础研究,仅有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和某些大学的一些小组在从事这方面工作。”关于斯图加特是否可能成为新的“硅谷”,他说道:“他们正在努力,但还无法做出结论。”
[Physics Today,198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