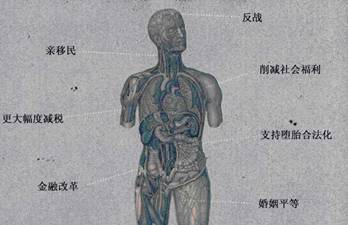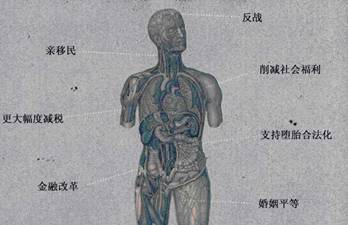政治倾向的形成是否与生物学因素有关,比如基因和激素水平?综合迄今的研究成果,无论在关于基因或环境因素是否能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的话题上,大部分研究依然是“不可知论者”。决定一个人对政治议题的看法,或许其反应已经植根于他们的生理机能之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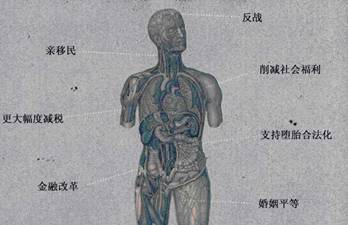
2012年初夏,一个政治广告开始流行,广告中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一群支持者发表演说,听众惊奇地瞪大眼睛,突然,屏幕变暗、配乐渐渐增强,其时诸如“恐惧和厌恶”“肉麻”“分而治之”等话语在屏幕上闪烁。随后,视频片段中有评论家抱怨说,奥巴马在使用恐吓战术以操纵选民。在最后的场景中,屏幕上出现奥巴马参加2008年总统竞选的海报,然而“希望”这个词已被“恐惧”替换……
这一广告由华盛顿保守组织“美国十字路口”制作,是一次典型的主导美国广播和YouTube视频网站的活动,意在为2012年总统选举造势。目前,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政治团体,其造势广告越来越俱恐怖色彩,试图触发选民的基本情绪如恐惧、愤怒、厌恶等,以此支配他们的抉择。
上述论及的竞选策略,正在印证着一项新的科学证据,即人们的政治信仰是如何形成的?政治学家过去认为,社会力量――主要是父母及童年环境――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倾向,致其成为保守主义或自由主义者,抑或参加投票或其他政治活动。“(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仅仅只有这些因素是不够的,”纽约大学心理学家约翰·约斯特(John Jost)说。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生物学对政治信念及其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生物学因素包括:基因、激素水平和神经递质系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人们对政治问题――社会福利、移民、同性婚姻或战争――的态度。精明的政客则利用这些生物学因素,通过巧妙地广告宣传以操控选民的情绪。
虽然把生物学与政治学联系起来的研究仍存有争议,并且难以重复,但是,证据的数量却在增加,这或许可能改变人们的看法:为什么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不一样?
“人们总是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感到自豪,”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翰·希宾(John Hibbing)说,“我们通常认为,政治信仰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理性反应。”但事实上,人们在认识和应对政治议题时,其基因组合和早期经历已预先安排好了某种方式。意识到这一点,有助于公众和政客更尊重那些反对的观点。希宾说:“我想看到的是,人们在减少对自身政治信仰偏执的同时,能理解他人对世界的不同体验。”
来自先天的意识形态
几十年来,针对基因疾病的研究成为了一种趋势,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酗酒等,以及性取向、教育能否取得效果等。但直到近十年,新的趋势主要是研究政治科学与人基因之间的关系。以前的观点认为,现代政治似乎与基本的人类生物学无关。然而,科学界最近提出了人类进化史上的创新观点:政治观点可能被遗传因素所影响。
1986年,尼古拉斯·马丁(Nicholas Martin)等人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出,基因能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产生影响,包括堕胎、移民、死刑、和平主义等。现为澳大利亚昆士兰医学研究院遗传学家的马丁,采用的是经典的行为遗传学技术,即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同一性别的异卵双胞胎(平均只有50%基因是相同的)。同卵双胞胎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前者具有更多类似的政治信仰。由于双胞胎一般生活在相同的家庭环境中,马丁研究团队因此认为是基因决定了思想的差异,即在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态度时,基因显然起到了关键作用。
尽管马丁的研究明显与政治学有关,但该领域的其他研究人员却将其忽略。20世纪初的优生学运动和纳粹有关生物学与人种差异的理论,使政治学家在涉及解释人们的遗传差异主题时格外小心。当初发表的论文“就像一块石头扔进深井,”马丁回忆道,“了无回应,一晃就是20年。”
然而在21世纪初,希宾和莱斯大学的政治学家约翰·阿尔福德(John Alford)了解到马丁当时的研究,为此他们重新分析了马丁的数据,并整合了美国双胞胎政治态度的类似资料。2005年,希宾和阿尔福德发表了论文,结论与早期结果相类似,显示了遗传因素与政治观点之间有着强烈的关联。这下终于引起了政治学家们的注意。然而,这种“注意”不是阿尔福德和希宾所期望的,“他们觉得我们是疯了,”希宾说。
不过,也有少数科学家(主要集中在美国)被上述结果所吸引,开始进行深入研究。比如,圣迭戈加州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采用双胞胎方法,以此阐明投票人数和政治参与度也与遗传有关。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帕克校区的政治学家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发现,来自澳大利亚、丹麦、瑞典和美国的双胞胎身上都有阿尔福德及希宾观察到的现象。
双胞胎研究的局限性
双胞胎研究结果远远不是决定性的,很大程度上此类研究不能完全控制环境因素。与异卵双胞胎相比,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更可能拥有观点相同的朋友,成年之后还保持着频繁联系。此外,父母、朋友和老师往往更平等地对待同卵双胞胎。究竟有多少基因和环境因素决定了同卵双胞胎政治信念的形成?一时很难得到答案。
相关的一些研究也在试图梳理多方面的影响。哈特米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即使同卵双胞胎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不长,仍然有比异卵双胞胎更多的一致性,说明遗传因素是多么地重要。然而,针对双胞胎的研究仍遇到了强有力的反对。“我很怀疑,双胞胎研究能否用于评估政治信仰的遗传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政治学家劳拉·斯托克(Laura Stoker)说,“这一理论框架是建立在一大堆假设上。我想看到的是,人们是如何减少对自身政治信仰的偏执。”
双胞胎研究也不能证实,即基因是如何左右人们在各种政治议题上持左或右的立场。对此,研究人员开始寻找其他候选基因。研究发现,与嗅觉系统、神经递质谷氨酸盐、多巴胺和5-羟色胺有关的基因都与投票热情及意识形态相关,或许这些研究结果已经通过检验,但尚未有独立的重复实验。
伊利诺斯州西北大学的社会学家杰里米·弗里兹(Jeremy Freese)表示,这些研究已经发现个别基因具有所谓的“难以置信”的强烈效果,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这些候选基因的方法是多么的脆弱。”
弗里兹认为,部分原因是特定基因与政治行为关联的研究论文通常发表在政治学刊物上,而不是自然科学刊物上,编辑和审稿人未必能意识到其研究的不足之处。“这些审稿人不了解,重复性是一大问题。”
纽约大学的政治学家克里斯多佛·道斯(Christopher Dawes)坦承,他研究的一些特殊基因课题很复杂,并认为采用与基因组相关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可能会得到更有启发性的结果。不过,这需要扫描大量人群的基因组,找寻与行为或特征相关联的序列。“我们逐渐认识到资料和技术的局限性,”道斯说。
如果其他某些复杂的行为或特征出现某种趋向性,其原因也不可能一言以蔽之。如身高这种特征,受到几千个基因影响,而其中每个基因的影响都轻如鸿毛。所以,似乎不可能有少量基因在推动某人成为自由派人士、社会保守派或自由意志论者。
大多数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过多的关注政治遗传学还为时过早。“眼前最重要的问题都还是谜团,继续前行没有任何意义,”阿尔福德说。
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可用于研究基因与政治倾向之间的联系。其中的一种联系便是人的个性。不过,很多政治心理学家认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划归为一项基本的人格特质:对改变持开放态度。自由主义者倾向于更多的接受社会改革,保守主义者则不然。一些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更能容忍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反之,保守主义者更加坚定、认真、讲究秩序。
理论上,对改变持开放态度的人易于支持同性结婚、移民和其他改变社会的政策,诸如美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政策;个性偏向有序和维持现状的人,则可能支持强硬的军力以保卫国家,取缔移民、禁止同性结婚等政策。但也有一些研究人员不认为个性和思想之间存在简单的联系。北卡罗莱纳州杜克大学的政治学家埃文·查尼(Evan Charney)认为,保守主义有时也会支持变革,比如在美国修改税法及福利体系中出现的问题。尽管查尼和其研究领域里的大多数人是自由主义者,但这种不平衡可能会造成他们对个性和政治之间联系的解释出现偏颇。
或许来自于本能反应
一些研究人员试图不局限于上述这些个性研究,转而衡量参与者的生理反应是如何影响他们对政治议题的反应。2008年,阿尔福德、希宾、哈特米等人检测了人们在面对威胁图片或噪音是如何反应的。通过测量皮肤电导,发现更频繁地眨眼代表更高敏感性,相比敏感性低的人,这些人更容易支持持枪权利、死刑和对伊拉克开战。
在另一项研究中,希宾显示了一系列令人情绪紧张的图片,包括人脸上的蜘蛛、爬满蛆的伤口、可爱的兔子和快乐的儿童。认为自己是保守主义的人,看到负面形象常有比正面形象更强烈的反应(保守主义者通常比自由主义者凝视负面图片的时间更长)。这让希宾联想到,保守主义者在面对可怕的或令人反感的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强大的军力及对犯罪者严厉制裁。
一些研究者正在探索激素与政治态度之间的联系。例如,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偏见与催产素――负责移情作用和爱情的好感激素――水平之间的联系。在一个实验中,吸入催产素的荷兰参与者对荷兰本国人更有好感,这暗示他们偏向自己的祖国。包括哈特米和罗德岛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罗斯·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最近正在研究,其他激素如睾丸激素和皮质醇是否与意识形态有关。但是,由于其样本量很少且报告所称的结果较为牵强,激素研究已经受到质疑。
综合迄今的研究结果,希宾在关于基因或环境因素(如父母教导)是否能够影响个人的政治行为的问题上依然是“不可知论者”。但不管怎样,这很难改变一个人对政治议题的看法,因为他们的反应已经植根于其生理机能中。
希宾表示:“一旦人们把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用来关注负面信息,他们很可能对世界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右倾人士不会通过论辩和左倾人士达成一致,反之亦然。
但是,情感的打击似乎更能改变人们的政治倾向。当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纽约人直接暴露于创伤事件中并经历了“转为保守派”的过程,表达了比从前更爱国、更支持军力和宗教的倾向。包括厌恶,也能转变人的态度。一项研究表明,当有其他负面因素提醒时,人们会表现出更保守的观点,例如,一瓶洗手液,一个标志,能够提醒人们去洗手或清除异味。
那么,设计恐惧、厌恶的负面政治广告能否改变人们的政治倾向?阿尔福德说,这些广告其目的在于调动有利于自己的选民投票。“从事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投票人数的意义,”阿尔福德说,“这不是改变人心,而是改变选举结果”。
无论生物学因素是否影响了政治选择,但它可能会影响一个人投票的积极性。在一项尚未公布的研究中,希宾发现,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高的人其投票积极性低于皮质醇水平低的人。阿尔福德认为,所有的这些研究,最大的影响可能是使政治话语更加文明,更能接受不同意见。“如果政治博弈中多几分人性化的色彩,那该多好!”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