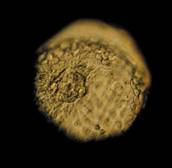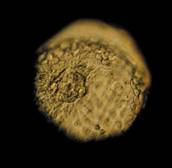各种咨询机构、科技组织和资助机构都十分关注人类基因组编辑,医学及伦理学研究者黛布拉·马修斯(Debra J. H. Mathews)、罗宾·洛弗尔·巴杰(Robin Lovell-Badge)及同行们对此提出了一些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基因组编辑的首要目标是人类胚胎
基因编辑工具CRISPR/Cas9的易用、准确和高效性使其在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而且在农业和涉及非生殖细胞(体细胞)的基因疗法中也有了初步的应用。CRISPR/Cas9及相关技术也可使用在某些司法领域,应用在人类生殖细胞(精子和卵子)及早期胚胎中。
去年9月,由三十多位科学家、伦理学家、决策者、杂志编辑和资助者组成的一个名为“欣克斯顿小组”的工作团队,聚集在英国曼彻斯特,围绕着人类基因组编辑在发展初期及生殖细胞应用方面,展开了相关伦理和政策问题的讨论。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已经召开或正在召开类似的会议。同时,一些组织机构发布了相关的立场声明。
在此,我们列举出“欣克斯顿小组”会议上的一些焦点问题,在未来的国际会议上这些问题有可能得到更多的关注。以下观点是由“欣克斯顿小组”的指导委员会提出的,不一定代表该组织内所有人达成共识。
世界各地的咨询机构在讨论人类基因组编辑相关的伦理和政策影响,此间出现了一些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列举如下:
在涉及人类精子、卵子和胚胎的基础研究中,是否应当允许使用基因编辑?
在基因编辑研究中,是否应当仅允许使用体外受精剩余的胚胎?还是应当允许培育胚胎专供研究使用?
在考虑将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生殖领域之前,需要在安全性和效能方面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如果上述安全性和效能方面的条件可以满足,那么我们又能够允许什么样的基因编辑应用于人类生殖领域?
建议措施
建立一个可被国际广泛采用的模式化监管框架 各种团体机构,包括我们“欣克斯顿小组”,一致认为在基因编辑技术切实可行地应用于临床生殖医学之前,有大量技术性、安全性问题需要解决。同时很多团体机构和我们一样,坚定地认为涉及基因编辑的基础研究不应当停止或受到阻碍。这些研究可能在诸多方面有巨大价值,包括不涉及基因组编辑的人类生殖应用,以及体细胞疗法的开发(参见图表“基本价值”)。
然而,国际科学界多数人和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赞助者都同意这一点,基因编辑技术的易用性和可及性使得其很容易被诈骗集团利用,尤其是在司法领域管制松散的生育诊所里。毕竟,在过去十年中,有成千上万的医疗游客不惜花费数百万美金,到国外去接受未经证实且不受管制的干细胞疗法。
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当建立一个模式化监管框架,该框架一方面应当足够具体,可以应对上述问题;另一方面,则应当广泛通用,能够被不同国家的监管机构所采用。对于这样一个监管框架,是有例在先的:由国际干细胞研究学会发布的文件,影响着国际范围干细胞研究工作的监管。但监管框架所提供的指导准则本身并不能阻止诊所进行未经证实的治疗方案,这属于当地政府的职能范围。例如《人类受精与胚胎学法案》以及名为“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HFEA)的监管机构,对于英国的研究及诊所中胚胎和配子的使用,设定了限制,一方面允许在研究和临床实践中使用,一方面对于那些越界的人则予以惩罚;两者之间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公众必须了解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当然这需要他们同管理机构、科学家和临床医师加强沟通。
为基础研究制订路线图 关于人类基因组编辑,虽然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一直是潜在的临床应用,但最直接、而且最激动人心的应用却是基础研究。咨询、监管机构应当为涉及人类细胞,包括种系的基因组编辑研究设置优先权。这应当包括游说世界各地的背景各异的科学家们,他们可能分属于下述各个不同领域的专家: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组学和人类遗传变异,突变类型、频率及其对身体和其他特征的影响,基因表达与调控,表观遗传学,人类胚胎和生殖生物学及临床遗传学。
在基础研究中,特别是任何与人类生殖应用相关的领域中,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
一个问题是脱靶效应。基于计算机的体外实验将需要用来评估靶位点之外引入变化的可能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若要将此种突变同自然突变(如细胞分裂或环境损害之后的不完善DNA修复)区分开来,也需要利用上述基于计算机的体外实验。
如果把基因组编辑应用于培养基中生长良好的细胞,如产生精子的精原干细胞,那么一个编辑的细胞则可以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其他细胞。通过对这些细胞的细胞亚群基因组进行测序,研究者可以获得脱靶效应的清晰指征。若只有一个或几个细胞是可用的,例如自早期胚胎起即被活检的细胞,那么上述分析则不够可靠。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从这些细胞中建立多能细胞系,由此将面临一个关键性的挑战:将脱靶效应从大量自然序列变异中区分出来,这些自然序列变异存在于个体细胞之间和细胞系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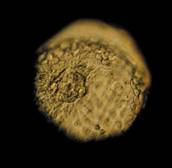
捐赠给拉霍亚体外受精诊所的胚胎是供美国干细胞研究使用的
最近对小鼠和人类细胞系的实验表明,与发生在每一代的自发性突变的数量相比,脱靶效应是无关紧要的。不过,突变发生的位置比突变的数量更加重要。与本质上随机的自发性突变不同,脱靶效应有可能受到核糖核酸(RNA)分子的影响,RNA分子可用来将具切割性的核酸酶引领到基因组的恰当位置。而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基因组编辑研究的实验对象都是基因同质种群,如近交系小鼠。究竟遗传背景的变异对基因组编辑的效率和准确性有何作用,对研究者区分脱靶效应与背景变异的能力又有何影响,我们仍知之甚少。
另一个问题是镶嵌现象。如果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多细胞胚胎,可能只有部分细胞会发生改变,导致出现已编辑和未编辑细胞的遗传嵌合体。即使把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一个单细胞胚胎,核酸酶可能不会切割靶基因的两个副本,或者在变化完成之前细胞可能已经开始分裂。对于基因组编辑的不同应用可能会出现何种级别的镶嵌现象?对此应该如何度量?镶嵌现象可能产生什么影响?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十分重要。
对于一些研究而言,如追踪细胞命运,镶嵌现象可能并不重要。(一些原样状态细胞只要携带了标记基因,如绿色荧光蛋白基因,研究者就能够识别这些细胞的未来变化。)对于其他研究而言,镶嵌现象可能意味着更多的问题。例如,如果研究目标是要确定一个基因的作用,该基因的表达产物是分泌型的,而分泌产物的总量对于基因功能来说是关键性的,那么未编辑细胞所占比例将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影响。
争取让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与讨论基因组编辑的研究工作,以及研究中对于人类胚胎的使用 尽管在国际上,人类胚胎、精子及卵细胞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类研究中,包括体外受精及胚胎干细胞的研究,有人仍然认为其在基因组编辑研究中的使用应当被独立看待。重要的是,若要避免镶嵌现象,体外受精所遗留的胚胎不太可能是一个好的模型,因为它们包含了一个以上的细胞;在它们达到或超出8细胞发展阶段之前,它们通常是不用于研究的。另外,大多数胎儿是由一个或几个早期细胞发育而来,而建立者效应会使得对镶嵌现象的功能性结果的预测变得复杂。细胞竞争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效应。例如,早期分析表明,一个胚胎中即使有80%的细胞被操纵,哪怕这些细胞在分裂率和存活率方面只是略有不同,最终的胎儿被证明包含的编辑细胞所占比例,同未编辑细胞相比要小得多。
减少镶嵌现象的效应需要引入基因组编辑工具――核酸酶和向导RNA――在受精之后,或者就在受精发生的时候。如果是这样,那么涉及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工作最终可能仅限于那些法律上允许培养胚胎以专供研究的国家。依据现行法律,研究仅限于以下8个国家:比利时、中国、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韩国、英国和美国。而且在美国,上述研究工作只能使用非联邦基金。
如果事实证明,人类基因组编辑的主要价值利益来自于基础研究,包括自身不涉及基因组编辑的应用。例如,如何改善生育能力或减少流产率,那么由于国家法律对相关研究工作的限制,可能导致人们无法获得这种利益。
设计工具及方法,使得人们可以进行包容性的、有意义的思考 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国家研究院等机构已具备条件,可发挥带头作用,以努力确保关于基础研究中人类胚胎使用问题的辩论在地理区域上与涉及人口上具有包容性,同时确保政府决策者了解该辩论情况。这对于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假设能够确保足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究竟什么样的临床应用是恰当的。
“欣克斯顿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涉及基因组编辑的基础研究,包括人类精子、卵子和胚胎,具有重大价值,但是他们也会因为讨论基因编辑在生殖方面的应用而被指控。实际上,如果没有一个特定情况的背景及客观事实,对于编辑人类生殖细胞系的可能的正当合理应用方面,我们发觉很难达成一致。“欣克斯顿小组”考虑了一系列的干预措施:校正可能致命的突变(例如突变导致泰萨克斯病,囊性纤维化和亨廷顿氏舞蹈症),引入预防性变更(敲除CCR5基因,以抵抗艾滋病毒感染)及非医疗强化(如增强肌肉质量)。在所列举的可能的临床应用清单中,关于各项的优缺点方面,我们甚至最终也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一些人担心,列举这样一份清单可能会被视为对上述干预措施的默许。
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些问题:人类生殖细胞系修改的利与弊;如何区分医学治疗与强化;对于孩子的生命,父母拥有何种权力......然而,如何能用多元化视角来规范调整颇具道德争议的新兴科技领域,很难找到可行的模式。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于2009年发布了胚胎干细胞研究准则草案,之后有将近5万人提交了评论意见。这些人当中有很多都是非科学人士,其中有1万6千人基于道德考虑反对胚胎干细胞研究。当看到自己的反对意见并未能阻止最终准则的颁布,干细胞研究的反对者向法院提起了诉讼,长达4年的诉讼带来的是胚胎干细胞研究领域的不确定性。

最近,人类受精和胚胎学管理局开展了一项公众参与的项目,以研讨会、分组座谈会和网络调查的方式,对线粒体替代疗法(MRT:将卵子或胚胎中携带缺陷的线粒体DNA移除,然后将取自于无线粒体疾病女性体内的DNA移植过来)的临床应用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广泛征求意见(英国政府已于2015年2月份批准了MRT)。这个公众参与的讨论项目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它的目标,为日后类似的活动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有的人认为上述两个由公众参与的事例是成功的,但并无由因及果的演绎性措施能够证明究竟这种成功意味着什么。
对于不同模式的公众参与的系统研究需要得到确认。例如,明确各派立场以及普遍社会态度的最佳方法。同样的,关于公众意见如何左右政府决策方面的调查也需要得到确认。
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意味着,基于显而易见的安全隐患,我们已无法继续回避长期存在的伦理问题。继续辩论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究竟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要实现这一愿景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政策,是时候该集体做出决定了。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