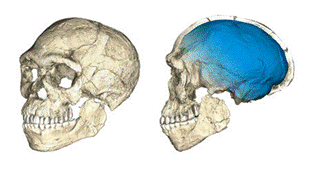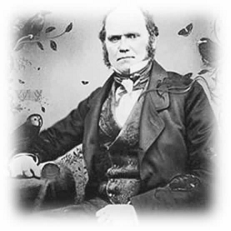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学界的主流理论是非洲起源说,即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是远古非洲狩猎采集者的后代。对于那片孕育自己的摇篮,我们试图通过每一场考古探寻,每一块化石遗骨,每一次基因分析,拼凑出它的更多历史。
不过这些研究往往集中于现代人类,或者说晚期智人,在8万至6万年前从非洲扩散至其他大陆的历史。
而当“出非洲记”结束以后——5万年前,2万年前,9 000年前,留在非洲的人类又经历了什么呢?关于他们的故事,我们了解甚少。(不管是离开还是留守非洲的晚期智人,虽然都算我们这些“现代社会人类”的史前祖先,但也属于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
生物考古学家伊丽莎白?索丘克(Elizabeth Sawchuk)一直尝试借助考古学和遗传学的工具,追寻非洲大陆的史前史。她参与了一支由来自12个国家的44名研究人员组成的跨学科团队,对生活于1.8万年前的非洲人的古DNA进行测序分析,进而更深刻地洞察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史前基因交流。用索丘克的话说,“这些遗传信息有助于像我们这样的人类学家更多地了解很久以前那些留守非洲的现代人是怎么迁移融合的”。
2022年2月23日,此项工作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索丘克应美国科学媒体Singularity Hub之邀评述了此项研究。
非洲往事
大约30万年前,解剖学意义上的最古老现代人出现于非洲。他们制造出更复杂和先进的石器工具,扩大贸易网络,能穿行长达400公里的里程运输原材料。1.4万年前至1.2万年前,人类用兽皮制作衣服,并开始以贝珠串装饰自己。
更广泛的生活方式转变发生于大约5万年前——人类向澳大利亚等遥远之地的迁移也恰在此时间开展。新型石器和骨器变得普及,人们开始用鸵鸟蛋壳制作串珠并交换这些装饰物。此外,虽然非洲的大多数岩石艺术都年代不详且风化严重,但考古遗址处的赭色颜料似乎表明了当时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
鸵鸟蛋壳制成的珠子是当时受欢迎的贸易商品,可以显示古代社交网络的范围
导致上述转变——或者说石器时代晚期的转变——的原因有哪些?为什么之前零星出现于非洲的某些工具和行为突然变得普遍?这是否与人类数量的变化或他们的互动方式有关?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考古学界。
深入过去的挑战
考古学家主要通过古人留下的东西来重建古人的行为。这些东西包括食物、工具、装饰品,还有他们的遗骨。它们可能累积数千年,从而形成了长期的、平均意义上的古人日常生活图景。但问题在于,若仅就考古记录做观察,我们很难搞明白古代人口是如何变化的。
这就是DNA可提供助力的地方。科学家利用遗传分析工具,再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口述和记载历史的证据,就能根据群体之间的遗传相似性,推断出古人的迁移和互动过程。
但遗传分析的对象不能是我们当下活着的人,因为我们的DNA无法重现远古祖先的生活:在过去5 000年间,由于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传播、城市的发展、古代流行病以及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的蹂躏,非洲人口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过程导致部分血脉消失,也将其他另一部分血统聚集融合,造就了新族群。用当下人类的DNA重建古老族群的基因图景,就像阅读一封被雨水淋洗的信件——有些文字模糊不清,另一些则完全不见了。研究人员需要来自古人遗骸的古DNA探索不同时空的人类多样性,并分析是什么因素造就了它。
不幸的是,非洲的古DNA极难恢复,因为非洲大陆横跨赤道,高温和潮湿会降解DNA。我们迄今为止得到的所有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古DNA序列都不超过9 000年。相比之下,掘自欧亚大陆的最古老DNA约有40万年历史。
打破“热带天花板”
我们团队尝试用1.8万至400年前个体的DNA探索8万至5万年前古人的迁徙交流。这帮助我们首次检验前文提到的猜测,即人口变化是否在石器时代晚期的转变中发挥了作用。
我们对埋在如今坦桑尼亚、马拉维和赞比亚境内的6具遗骸的DNA进行了测序,并将这些序列与之前获得的28个非洲人(活动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南非)的古DNA做比较,还为其中部分人生成了新的基因数据,试图从少数古代非洲人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些古DNA保存得很好,可用于研究。
以上工作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基因数据集,能帮助我们研究古代非洲的狩猎、采集或渔猎者的族群历史。我们用它来探索——在过去几千年间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以前的——人口结构。
携带DNA加入长期争论
我们发现,在5万年前石器时代晚期的大转变阶段,非洲人的确改变了自己的迁移和互动方式。
虽然这几十个古人所生活的时空相距上万里,相隔数千年,但他们每个个体都是3个族群的后代——这3个族群与非洲东部、南部和中部的人类(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在的)有关。东部族群的血统出现在南方的赞比亚,南部人类的血脉又存在于北方的肯尼亚。这些情况表明非洲古人长途迁移,并与远离自己“出生地”(族群起源地)的异性生育后代。可能导致这种人口结构出现的唯一方式就是人类在数千年间进行了长距离迁徙。
此外,我们发现,几乎所有东部古人都与今天生活在中非热带雨林里的狩猎采集者共享大量(数量大到惊人)的基因突变,这意味古代东非是真正的基因大熔炉。这种融合与迁移发生在大约5万年前,当时中非的觅食者族群出现了重大分裂。
我们还注意到,至少对于此项研究中的非洲古人来说,在地理位置上最接近他们的邻居,也正是在遗传上最接近他们的远房。这意味着,大约2万年前后,一些非洲地区的觅食者几乎完全就地寻找伴侣(与此前的迁移融合情况不同)。这种习惯必然占据绝对主流且持续很长时间,因为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部分群体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都始终“与自己的地理近邻保持着遗传上的距离”,这种情况在马拉维和赞比亚尤为明显。
至于说为什么5万年前发生不同族群的大迁徙大融合,到2万年前,人们又变得安土重迁起来,目前我们给不出一个满意的解释。或许,随着上一个冰河时代于2.6万至1.15万年前达到顶峰并开始走弱,不断变化的环境使得在家附近觅食更容易;又或者,复杂的物品交换网络减少了人们负重远行的需要。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出现了新的群体特性,婚姻规则因此重组。如果是这样,我们应该会看到手工艺品或其他风俗(如岩石艺术)的多样化,看到特定类型的风俗习惯聚集于不同地区。事实上,这种所谓“区域化”的趋势正是考古学家所观察到的,它们不仅影响文化传统,也影响基因流动。
考古遗迹的恢复和分类是一个缓慢而费力的过程,不过,小碎片也能讲述大故事
新数据,新问题
古DNA研究提出的问题与它给出的答案一样多。人类学家在非洲东部和南部找到了中非族群的血脉,这让他们重新思考:在遥远的过去,这些对于当时居民来说相隔遥远的地区如何发生相互联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目前关于中非的考古学研究仍然不足,部分原因在于政治、经济和后勤问题极大增加了深入中非开展研究的难度。
此外,虽然遗传证据支持5万年前非洲的重大人口转变,但我们仍然不知道关键驱动因素。想确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石器时代晚期的转变,需要对区域环境、考古和遗传记录进行更仔细的检查。
最后,这项研究提醒我们,研究者仍可从非洲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人类遗骨和文物中挖掘到很多东西,而管理这些藏品的博物馆负责人能够发挥极为关键的学术作用。我们团队所研究的一部分DNA来自几十年前就发现的遗骸,另一部分则来自已于博物馆内保存了半个世纪的遗骸。
科学家才刚刚开始了解非洲的人类多样性。
资料来源 singularityhu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