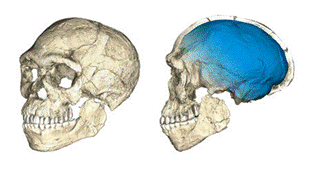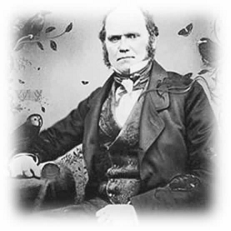以锭、沉船、法老和国际色彩贸易为特色,使用现代考古学和材料科学,追溯玻璃的丰富历史。
今天被人们爱答不理的玻璃,过去似乎只有国王才高攀得起。数千年前的古埃及法老甚至带着玻璃陪葬,留给后世考古学家惊艳的标本。图坦卡蒙国王的陵墓里一个装饰性的书写调色板和两个蓝色头枕都由实心玻璃制成,他所戴的黄金面具镶嵌有蓝色玻璃条纹。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的考古学家安德鲁 · 肖特兰(Andrew Shortland)表示,青铜时代晚期的材料以实用的米色、棕色和沙色为主色调,五彩斑斓的玻璃(充满了蓝色、紫色、青绿色、黄色、红色和白色)提供了除宝石外最靓丽的色彩景观。在材料的层次体系中,玻璃的地位稍逊银金,不输宝石。
但关于这位曾经的材料界贵族,我们有许多问号:玻璃最早于何处由何人制造?其制作工艺怎么样?它如何在古代世界传播?
过去几十年间,材料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以及专家们对过往挖掘的文物的重新分析,填补了玻璃史的很多缺漏。这些分析工作也为我们了解青铜时代工匠、商人和国王的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国际联系打开了一扇窗。
阿玛尔纳书简,指的是在埃及阿玛尔纳遗址发现的大量以楔形文字写成的泥板文献,记载法老与西亚各国国王之间的往来书信内容,其中提及了玻璃。亚实基伦的迦南统治者伊迪亚曾如此说道:我的国王,我的主,我已经订购了一些玻璃,特此发送给国王,我的主,30(片)玻璃
千年寻踪
玻璃通常由二氧化硅制成,内部原子无序排列,是“玻璃态”的非晶体。(不同于晶体结构的水晶。)
考古学家发现的玻璃珠可追溯至公元前3000年。基于玻璃材料和技术的釉料则出现得更早。不过到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200年——玻璃似乎才真正变得流行,在古埃及、迈锡尼时代的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也称近东,位于现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广受追捧。
那个时代的玻璃不同于今时之物,通常是不透明且色彩饱满的,其二氧化硅来源则为压碎的石英卵石,而非沙子。聪明的古代人找到方法将碎石英的熔化温度降低到青铜时代熔炉所能达到的水平:沙漠植物的灰烬中含有丰富的盐类,如碳酸钠或碳酸氢钠,通过掺入这些成分,熔融工作变得容易;此外,添加物还带来了氧化钙,从而使玻璃更加稳定。古代的玻璃制造商还会添加赋予玻璃颜色的物质,例如钴(深蓝)或锑酸铅(黄)。这些成分融入熔体,为如今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化学线索。美国西北大学的材料科学家马克 · 沃尔顿(Marc Walton)表示:“我们可以开始分析用于生产玻璃的原材料,然后推断它来自世界的哪个地方。”
但上述化学线索无法帮助学者们走得很远。大约20年前,当肖特兰和同事调查玻璃起源时,他们发现来自埃及、近东和希腊的玻璃似乎在化学层面上十分相似,难以通过当时的技术进行区分。
蓝色玻璃是个例外。这要归功于波兰出生的化学家亚历山大 · 卡茨马尔奇克(Alexander Kaczmarczyk)的工作。他在20世纪80年代发现,把铝、锰、镍、锌等元素与钴放一起用,能使玻璃呈现深蓝色;此外,通过检查元素的相对含量,卡茨马尔奇克等人甚至在埃及的绿洲里追踪到了用于蓝色着色的钴矿石及其矿物来源。
肖特兰跟随卡茨马尔奇克的脚步,开始研究古埃及人如何使用钴矿石。他和同事在实验室里重现了青铜时代晚期工匠可能用来制备相容颜料的化学反应,并成功制得一种深蓝色玻璃,与古埃及蓝玻璃颇为相似。
这条玻璃鱼是在阿马尔纳城一座相当简陋的私人住宅内发现的
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一种被称为“激光剥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的新技术为新发现和新见解提供了可能。LA-ICP-MS能借助激光去除肉眼不可见的微小材料斑点,使用质谱法测量一组元素,创建样品的化学指纹。
基于此方法,肖特兰和沃尔顿等人在2009年对希腊出土的青铜时代晚期玻璃珠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希腊玻璃具备近东或埃及的特征——支持了希腊从这两个地方进口玻璃的观点。(希腊方面可能对玻璃进行了加工。)埃及玻璃往往含有较高水平的镧、锆和钛,而近东玻璃则含有更多铬。
难择“西”“东”
玻璃最早诞生于何处呢?研究者长期以来的争论焦点集中于近东和埃及。在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基于一些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美丽且保存完好的玻璃制品,而更倾向于选择埃及。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人们在现伊拉克境内的青铜时代晚期城镇努济发现的大量玻璃,专家观点开始向近东地区倾斜。
然而,对考古文本的重新分析显示,努济镇的存在时间比此前估计的要晚100~150年,彼时的埃及玻璃制造业似乎更发达,因此较近东更具说服力。
但故事并未就此结束。玻璃会降解,尤其是在潮湿环境下,而沙漠环境则拥有极为理想的保存条件。来自埃及古代墓葬和城镇的物品历经数千年仍保完整,但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河漫滩上,墓葬里的近东玻璃因经常受到水的侵袭,而变作片状粉末。
坏了的玻璃难以辨认,更无从分析,这意味着我们可能遗漏了大量近东玻璃。用肖特兰的话说:“我认为很多玻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你现在无法真正确定哪块是最早出现的。”
“投桃报李”
分析玻璃的制造地是一项高难度工作,部分原因在于材料经常被交换(无论是以玻璃制品抑或玻璃原料的形式)。
塞浦路斯研究所的考古材料科学家蒂洛 · 雷伦(Thilo Rehren)研究了图坦卡蒙墓中物品背后的工艺。他指出,玻璃有助于我们将古代帝国联系到一起。国王将物资运送给其他统治者,并期待对方投桃报李(物资或忠诚)。青铜时代晚期的物资清单显示,象牙、宝石、木材、动物以及人口等都被用于交换,玻璃当然也被囊括其中。
肖特兰和同事对一条出土于埃及古罗布的玻璃珠项链开展分析,发现了与美索不达米亚相关的化学特征:铬含量相对较高。出土地点似乎表明它是送给法老图特摩斯三世以及他妻子(近东妇女)的礼物。“我们现在刚开始看到古埃及与其他地区间的一些交流。”
20世纪80年代初期,潜水员在土耳其海岸附近发现了公元前14世纪的乌鲁布伦沉船。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考古学家卡罗琳 · 杰克逊(Caroline Jackson)认为,针对这艘沉船的分析有望揭示3 000多年前的全球经济。它可能是腓尼基的航船,往来各地,运送礼物——象牙、铜、锡,甚至是来自波罗的海的琥珀。发掘团队从沉船内找到一堆彩色玻璃——175个未完成的玻璃铸块,待进一步加工。
大多数铸块呈深蓝色,不过也有紫色和青绿色的。杰克逊与同事切下少量小碎片分析发现,这些原始玻璃块原产于埃及。
陶中璃影
难以确定玻璃制造地点的另一个原因是制造过程几乎不产生废料。
大约20年前,雷伦与考古学家埃德加 · 普施(Edgar Pusch)来到尼罗河三角洲一个跳蚤猖獗的挖掘点,尝试通过出土于此的陶器碎片来寻找关于古代玻璃“作坊”的蛛丝马迹。该遗址位于今天埃及境内的村庄坎蒂尔(Qantir),是公元前13世纪法老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的古埃及首都。
雷伦和普施发现:许多陶器都带着一层富含石灰层的不粘性屏障,方便拆卸;其中部分器皿(包括一个重复使用的啤酒罐)似乎曾被用于制造玻璃,因为它们装有白色、泡沫状的半成品玻璃。此外,他俩还将陶器的颜色与它们在熔炉内承受的温度联系了起来:玻璃原料可能在大约900 ℃的高温下熔化,进而转变为半成品玻璃;但有些陶器呈深红色或黑色,这表明它们曾被加热至1 000 ℃以上,这个温度足以令玻璃熔化并均匀着色,最终成为玻璃铸块。一部分陶坩埚甚至含有以铜着色的红色玻璃碎片。
之后,雷伦等人又在其他遗址找到了类似的关于玻璃制造的证据。他们发现阿玛尔纳遗址的陶器里有且仅有钴-蓝色玻璃碎片。而在坎蒂尔的陶坩埚内,铜-红色玻璃碎片是主要成分。古埃及王室贵族墓葬所在地利斯特也有带玻璃碎片的陶器出土,不过其主色调为青绿。
发掘点的玻璃色调单一,意味着该“作坊”专攻某种着色剂。不过色彩缤纷的玻璃制品也并非罕物,发掘团队在阿玛尔纳找到了多色调玻璃棒(可能通过重新熔化不同颜色的铸块制成)。这一发现也支持了部分学者的观点:各色玻璃铸块的运输和贸易活动在多地开展,它们被用于制品加工。
火舞琉璃
很多考古学家仍在阿马尔纳追寻玻璃往事,有时还会仔细重复前辈们的探索工作。
1921年至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 · 伍利(Leonard Woolley)领导团队发掘了阿马尔纳遗址。但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埃及古物学家安娜 · 霍奇金森(Anna Hodgkinson)看来,伍利等人行事匆忙并专注于更花哨的发现,而没有花功夫去记录玻璃,“坦率说,他们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在2014年和2017年的挖掘工作中,霍奇金森和同事们努力填补前辈的疏漏。他们在阿尔玛纳遗址发现了玻璃棒和玻璃片,其中一部分出土于没有窑炉的、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附近,这有些令人费解,因为玻璃在当时象征地位。受到更古老埃及艺术——描绘两名金属工匠用管子向火中吹气的画作——启发,考古学家想知道能否使用小火来加工玻璃。他们围着火炉埋头干,终于发现,比造玻璃常规火候更小的火力也能达到足够烧制玻璃珠的温度。霍奇金森认为,早期考古学者可能忽略了这种小火力的炉子。鉴于此,阿玛尔纳时代的玻璃制造或许并不如此前推断的那么高级。她进而推测,当时的妇女和儿童可能也参与了玻璃制造,因为维持恰当火候需要更多人手。
雷伦也一直在思考这些玻璃的去处,因为近东地区的商业城镇盛产玻璃,并且大量运往希腊。“在我看来,它不像是一种受到严格控制的王室商品。我相信,再过5至10年,我们就能够证明阿马尔纳的玻璃是一种昂贵独特的高级商品,但并非王室独享。”
画中的两名金属工匠用管子向火焰吹气(上);研究人员模仿画中人以管吹火的方式,尝试制造阿马尔纳同款玻璃珠(下)
另一方面,研究人员也开始借助材料科学追踪彩色玻璃制品的潜在“颜色”交易。2020年,肖特兰等人报告称,他们使用同位素追踪了锑的来源,这是一种可用于产生黄色或使玻璃变得不透明的元素。肖特兰指出:“绝大多数的早期玻璃都含锑。”不过锑非常罕见,这让他的团队很想知道古代玻璃制造商是从哪里得到此物质的。
他们分析发现,这些玻璃中的锑同位素与来自今天高加索格鲁吉亚地区的辉锑矿(含硫化锑的矿石)相匹配——这是有色玻璃国际贸易的最佳证据之一。
研究人员现在依然努力探寻着玻璃诞生的元年。虽然埃及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但近东地区仍有许多遗址可待考古学家挖掘以找寻新线索。由于现代社会对文物跨国(甚至只是跨区)分析的诸多限制,霍奇金森等考古学家正致力于在挖掘现场应用便携式考古方法,并积极与当地研究人员开展合作。与此同时,借助强大的新技术去重新分析那些已被探究过的旧物件,也有望带来新的考古线索。
鉴于我们对玻璃历史的认知是不断发展的,雷伦提醒大家不要过分相信任何研究结论。尽管考古学家借助历史记录和已知文化背景,仔细思考了这些古代玻璃器物的意义和历史,但我们须明白,曾经散落于某地的材料中只有一小部分能保存至今并被发现,学者手里的珍贵遗存不过是零光片羽。而用雷伦的话说:“考古研究工作可能给出相互矛盾的信息和观点。”所有的考古信息与玻璃“碎片”混在一起,更是能以不同方式拼凑出不同的图景,得到不同的结论。
资料来源 Knowable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