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安格拉·默克尔的监督下,德国在能源创新方面投入巨资
无论问及哪位德国研究人员“为什么德国的科学基地正在繁荣发展”,他们一定会提到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他们会说,这位世界上最强大的女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根本――东德物理学家。
全球10年金融动荡期间,默克尔政府的年度科研预算以典型的德国方式获得了稳定的、可预测的增长,激发了大学之间的竞争,促进了公共资助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在默克尔的监督下,德国在可再生能源和气候研究领域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在保证对基础研究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政府对其他领域的影响也在加大。
越来越多的外国研究人员选择在德国发展事业,而不是选择像美国或英国这样的传统人才吸引国。德国局势安全,但发展缓慢,这一点是举世闻名的,然而德国看起来开始呈现龟兔赛跑之势。
德国慕尼黑马普学会税法和公共财政研究所所长、德国主要资助大学研究的机构――德国科学基金会(DFG)副会长沃尔夫冈·施恩(Wolfgang Schn)说:“德国是成功的,其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科学预算或某种‘默克尔效应’。像默克尔一样,德国有着深厚的科学根基。”
在20世纪的动荡形势之前,德国的科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其创建的惯例至今仍有许多国家在遵循。男性主导的等级制度和普遍的、死板的法规留下了一些残余观念,虽然德国一直在跟这些观念做斗争,但是德国的研究看起来一如既往,依然强大。特别是在全球似乎都对科学越来越无动于衷的阶段,德国的这种势头难能可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肯尼斯·普雷维特(Kenneth Prewitt)说:“如果美国的科学政策制定者和预算决策者愿意再次从德国那里学习经验,我会很高兴。”
德国现代科学结构的基础是两个世纪前由普鲁士教育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提出的理念,他率先提出的诸多观点在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影响力。例如,他提出建议――大学教授在从事教学的同时也要进行前沿领域的研究。
他的理念是:教育应该广泛而深刻,学术生活应该不受政治和宗教的影响……这些对德国人而言仍然刻骨铭心。柏林高级研究院秘书长索斯藤·威廉米(Thorsten Wilhelmy)说:“洪堡体系是我们的DNA,即使在艰难时代,政治家也不想削减基础研究,这就是其中的原因。”
这些理念经历过剧烈的政治动荡。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使科学走入歧途,使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1949年,德国被重建为两个国家,两国在相互对抗的政治制度下重新积累各自的科学实力。
西德民主立宪制仍然有效,该国宣称:“艺术与科学、研究和教学应该是自由的。”为了确保中央集权和滥用权力的情况永远不会再度发生,西德创建了一个高度联邦化的国家,文化、科学和教育的责任由各州来承担,这种特征注定对大学的发展产生正负双面影响。
相比之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东德)实施集中研究策略,研究受到严格的控制。东德科学家跟西德科学家是隔离开来的,随着东德经济的逐渐衰败,其政治制度也变得越来越苍白无力。默克尔是在这种体制中长大的。1978年,她毕业于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获得物理学学位,之后进入柏林的中央物理化学研究所――东德最负盛名的研究中心之一。在那里,她遇到了第二任丈夫――量子化学家乔基姆·索尔(Joachim Sauer),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博士学位。
1990年,当两个德国统一时,西德特别委员会评价了东德科学家的能力。许多人失去了工作,但索尔被接受,调入了柏林的洪堡大学。以前没有公然表明政治立场的默克尔欣然参与了民主政治,很快就加入了中右派的基督教民主联盟(CDU)。她顽强地爬到该政党顶层领导的位置,并于2005年成为德国第一任女总理。2009年和2013年也分别赢得了联邦选举,而且看起来大有保住这一职位之势。在德国,担任政府首脑没有任期的限制。3月份,她发表意见说:“我本人来自基础研究领域,而且我也总是说,你不可能预测到这个领域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为其发展留出空间。”
稳定的支持
德国公共资助的科学组织有五大支柱科研机构:大学及其四个独特的研究机构,每个机构都是以德国历史上的科学巨人命名的。
马普学会成立于1948年,以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1858―1947)命名,目前管理着81家基础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的所长都会得到额外的预算资金,他们拥有资金的支配权,可以用来开辟自己的研究方向。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通常每年可以获得200万欧元的基本运维资金来实施他们的研究计划,其中不包括主要的设备采购资金。1949年弗劳恩霍夫协会成立,该协会致力于应用研究,是以巴伐利亚物理学家约瑟夫·冯·弗劳恩霍夫(Joseph von Fraunhofer)命名的,他是精密光学的先驱。国家研究中心根据政府优先事项实施大型战略性研究计划,目前该中心被收编于亥姆霍兹协会。亥姆霍兹协会是以开创性生理学家兼物理学家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命名的。一批其他的科研机构和设施被收编于由博学家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命名的协会中。
早在1949年,一项协议规定:联邦政府跟各州一起分担这些研究机构的费用。但是一般说来,各州必须要为自己的大学提供财力支持。这样的大学有大约110所,另外还有230所科技应用大学,这些大学主要是为产业界培养劳动力,不能授予博士学位。
米尔海姆市马普学会煤炭研究所所长费尔迪·舒斯(Ferdi Schüth)说:“这种结构的清晰度和透明度迎合了德国人爱好井然有序的心态,这让包括政坛官员在内的外界人士更加容易理解。”
西德在战后经济奇迹期间,对科学研究的支持迅速加强。尽管德国的统一使该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多年来政界人士一直对科研保持着稳定而强势的支持。政府对所有研究机构和DFG的支持每年都保持增加5%。直到2015年,联邦政府和各州之间签订的“研究和创新条约”规定,对科研支持的年增长幅度有所下降,这种下降态势会持续到2020年,但是增幅仍然保持在令人羡慕的3%。
马普学会主席、化学家马丁·斯特拉特曼(Martin Stratmann)说:“未来的资助有保障,这真正地能够使我们以长远的目光对研究战略进行规划。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是其他国家几乎不具备的优势。”
支持资金流
20世纪70年代后期,免疫学家多洛雷斯·申德尔(Dolores Schendel)在慕尼黑大学做了两年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她深知在德国搞研究意味着什么。正是对长期资助充满了信心,使得申德尔没有返回自己的祖国――美国。她本想仅仅帮助慕尼黑大学的骨髓移植计划建立一个小鼠实验室,但是她发现实验室的设备是富有吸引力的,而且随着她的研究成果可转化性越来越强,她的成果不再适合做成系列高端论文,她知道她可以依靠有保障的地方资助。后来,为了扩大研究规模,申德尔转移到慕尼黑亥姆霍兹研究中心。她创建的一家新公司被收购时,她成为慕尼黑免疫治疗企业――医学基因公司(Medigene)的执行总裁兼首席科学官。目前,她正在对候选的癌症疫苗进行临床试验。申德尔说:“若是在美国,我不敢确定我是否能够取得这些成就。在美国,资金的支持在稳定性上往往比较欠缺。”
1990年,国家统一造成了混乱局面,这迫使该国要解决某些制度问题,如各研究机构之间缺乏合作等问题。因此,政界人士开始铲除合作道路上的诸多障碍。
1999年,默克尔之前的联邦政府是社会民主党和绿党之间的一个联盟政府,该政府修订了一项法律,要求由各州政府为大学做出从分配预算资金到进行学术任命的所有决定。此后,各州逐个开始允许大学来管理自己的事务了。
所有大学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具有同等地位的。直到2005年,政府为大学提出一项重大改组行动,推出了“卓越计划”。现在,该计划已经很成熟,它鼓励大学之间相互竞争,获取联邦资金,推动顶尖水平的研究,促进研究生院建设,而且最重要的是促进“卓越群体”建设――推动跟其他研究机构的科学家进行大规模合作。此外,在所有类别中胜出的大学也将获得“精英大学”的称号,还会获取额外的资金支持。
2005年晚些时候,默克尔成为总理,她任命跟她志同道合的同事兼朋友安妮特·沙万(Annette Schavan)担任教育和研究部长,沙万通过一系列巡查活动,推动了卓越计划,从根本上改变了德国的大学。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向该计划投入了46亿欧元,在各轮巡查中获得精英称号的大学共有14所。那些还没有获得这个称号的大学,正在努力争取获得精英称号,通过进行群体内部合作,增强了竞争力,开辟了其他的支持资金流。在德国科学领域,一度孤立的科研机构目前正在进行合作。
默克尔和沙万捍卫了国家法律,允许联邦政府直接资助大学的研究,允许大学拿出高薪来吸引或留住水平最高的科学家。作为公务员,德国大学教师的收入通常少于其他国家的科学家或产业界的科学家。
由于所有的这些变革,德国大学的世界排名已经攀升。2005年,只有9所德国大学出现在《泰晤士高等教育》期刊排名前200位中。目前,有22所大学进入前200位。在绝大多数年份中,慕尼黑大学在德国大学排名中都是名列榜首,在每一轮卓越计划中都能胜出,该校从2011年的世界排名第61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30位。
自从2005年以来,物理学家埃克塞尔·弗雷穆特(Axel Freimuth)一直担任科隆大学的校长。他说:“科隆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变得难以辨认出来。”弗雷穆特看到了卓越计划所带来的巨大转变和大学教学的转型。在弗雷穆特成为校长的时候,德国开始从本国由来已久的特殊文凭制度转变为欧洲标准的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制度。这样,在3~5年的时间里能够更加有效地培养学生。随着大学自治的来临,弗雷穆特创建了一个新的管理体系。他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从战略上去行动,这其中有一种全新的精神。”
群体研究热
与此同时,群体研究热在德国已经蔚然成风。沙万实施了几项举措,让不同支柱领域的科学家一起搞研究,并与产业界合作。最引人瞩目的是,她借助亥姆霍兹协会的影响力创建了一个国家卫生研究所网络。在全国范围内,亥姆霍兹协会将卫生研究机构的力量集中起来,这些研究机构中包括对神经退行性疾病或代谢性疾病等病变的研究。
柏林方面正在进行试验,将查理特教学医院和马克斯-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中心(亥姆霍兹协会下属的一个中心)的研究力量汇集在一起,组成一个被称为柏林健康研究院的转化研究机构。巴登符腾堡州已经将数亿欧元的资金投入到“网络谷(Cyber Valley)”计划中,该计划于2016年12月推出,将所有区域性人工智能研究整合在一起,得到了宝马、戴姆勒、保时捷、博世和脸书等大型公司的大力支持。
同时在海德堡大学和德国癌症研究中心任职的神经科学家汉娜·莫耶(Hannah Monyer)说:“这种群体研究确实有很多优势。”德国癌症研究中心是亥姆霍兹协会下属的一个中心,同样位于海德堡市。尽管群体研究要求研究人员花更多的时间来进行交谈和进行组织安排,但是莫耶说:“在当今,这是我们能够采取的最佳行动。”在一轮卓越计划中他们创建了一个研究群体,当她的研究工作暂时涉及不熟悉的领域――疼痛机制时,研究群体为她省去了大量的工作。她不必从头开始学习一切,而是与当地的行为实验室进行了密切协作,该实验室为她提出了建议,提供了设备和技术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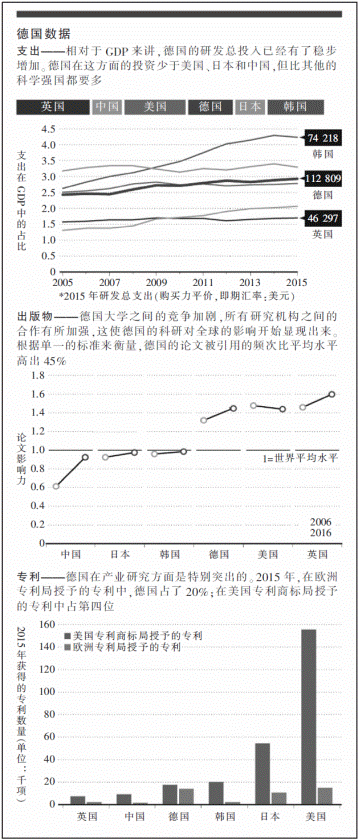
大规模合作仍然处于测试阶段。血管生物学家霍尔格·格哈特(Holger Gerhardt)在伦敦克里克研究院拥有一个固定的职位,2014年他离职加入了柏林健康研究所的一项计划。他说:“我知道这是一项特大型的实验,但是我觉得或许我真的能够在这里创造出新的成果。”
在德国文化中,人们追求管理秩序和道德秩序。有时,研究人员目前所享受的条件改善会受到这些秩序的挑战。格哈特说,他自己经常提醒群体合作伙伴不要创建不必要的组织结构。虽然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是被允许的,但是这类研究特别难以进行。除了几个较老的细胞系之外,人类胚胎干细胞的使用是被禁止的。在这一点上,默克尔仍然是坚定不移的。
有关德国的数字
总的来说,一些数据表明德国在科学上处于一种积极向上的状态(见“德国数据”图表)。在德国的大学中,外国学者的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9.3%跃升至2015年的12.9%。目前,在引用频次指标中占前10%的公开发表论文中,德国的排名已经超过了美国。
但是,德国在科学上仍有需要追赶的领域,特别是在大学基础设施方面。跟非大学研究机构的现代化相比,大学的设施看起来是极为破旧的。对于越来越多的学生,各州必须要承担所需的费用,学生是免费上学的,结果楼房的修缮工作跟不上。
在德国,几乎没有科学家看到该国攀越到科学界的顶峰。一方面,德语可能仍然是令人反感的,尽管在当今德国的实验室里通常讲的都是英语;规章制度和填表要求也让许多人望而生畏。因此克鲁尔说:“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人是不愿承担风险的。在这里,激进的、突破性的创新较为少见。”
此外,在提高女性代表在研究中的占比方面,德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研究机构中,2005年具有最高科技职位的女性所占比例为4.8%,少得可怜;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3.7%,仍然很少。在大学,拥有顶级学术职位的女性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10%上升至2014年的17.9%,仍然远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在产业界,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全国30强科技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有160名,申德尔是其中仅有的3名女董事之一。
但是,科学家们普遍相信,情况将会继续得到稳步改善。在竞选宣言中,默克尔承诺要继续支持研究和创新,并将年度预算增加到4%。只要不出差,这位总理每天都会回到她在洪堡大学附近的公寓,利用余下的夜晚时光跟她的化学家丈夫待在一起。舒斯说:“归根结底,这就是她的根。她知道作为科学家意味着什么,她清楚研究的价值,这种风气是自上而下蔓延开来的。”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田 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