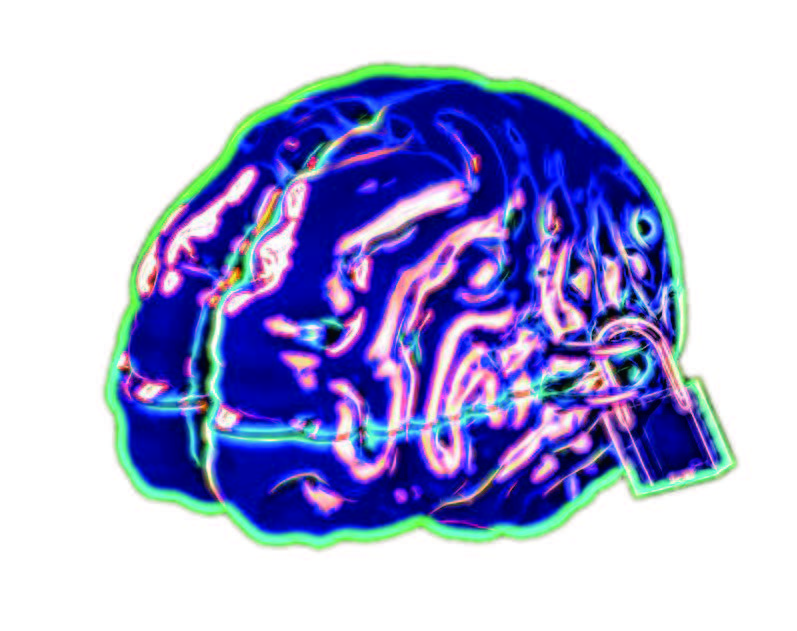在信息互联和大数据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对于隐私的担忧也令人不由地担心。假若更进一步,记录我们信息的装置从手机和电脑变成大脑植入物,会发生什么呢?
在我被囚禁的第289天,他们过来见我。
我的脑袋不断悸动,感觉像塞满了金属纤维,但是当哈格里夫船长和博莎拘留官为我的牢房开锁时,我还是在脸上挤出微笑。我的手臂、双脚、手腕、腰部、胸部、大腿和脖子都被绑在支架上,一套厚厚的囚犯绑缚衣紧紧捆住我的躯干,靠磁力吸附在支架后部。在那之后,他们又将我封禁在外骨骼囚服里。
总的来说,我将这视为一种恭维。
博莎在全息影像仪上检查我的状态。当她瞥向哈格里夫,说了句“没有进展”时,我笑得更欢。
哈格里夫用指节敲打了埋入我的太阳穴的接线。“哦,他迟早会崩溃的。或者,你可以干脆地告诉我们。我们最终会把秘密挖掘出来,哈鲁斯。”
“唉,”我透过固定在我脸上的钢网口络用刺耳的声音说道,“你们到目前为止都干得不错。”
博莎的拳头击向我的脑袋一侧。我因为这次拳击而摇摆,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我在太空船坞的酒吧里挨过更狠的拳头。
“我得要说,一边脑袋连着‘接线’,一边当走私犯是相当愚蠢的职业转向。”
哈格里夫这一次说到点子上。当名叫“接线”的大脑植入物出现时,每个人都认为只有富人会购买它们。结果相反的事成为真实。“接线”的制造成本变得如此低廉,任何一个希望与现代生活保持同步的人都得要买一台。他们将记忆和信息即刻储存、备份在数据圈里,随时都能访问。在一些星球,安装“接线”是强制性的。富人们负担得起通过内部湿体(wetware)访问的远程存储,那种存储空间是黑客也无法骇入的,也不会把他们的记忆、去过的地点、做过的事情登记在半公开数据库中。实际上,你负担得起不安装“接线”的代价。
这是我转向走私的部分原因。各星系的人会支付可观的信用点,只为获得一些他们不想在海关登记的物品。麻醉剂、烈酒、数据库、文物、军用级武器、远古遗物。任何东西都可以。我和船员们的走私事业干了差不多九个标准年。我犯了一次差错,但一次闪失就足以让我陷身囹圄。我被星系安全部队抓获,丢进这个位于星系深处的拘留中心,接受审讯。
哈格里夫靠在像镜子一样光滑的墙上。“如果你放弃你的船员,一切都可以结束。”
我打了个响鼻。“你们不经常做这种事,对吧?”
“嘿,我们有的是时间。你没有。”
我将近在这儿坐了300天,抵抗着他们从我的“接线”输入进来的“剥头皮”软件,忍受它在我头脑的“服务器机柜”间闻来闻去。它从我的脑子里搜罗出我干过的买卖、服务过的主顾、走私过的有趣物品。最重要的一项是:我的船员去了哪里。我对抗“剥头皮”软件时,脑袋悸动,伴随着滞钝的疼痛。我往脑海里填入分心的念头、错误的记忆和随机的统计数据,假装它们是真实的,以此来迷惑软件。我杀灭研究模式,用心智的方式埋葬数据。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意志大战。人工智能无法判断哪段记忆是真实的,哪段记忆是虚构的,除非它们想把我的大脑变成一堆冒烟的神经元。但软件在适应新情况,识别出新模式,渐渐知道我是如何思考的。如果我身上的外骨骼囚服没有将我的睡眠限制在一晚四小时,并将我的食物和饮用水摄入量降到最低的话,或许我能够抵抗它。他们一边用持续不断的白噪音对我进行狂轰滥炸,一边将我包裹在桑拿一般的酷热或者边境永冻土一般的寒冷中。这是“文明”的酷刑,勉强合乎星系际法律。我的身体麻木了。我几乎无法保持醒觉,更不用说进行心理战。
但我每抵抗一天,我手下的船员们就能多抢先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对付出问题的掮客交易。我们不会关注如何在下周、下个月幸存下来。我们只关心明天。我们能在事实上将难题永远推迟下去,只要我们能坚持到第二天。现在,我在为船员们做那种事,痛苦地熬过一天接着一天。任何一位优秀的船长都会这么做,而我自豪地认为自己是最出色的。当我们成为走私者时,我们发誓要对彼此绝对忠诚。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不会让别人说出阿利斯泰尔 • 哈鲁斯没能硬撑到确凿的崩溃点。
“我希望他没有松口。”我回头瞅去,看见博莎在拨弄我的外骨骼囚服的约束带,用能压裂骨骼的力气收紧约束带。“那样更有意思。”
哈格里夫倾身靠近我,近得足以亲吻到我,再用纹身的手指轻弹我的“接线”装置。“哈鲁斯,你是个生意人。那么让咱们做笔生意吧。你现在开口交代,我会将你从外骨骼囚服里放出来,拔掉‘剥头皮’软件。给你一间头等舱房间。该死的,只要告发指认你手下的船员,我会给你安排一件钴等级的金属基板,不是那种非法制造的便宜垃圾。你有什么想法?”
我使出全力,用脑袋去撞她,让她知道我的回答。骨骼嘎吱嘎吱响,鲜血四溅。她趔趄后退,手摸着被撞伤的鼻子。尽管我很疲惫,可我还是在口络后面用力咧嘴笑,几乎要把脸庞撕裂,“那真的是你能秀出的最好一招?”
博莎正要将我的下颚碎裂成糖玻璃一样的碎片,哈格里夫阻止了她。“不,将剥头皮软件提升到下一级。实际上,提升三级吧!让它去深挖,让永久性伤害见鬼去吧。看看再过几个月后他有多反叛。哈鲁斯,等你乱流口水、通过管子来喂食时,你会希望你接受我提出的条件。”
博莎超驰控制了系统,调整设定,让它低于法定最低值。机器运转起来。我咧嘴看着她们离开,去为下一场即将到来的心理战做准备。随着剥头皮软件野蛮地挖洞进入我的大脑,我的头痛变得令人战栗,悸动不已。当我在心智的结构里擦除我的船员们的名字,我的被牢牢束缚的拳头晃动起来。我准备好再抵抗一天。以及它之后的一天。还有它之后的另一天。
那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只要再抵抗一天。
资料来源 Natur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澳大利亚科幻作家杰里米 • 绍尔(Jeremy Szal)生于1995 年,毕业于新南威尔士大学,他创作的黑色太空歌剧小说《风暴之血》(Storm blood)将于2020 年2 月由英国格兰茨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