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科学和技术在未来设计中的作用,将从一个在美国度过了他的一生和他的科学生涯自20世纪30年代后期延续至今的人的眼光予以讨论。读者可能会从我的讨论中发现一些适合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特点。
鉴于科学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财政支持,而且在现代还依赖于整个社会的支持,因此,讨论科学同社会的相互影响是恰当的。以美国为例,一些讨论的题目是能影响研究基金的分配的政府官员的观点、基金机构的反应和科学家的观点。最后,我们将研讨科学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并试图得出关于它们相关的未来和技术的未来的含意的某些结论。
政府官员的观点
参与制订或影响科学政策的政府官员,表达了他们想改变支持研究和开发的意见。他们通过建立在科学和社会的作用的某种新观念基础上的“范例改变”(“paradigm shift)来加以表达。“paradigm”这个词有几种含意,而用在这里所谓的是“方式”或“模式”。换言之,政府官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对科学资助的方式。他们的动机是,引导研究朝着诸如保证有一种更强的经济和改善环境的方向进行。越加明显的是,控制着政府基金的政府官员,不情愿资助那些他们认为与国家需要无关的科研项目。
政府官员择优安排的一个例证是,他们在议会投票反对继续建造被称做超级超导对撞机的高能加速器。这种择优资助方向的改变意味着,如果核物理被认为较之其他的科学学科对新的国家优选项目的关系较少的话,它得到的支持就会变得更少。

基金管理机构的观点
联邦政府官员想把政府掌握的研究基金引向支持服务于国家优选项目的的意图,已影响了可以从基金管理机构得到的资助的性质。例如,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化学方面的资助的少量增加是朝向所谓的战略研究动议权的方向,包括诸如先进的材料及加工、生物工程、环境化学和高性能计算技术。很可能这种趋向还会继续下去。联邦科学、工程与技术协调委员会将目前国家优先资助的领域认定为高性能计算技术、先进材料、加工研究与教育、生物工程与全球变化。表现出来的意向是,要对这些领域作更多的努力,而不是完全将它们排除在外。在有关未来对科学的声明中使用诸如“新模式”、“战略领域”、“优选项目”和“国家竞争力”之类的词汇的结果,会在科技界引发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对科学支持的诸多方面,例如,这种“模式”真的是有新意吗?该由谁来决定哪些领域是有战略意义的?该由谁来确定优选项目?难道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重大贡献应该遭受很大的牺牲吗?
至此,事情已变得十分明显,政府希望把由它资助的科研活动引向它认为是战略性的领域。这是一种新的模式或者只不过是一种重点的转移?很明显,一些年来已经对战略性(优选)项目给予了很多的资助。在美国,一项由国家科学基金会执行的重大的工业-大学合作研究计划。1994年1月24日由美国化学会出版的《化学与工程新闻》上,详细介绍了这项非常成功和涉及范围很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的动机是,把由大学开发和转让的与工业有关的技术付诸实现。目前已有50多个活动中心,参加的有大约1,000名专业人员、1,000名研究生和78所大学。有700多个机构,包括政府机构、国家实验室和约500家公司资助这些中心。这篇文章中的一张表格列举了包括许多技术在内的研究课题。文章还指出,这些中心的成功率非常高,失败的只占6%。赞助机构在这些中心提供的技术的基础上作了巨大的投资。还有许多不属于国家科学基金会计划的其他合作形式。
我们真的有一种“新模式”吗?如若有,那么这种“新模式”又是什么?为了国家的需要而研究并非新事;与工业合作也并非新事。什么才是新的呢?种种迹象表明,所谓新的是指受政府资金控制的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被削减到某种未特别规定的程度,以利于那些看得出对国家有利的研究。我相信这就是科学家们担心的原因。科学和技术的重大发展,一般都源自好奇心-驱动的研究,而这些发展曾经对国家利益起了重大的影响,使国家增加了新的工业部门,并对健康、福利和社会的安全做了贡献。试问,削减好奇心-驱动的研究符合国家利益吗?
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
很多科学小组已产生了不少的文献,它们用许多例子来描述好奇心-驱动的研究是如何引起乃至推动社会的重大发展。《今日物理学》1993年10月期庆祝了《物理评论》杂志创刊100周年。这一期的主要部分献给了基础研究方面的内容。罗伯特K · 阿代尔(Robert K. Adair)和欧内斯特M · 亨利(Ernest M. Henley)的一篇文章指出:“在《物理评论》中反映了基础物理学研究的100年。这些研究是维持现代社会技术丰收的`种子'”。在关于激光的一篇文章中,尼古拉斯 · 布隆伯根(Nicolaas Bloembergen)指出:“报道激光应用的第一篇论文,在1960年被《物理评论通讯》拒收,如今激光已成为一个庞大的、还在发展的工业,然而激光研究的先驱者的初衷却是为了研究物理学。”在一篇有关光纤的文章中,阿利斯特M · 格拉斯(Alister M. Glass)指出:“光学和量子力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已成长为推动一场通信革命的技术。在一篇关于超导的文章中,西奥多H · 格伯勒(Theodore H. Geballe)写道:“理解Kamerlingh Onnes的发现,花了整整半个世纪,另外1/4世纪使它变得有用,估计我们不会等那样漫长的时间来使新的高-温超导体投入应用。”其他的文章涉及核磁共振、半导体、纳米结构和医学回旋加速器,这些都是源自基础物理学研究的具有重大的技术和医学意义的课题。
1992年,美国化学会会长欧内斯特L · 伊莱尔(Ernest L. Eliel)在该学会的一份出版物《科学与意外发现》的序言中,就“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写道:“许多读过托马斯 · 爱迪生生平的人都认为,有用的产品都是有明确目的的研究成果。也就是说,这种研究是为了生产一种希望得到的产品特别设计的。但是,这本小册子中所列举的例证表明,进步往往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取得的。就像Serendip王子那样,研究人员往往会发现较之他们本来想寻求的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更重要的财富。例如,导致后来研制出特氟隆(Teflon)的四氟乙烯,本来是想用来制作新的致冷剂的。抗艾滋病的药物AZT,本来是设计来做一种抗癌药物的。”他还进而指出:“但是,大多数研究的背景情况却是各不相同的。研究人员感兴趣的是某些自然现象,有时是明显的,有时是推测的,有时是被理论所预言的。”因此,罗森堡(Rosenberg)关于电场对细胞分裂的影响的研究,导致了一种重要的抗癌药物的发现;肯德尔(Kendall)关于肾上腺激素的研究,产生了一种抗炎症的物质;卡罗瑟(Carother)对巨大分子的研究导致了尼龙的发明;布洛克(Bloch)和珀塞尔(Purcell)关于射频在磁场中被原子核吸收的基础研究,产生了磁共振成像技术;科恩(Cohen)和博耶(Boyer)发展的基因拚接技术,生产出比其他产品更好的胰岛素;哈根-史密特(Haagen-Smit)对空气污染物的研究,产生了催化转换器;赖尼泽(Reinitzer)发现液晶,将使计算机和平面电视屏幕发生革命性变化;激光的发现——起初是在实验室里的一种好奇心引起的——被应用于这样一些不同的领域:分离的全反维生素A酸的重新连接和超级市场里的条形码阅读。所有这些发现均在《科学与意外发现》这本小册子中有详细的介绍。伊莱尔进而指出:“从基础发现到实际应用之间的路往往很长,例如从尼龙需要10年左右,到液晶大约80年。”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我们现在停止进行基础研究,那么供给应用的`水井'到头来就会干涸。换言之,没有继续不断的基础研究,新技术的机遇最终就会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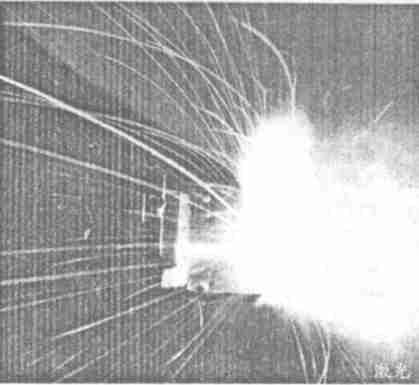
在《科学与意外发现》这本小册子中,收集了进一步论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的某些其他的题目,如涉及化学对药品影响的几个案例。美国实验生物学会联盟(FASEB)在1993年5月期的《新闻通讯》中,注意到了基础生物化学研究及其对社会所带来的好处。我从该联盟1993年5月出版的《公共事物通报》中引用了这样一些看法:“最近有人提出,基础研究和国家目标之间更密切的联系,应该成为决定对研究的支持的标准。他们还表现了这样的关注:科学本来是为了自身的目的而进行研究的,如果把这种研究引向更好地贴近特定的工业应用,它就对国家更有利。”他们进而指出:“但是,已得到的证据清楚地表明,这种期望的联系业已存在。实际上,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参与对通常的人类疾病的研究和治疗,并且与医学科学家有着密切的合作。参与生物医学开发的工业部门,已经从建立在主要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基础研究的基础上得到发展的治疗方法、并在商业应用中取得明显的效益。”
“维持以生物医学为基础的一个关键因素,对基础研究来说,是继续为它提供一系列能转化成新产品的思想和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是,要为一个基础研究的广泛基础提供适当的联邦政府支持,而不是将基础研究变成把重点放在指定的研究上,因为成功的途径是不可预测的而且变化很快。”
“历史已经重复地表明,在基础研究方面进行什么样的努力才会产生出关于如何才能防病和治病的洞察力,这一点是无法预测的;因此,重要的是要支持足够数量的有价值的基础研究项目,以便不错失机会。虽然基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填补我们在了解生命过程如何运作方面的差距,但它已经产生了大量的实际应用成果。我们认识到,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可能会尝试将有限的资金投向那些看起来很快就会得到回报的项目;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对大范围的非指定的研究的支持已被证明是更好的投资。它可以提供从中产生所有新的医学应用的更广泛的知识基础。同时,还必须根据对那些最有价值的思想进行判断,作出对什么样的研究应该予以资助的讨论。”
FASEB还继续对经济效益问题和一系列的由基础研究-驱动的医学突破的案例进行了讨论。“社会从基础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利益。由基础研究产生的技术,已经挽救了成百万计的生命,并节约了数10亿美元的医疗费用。根据国家卫生研究所对26%的在诊断和治疗方面取得进展的领域进行测算的结果,单单这些发明每年就节约了大约60亿美元。然而,这些由基础研究-驱动的发展的意义,远不只是降低了医疗成本:许多孩子和成年人的生命得救,而且还使我们的人民从疾病或永久性残疾的长期困扰中解脱了出来。精力更加充沛的、生产力更强的劳动力,会对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进步起正面的影响。
FASEB还进一步例举了13个基础研究对诊断和治疗疾病做贡献的案件,这些疾病大都是严重的。这份《公共事物通报》还指出:“我们预先知道所有有关的事情的能力是很差的(罗伯特 · 弗罗施语),在提出关于对科学资助的新思路方面,还从未考虑过“损害这一体系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未完待续)
[资料来源:www.nobel.se,2000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