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需要改变农业,使作物在气候真正变暖后仍然可以正常种植,在较少灌溉水和较少使用化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高产……”
――罗杰·N.比切
更多奥秘在等待人们揭示和发现
在科学界,从事植物叶柄的研究一直以来都不如对黑猩猩的大脑,或癌细胞突变激酶基因研究那么诱人,然而,植物世界却一直是无数基础科学发现的灵感。
比如,奥地利遗传学家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从对豌豆的研究观察中发现了遗传的基本规律,法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天文学家珍•杰奎斯•奥托斯•德•麦兰(Jean Jacques d'Ortous de Mairan)从向日葵的朝向发现了昼夜节律,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詹姆斯•萨姆纳(James Sumner)从刀豆中首次获得了尿素酶的结晶,包括诺贝尔奖得主芭芭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通过对玉米的研究获得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即被称为转位子(一种脱氧核糖核酸片断,它能够移到同一个或另一个染色体、质体或细胞上的新位置,并转录各种基因的特性,如对抗菌体的抵抗力――译注)的可转移基因,等等。
现在,植物在许多令人振奋的新领域中都引领了科技新潮流。比如,在了解基因表达的遗传变化,弄清楚有机体的遗传信息、外观和特征之间的复杂关系等,“植物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乔安妮•乔瑞(Joanne Chory)、霍华德•H(Howard H),以及索尔克研究所植物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实验室主任玛雅姆•R•纽曼(Maryam R. Newman)如是说,“植物学研究已经导致了基础生物学领域内的许多新发现。”
植物学领域内还有更多的奥秘在等待着人们去揭示和发现。比如,植物是如何将数吨之水传送到高耸的红杉树顶部;又比如,橡树强壮的树枝是如何承受地心引力和强劲飓风的。“植物结构的复杂性超出了工程师们的想象,”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艾略特•M•迈耶罗维茨(Elliot M. Meyerowitz)和乔治•W•比德尔(George W. Beadle)说,“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机制,将会在工程学领域内开拓新的视界。”
获取这些新知识不仅具有学术上的重要价值,同时还拥有许多实际用途。比如,了解荷尔蒙激素的复杂机制,就能用来控制植物的生长;了解植物的生物化学机制,就能让植物获得更强的抗病虫害能力和抗干旱能力。尤其是目前对于面临全球多种挑战的人类来说,这已经是当务之急。
而联合国的一些统计数字发人深省,预计到2050年,全球在目前68亿人口的基础上将再激增30亿,其中有近一亿的人口正在承受着营养不良的痛苦。同时,世界对能源的需求也在呈持续上升趋势,长期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后果正愈来愈明显,土地在需要生长粮食的同时,还要种植生物燃料作物,所有这些都对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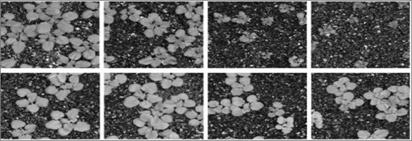
对于面临全球多种挑战的人类来说,加深了解植物的生物化学机制并以此增强其抗病虫害、抗干旱等能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包括气候变化正在带来或酝酿一些风险极大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威胁着地球上最重要的小麦主产区的秆锈菌Ug99的传播。因此,人类必须考虑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粮食和用作燃料或能源的植物材料。
“2050年左右将多增加30亿人口,但土地资源不会增加,淡水资源也不会增多,同时还要面对地球气候发生的重大变化,所有这些都将对农业产生重大影响,”美国粮食和农业研究所主任罗杰·N.·比切(Roger N. Beachy)说道,“我们需要改变农业,使作物在气候真正变暖后仍然可以正常种植,在较少灌溉水和较少使用化肥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高产。我们需要不怕虫害的植物,我们需要在气候变暖时不会生病的植物。”

“我们对遗传学的研究工具已经投入了许多,现在加大对植物学研究的投资时机已经成熟;未来意味着会有更多的回报机会。”
――菲利普·A·夏普
“新生物学”敦促投资植物学研究
2008年9月,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NRC)开始关注一些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食品、环境、能源、健康等――并探寻生物学研究可以做出最大贡献的一些领域。“很明显,几乎在所有上述领域内,植物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和主要来源,关键是能否及时获得解决方案,”NRC“21世纪新生物学”委员会副主席、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赫综合癌症研究所教授、诺贝尔奖得主菲利普·A·夏普(Phillip A. Sharp)说。而比切认为,有这么多的东西需要去学习和了解,他担心的是我们的学习速度是否足够快。
在面对如此多的紧迫任务面前,人们可能会认为植物学研究在世界各地都会得到重视和资助。中国近年来比较重视这方面的研究,在粮食生产不足的印度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但在粮食充裕的美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对植物研究却并不那么重视。在美国,生命科学中的植物学研究是最不为人关注的,联邦政府每年拨予生命科学研究400亿美元的经费预算中,植物学研究所占的比例不足2%,获大头的则是生物医学研究。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只对我们本身感兴趣,”乔瑞解释说,“国会的人往往将着眼点放在疾病和人类健康方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的农业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在不久前,联邦政府欲承担数十亿美元的代价在部分地区对种植业做出一些限制。“为什么要花钱去研究让农民生产更多作物的方法呢?”比切说,“正是我们的成功在一直阻碍着我们。”
研究经费之间的差距在美国的一些研究型大学中也非常明显。杰出的植物学家维基·L·钱德勒(Vicki L. Chandler)说,从事癌症研究的实验室往往拥有大量的博士后和研究生,而研究植物的科学家所获得的拨款只够支持一位博士后研究员和一位技师。如果要支撑一个卓有成效的实验室则“十分困难”,许多有前途的研究生必须放弃植物学研究才能找到有经费支持的项目。对此,比切认为,“如果仅仅是经费的原因而无法实现目标,这是一种耻辱。”
然而,并非都是坏消息。尽管支持度相对较低,植物生物学家和遗传学家在过去的10——15年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当乔瑞于1985年从细菌学研究转向植物生物学研究时,“已发现了一种植物受体,”她回忆说。如今,有了新的研究工具以及阿拉伯芥、拟南芥等植物遗传、生理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模式植物,植物生物学家对这些植物所进行的遗传基因测序获得了大量植物遗传学的知识。科学家们预言,植物基因组里存在着数百种基因编码的受体,目前已确定了这些已知植物激素的受体。
例如,光生物学家已经了解到,植物中的某种光受体可感知附近植物的荫蔽,从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说,它能感知到与其争夺阳光的竞争对手――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植物就会调整生长激素,加快其生长速度。当然,这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加速生长的同时,植物会降低对病虫害的防御能力。比如,植物群中的某一植物为争取在植物中长得最高的优势,即使意味着更容易受到虫害的侵袭也在所不惜。在研究中,乔瑞与德国图宾根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德特勒夫•威格尔(DetlefWeigel)还了解到,瑞典等受光照较低国家的植物,其感光受体的敏感程度是阳光明媚的西班牙同类植物的10倍以上。
“我们对遗传学的研究工具已经投入了许多,加大对植物学研究的投资时机已经成熟,”夏普道,加大投资“很可能会引发最大的知识爆炸,由于之前在该领域内投资严重不足,意味着加大投资会有更多回报的机会。”
机会在哪里?“下一个挑战除了产量,还是产量,”乔瑞说。这意味着要绘制出成百上千种植物的基因图表及其细节,然后再学会如何操纵这些基因。NRC在“21世纪新生物学”报告中指出:“我们目前拥有的只是植物零件的清单,而不是汇编指令。”
如果我们能够对玉米基因的汇编指令进行调整,是否能使其根系发展与土壤中的固氮微生物的关系更为密切,并以此减少其对肥料的需求?“确实有一些植物知道它们该怎么做,”钱德勒说,“甘蔗就拥有这种密切的关系,所以对氮肥的要求远远低于玉米。”
我们可以发挥充分的想象力,想象如何通过植物生长出大量的生物质原料,包括是否有可能对草原上的牧草进行一些生物学上的改变,即通过“生物学精炼”途径,将牧草细胞壁上的纤维素改造成乙醇或其他燃料等化学物质呢?对此,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杰拉尔德·芬克(Gerald R.Fink)、怀特黑德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玛格丽特·索科尔(Margaret Sokol)教授认为,“尽管目前这些还都只是科幻小说般的想象,但它有可能会成为现实。”
通过生物化学途径实现的看似微小的变化会产生巨大的差异。以植物最基本的功能为例,通过光合作用,将阳光的能量转换成为植物的茎、叶、种子和果实,这一过程的核心是一种称为Rubisco的酶――它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结合进生物质中。乔瑞说,Rubisco可能是地球上最丰富的蛋白质,约占植物叶片总蛋白的30%,同时它也是一种非常低效的酶。比切说,尽管植物只能捕获阳光照射中大约2.5%的能量,但若能进行基因调整以提高Rubisco酶对阳光能量的吸收率,比方说达到3%,“我们就可以解决世界粮食问题了。”
即使无法提高酶的效率,通过对整个光合作用过程进行基因工程的重新设计,也能提高效率。约3%的植物(包括玉米和甘蔗在内)采用的是C4光合固碳途径,固碳产生四个碳原子,而不是更为普遍的C3途径那样产生三个碳原子――C4途径不仅吸碳效率更有效,对水分的要求也更少。因此,若将C4途径加入到C3植物中,可大大提高其生长速度,同时也更为耐旱。据剑桥大学的朱利安·希伯德(Julian Hibberd)估计,加入C4途径基因工程改造的水稻产量可提高50%。

“植物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真正伟大的系统。当植物组织的种子被赋予表观遗传模式时,甲基化的变化就转移到了下一代。”
――瑞恩·利斯特
需要资金投入的同时更需要知识
当然,改变生化途径不仅仅是加入新基因那么简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刚发现了如何对植物进行基因工程改造,那时有许多的期望,希望它能迅速带来一场农业革命,”比切回忆道(比切在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实验室研制出了第一个基因工程抗病毒作物)。比切说,当时基因革命的主要重点是放在对需要较少杀虫剂和对除草剂有耐药力的作物上。由于玉米、大豆和棉花已通过转基因技术获得了抗商业化除草剂和杀虫剂的能力,新技术研究资金的投向主要集中在孟山都、杜邦/先锋种子等公司。而对能在本质上提高产量、减少肥料需要、抗旱抗严重病虫害,或拥有更高营养价值植物的研究进展却迟迟未能出现。
比切认为,部分原因是,消费者一直不愿为更具营养价值的食物付出更多,一些对于第三世界至关重要的作物,如木薯或大米改进的研究,获得的支持很少或根本没有。即使是像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那样,想通过积极开发营养价值更高更耐旱的作物,来致力于解决世界各地的饥饿和贫困问题时,“他们却发现没有足够的科学知识来达成目标,”比切说,“于是他们决定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合作,希望通过科学家来填补知识上的空白。”
其中一些所需的知识包括如何更好地了解基因调控的原理。事实证明,植物非常擅长利用一小点的RNA来控制它们的基因。理查德·A·约根森(Richard A. Jorgensen)于1986年首次观察到这一现象,当时他在DNA植物技术公司工作,他想,如果通过增加一个紫色基因到矮牵牛花中,创造出一个特别耀眼的紫色花朵的矮牵牛花,一定会引起投资者的惊叹。但他创造出的转基因牵牛花开出的却是白色的花,其中的缘由花了十年时间才搞清楚。原来利用自身那一小点的RNA,植物细胞能够检测和销毁来自RNA的病毒,或来自其自身沉默基因的威胁,科学家面临的挑战是要在大量不起任何作用的RNA转录中找到起关键调控作用的microRNAs。钱德勒说:“大量信使核糖核酸在形成过程中,其中许多有可能是垃圾RNA,但为什么植物要浪费大量能量劳而无功地进行这种RNA转化呢?看来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至今还弄不明白的。”
了解多种类型的小RNA分子如何控制植物基因,在科学研究和农业生产上都将会获得丰厚的回报。钱德勒说:“很明显,温度变化和生长状况可能对基因沉默的数量产生影响。”最近对大麦的研究表明,生长在不同海拔高度的这类植物有着不同类型的转位子活动模式,并通过小RNA进行调控。夏普说:“以RNA为介质的调控是一项非常成熟且非常激动人心的研究。”因此,了解这种基因调控机制可以帮助作物适应诸如干旱或高温等灾害性气候。

甲基化标志着一个基因是否处于开/闭状态,而当植物组织的种子被赋于同样的表观遗传模式后,其基因通过改变后可能会固定下来
如果说以RNA为介导的调控机制还不太复杂的话,那么还有另一种级别的基因控制,即附着在一个基因上的甲基的数量控制着细胞合成蛋白质的多少,这种控制被称为表观遗传学。在包括植物在内的许多有机体中,甲基化标志着一个基因是处于打开状态还是关闭状态,这种甲基化模式是可以遗传的。而植物的茎和叶承受到的环境压力可能会导致甲基化模式以及基因表达的转变,因此,索尔克研究所的植物遗传学家瑞恩·利斯特(Ryan Lister)指出,当植物组织的种子被赋予了同样的表观遗传模式,甲基化的变化就转移到了下一代。“由此看来,植物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探讨的真正伟大的系统。”
这方面的研究在科学上获得的回报远远超出植物本身。利斯特以完善的方法读取了拟南芥表观基因组(为读取第一个完整的人类表观基因组铺平了道路),并发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甲基化模式。这只是取得的许多进展之一。正如2010年9月《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杂志的社论中所说的:“拟南芥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模型系统,对更好地了解人类健康和疾病起到了很大的启示作用。”
表观基因研究还为调控植物的生长速度、对环境压力的承受力以及提高产量提供了新的控制杆。事实上,研究人员猜测,植物很有可能使用表面基因的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钱德勒解释道:“植物的表观基因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可能是这样一种机制,在多种调控途径中进行尝试,之后可能通过基因改变固定下来。”

“要了解某种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大学将无法培养出创造高产作物的研究人员。”
――乔安妮·乔瑞
令人振奋的科学新前沿
所有这些新发现对科学家来说十分诱人,但钱德勒指出,“我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比切和其他一些人认为,如果研究植物的科学家团队与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合作,采取更广泛更系统的研究方法,这一领域内将会有更多的发现。例如,为什么某些植物会形成共生植物群?这种生态系统是如何形成的?乔瑞说:“要了解某种生态系统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下,植物研究的另一条主线是,随着环境变化压力的加重,如何面对植物病虫害可能加剧的问题。对此,美国植物生物学学会执行理事克里斯平·泰勒(Crispin Taylor)说:“一个系统的生物学方法可以观察到植物某种病原体分子结构的详细情况,以及给植物带来的种种压力所产生的变化。”
加州理工学院的迈耶罗维茨(Meyerowitz)说:“通过数学与工程学的结合,以了解植物的生长机制,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研究前沿。”例如,一棵树的分支结构,是基因和机械应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因为这种互动以及细胞的实际物理结构形成的树木的分叉结构,可以用数学方法建立起某种模型。
然而,大多数的实际应用还有待于未来的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项目有提高高粱的营养成分、提高植物根系对氮的吸收能力、给木薯等作物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以及更好地了解我们从植物中获得的营养与人类健康之间的联系等。孟山都公司的科学家已经承诺,力争到2030年将玉米、大豆和棉花的产量提高一倍。对此,夏普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于所有这些可能性,我们只是做了一些粗浅的尝试而已。”


孟山都公司承诺,力争到2030年将大豆、玉米、棉花的产量翻一番
总而言之,植物学研究的成果不仅在神经科学、癌症生物学领域内令人兴奋,同时还提供了一个拯救世界的机会。科学家指出,推动植物学研究的发展将有赖于各方面的支持。夏普说:“种种机会就在我们眼前,但植物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境。”而比切担心的则是基础科学的研发和公司开发能力之间的巨大差距,眼前的重点应放在能够获得快速经济回报的产品之上。他说:“目前尚未有足够的资源与途径来填补这一差距。”
乔瑞指出,如果没有更多的资金用于基础研究,大学将无法培养出行业所需要的创造高产作物的研究人员。迈耶罗维茨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做得不够好,但我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不会再为这个问题而困扰。”
资料来源 http://www.hhmi.org/
责任编辑 则 鸣
――――――――――
本文作者约翰·凯里(John Carey)为资深科普作家,31年前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林业科学与环境研究学院,之后曾考虑攻读林学博士,后投身于新闻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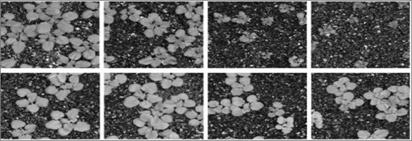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