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瞄准的靶子是我们的头脑――什么样的武器才是最可怕的武器?本文构思的“人工智能纳米微粒”能够以风为携带者,顺势进入目标者的头脑,进而影响控制他们的意识。中国古诗词中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种武器显然能达到这种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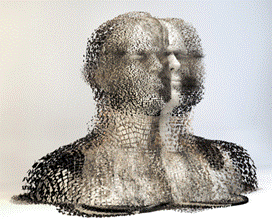
在这个地方生活的第16天,我企图自杀。他们犯了个错,给了我一把刀子在吃东西时用,我抓起那把刀子,剥下我的紧身衣,在两边的手腕上切出两个大口子,注视着深红色的花朵迅速绽放。
在我的鲜血流尽之前,他们抓住了我。守卫按住我,约尔科维医生给我注入了满满一剂医疗胶水,给我的伤口喷上生物泡沫。“行了,”当躺着的我瑟瑟发抖、最后一段快乐的记忆在头脑里跳动的时候,她低语道,“我们会把它弄出来。我们会找到办法。”
我为他们打了一场战争,他们却仍然不肯让我就此死去。
他们没有再用从头到脚的约束服将我捆起来,而是把我送入一个新房间。约尔科维医生建议说,变换下周遭环境也许对我有好处。我知道这不会有一丁点影响。
“试图离开?”当我在长凳上坐下,“除尘者”从我后脑勺嗤笑道。这个邪恶的似男似女的嗓音吸干了全部暖意,“你可不会那么轻易地离开。”
“闭嘴。”我低声说道,“留下我独处就行。”
我犯了个错误。这个人工智能的反应只是哈哈大笑:“哦,别科夫,你晓得事情不是这么进行的。”
我们的第一个错误是以为敌人会用常规武器进行袭击。恰恰相反,他们释放了人工智能纳米群到空气里,伪装成尘土微粒。风承担了余下的工作,几天之内,我们的一半军队人员的头脑里都被植入了敌方的人工智能微粒。它们被写入的程序就是要憎恨我们,鄙视我们,折磨我们。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给我们展示一些根本不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大批士兵失去理智,丢掉了性命。但我仍然坚守着。
幸运的我。
“他们永远无法摆脱我们。”“除尘者”说道。我转过脑袋,仿佛这样能帮上忙,“你永远不会再见到金姆。”
我的肌肉紧绷得像大桥钢缆,“你怎么知道金姆的名字?”
“你想起了我。”这时响起金姆温柔的嗓音,她的声音总是能抚慰我,“你的最后一段快乐的记忆。你让我能够访问到她的记录。还有你俩在一起的最后时刻。”
我用两侧手掌紧紧按向太阳穴,“让她离开这儿!”
“总是想着她只会让情况更糟,”“除尘者”说道,声音恢复了正常,“我们读到你的大脑突触。你的神经传送体――你的所有记忆、情感和身体反应――它们就是燃料。”一阵汩汩声掠过我的头颅――一些接近于要笑出声来的感觉。“你想到它的时间越久,你越会给予我玩弄的机会。”
“去死吧!”我尖叫起来,恐惧的卷须在我体内蠕动,“只要停下,只要――”
我的心脏提到了嗓子眼。密室的墙壁消失不见了,我凝视着曲线弯曲的金灿灿的沙滩。风爱抚着我因为汗水而变滑的皮肤。海浪拍打在海岸上。金姆站在沙滩上,微笑着,红色的头发在微风中飘动。
“过来。”她低声说道,向我打起手势。
“你怎么在做这事?”随着我离家参战前的最后一天的画面消失不见,我此刻颤抖起来,胸膛缩紧。
“我在你的头脑里待得越久,扎根也就越深,”“除尘者”奚落起来,“想要见识一下吗?”房间呈现出苔原上的寒意,周围森林逐渐成形。白雪撒满了地面。我看见自己所在的班组徒步穿行于乌拉尔山脉。我注视着好友米哈伊尔在一处岩脊上滑倒后跌下山,他的尖声惨叫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随着记忆在我面前回放,我向后却步,止不住地哆嗦。米哈伊尔的尖叫声变得越来越响,雪花落到我的肩上,我告诉自己,这不是真的,眼前这一切都没有一样是真的。这只是“除尘者”在玩弄我的头脑。
“停下!”我咆哮道,用双手抓住脑袋,“别来玩弄我!拜托了!”
“我们甚至能改变你的身份。”“除尘者”说道。我透过泪水沾污的视界,看见镜中的我自己。我的斯拉夫人五官消失不见,我眼前凝视着一张金发碧眼的北欧人脸庞,接着又变成瘦削、高颧骨的非洲裔加勒比人脸庞,最终渐渐转变成一个大腹便便的东亚男人。“够了!”我尖叫起来,同时抓住我此刻的黑色头发,“够了,你这个怪胎――”
画面凝结,我现在成了个女人。随着每一秒逝去,我变得越来越苍老,皮肤上出现皱纹。“你甚至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对吧?”“除尘者”嘲笑道。
“住手!”
“你谁都不是。”我的身体开始褪色;仿佛我正在遭到涂抹,“你压根不存在。”
我尖叫起来,当我将脑袋砸向镜子玻璃时,嗓子毛糙得像砂纸。世界开始眩晕。镜子变成蛛网状,一片玻璃坠落到地上。气喘吁吁的我捡起玻璃碎片,将它戳入我的手腕皮肉内,像耙子一样割到手肘关节处。镜子碎片剐擦到骨头,同时我的皮肤裂开来,暴露出满是血污的静脉、肌肉和动脉网络。温热而富有光泽的鲜血泉涌而出,我的手臂疼得像着了火。我极其痛苦地倒在地上,等待最终结局将我吞没。
“你真以为他们会给你一面镜子?”我抬起头。墙壁上什么都没有,只有我用额头撞出的一块凹痕。我的手臂也完好无损,地上没有血迹,也没有玻璃碎片。“我告诉过你,你没法那么轻易地逃离。”
我头晕目眩,抓住我的手腕,试图用指甲将手腕切开。怒火减退后,我跌坐到地板上,啜泣起来,同时海滩上的笑声围绕着我,咸苦的海水在我周围旋动。凉爽的海浪拍打我的双脚,金姆热热的气息喷到我的脖子上,她不停地叫我过去,让我感受一下趾间的沙砾。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杰里米·绍尔(Jeremy Szal)居住在澳大利亚悉尼,他的作品刊登在《自然》、《光速》和其他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