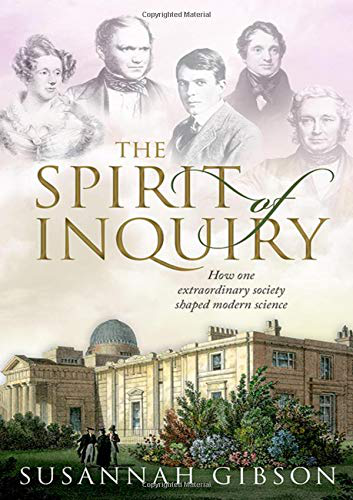19世纪,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发生了重大变革,但这场变革的源头出人意料。在本文中,乔治娜·费里(Georgina Ferry)会把这段历史为我们娓娓道来。2019年,乔治娜·费里为多罗西·克劳福特·霍奇金(Dorothy Crowfoot Hodgkin)撰写的传记将会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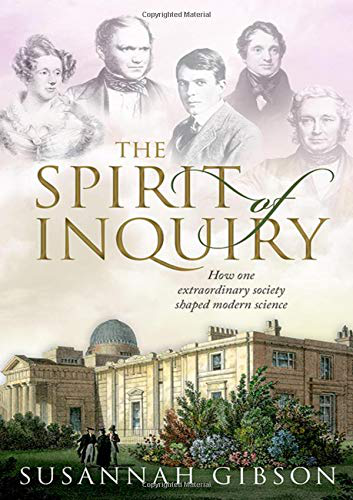
《探究精神:一个非凡卓越的学会如何塑造现代科学》(The Spirit of Inquiry: How One Extraordinary Society Shaped Modern Science ),苏珊娜·吉布森 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 年。图中的剑桥大学天文台建于1823 年,在剑桥哲学学会成立4 年后
1873年,Nature杂志的一位记者忧心忡忡地写道:“科学在英国已经消亡殆尽……而大学或许是科学最没有活力的地方。”这篇匿名发表的文章,标题叫作“剑桥之声”,其观点完全正确,比如,当你把当时的英国大学和德国大学放在一起比较时,就能明显感到英国大学在科学研究上处于下风。
长期以来,化学、生理学以及实验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始终没能成为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重点。在长达700年的历史中,这两所大学都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训练年轻人成为教堂牧师之上。对于那些出身更加“高贵”的学生,牛津和剑桥则更多地扮演了精修学校(教学以上流社会的礼仪、规范为主)的角色。然而,到了19世纪中后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873年,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一样,开始着手建立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物理实验室,剑桥大学第一位卡文迪许物理学教授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也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论文《论电和磁》(Treatise on Electricity and Magnetism)。从1861年开始,剑桥大学的本科生已经能够获取为期3年的自然科学学位。是什么推动了这些变革?
历史学家苏珊娜·吉布森(Susannah Gibson)认为大部分归功于剑桥哲学学会。她把自己的精心研究汇编成著作《探究精神》,并提出:剑桥哲学学会最终把剑桥大学改造成我们今天熟知的引领世界的科学中心。在2018年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剑桥大学名列自然科学榜的第二位。
19世纪初,“自然哲学”方面的发现正成为流行文化中的一部分。“科学”一词还需要获得其现代含义,而“科学家”一词直到1833年才创造出来。这个词的创造者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就是剑桥哲学学会的成员。当时,地方哲学学会在英伦大地遍地开花,从普利茅斯到格拉斯哥随处可见。哲学学会为求知欲旺盛且能够负担会费的人士提供了聚会和聆听关于最新发明、发现讨论的机会,讨论的内容从化石收藏到蒸汽机车。若干哲学学会(包括纽卡斯尔和布里斯托尔的哲学学会)从成立初期就对女性开放。
不过,剑桥哲学学会有些不同。由剑桥大学伍德沃德地质学院教授亚当·塞奇威克(Adam Sedgwick)和他的朋友、博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John Stevens Henslow)于1819年创办的剑桥哲学学会只接纳剑桥大学学生,宗旨则是“促进科学研究,并且……提倡与哲学进步有关的内容交流”。正如吉布森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要想达到促进科学研究、交流的目的,创立学会要比改革大学容易一些。
剑桥哲学学会邀请会员参加每两周一次的晚间聚会。会上,会员可以发表演讲和展示自己的成果。会员讨论了首任学会主席的威廉·法里什(William Farish)的工业机械黄铜模型,讨论了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e)关于在英国矿石中观察到镉的声明(镉才发现没几年)。剑桥哲学学会还出版了自己的期刊,其质量甚至能与伦敦皇家学会期刊一较高下,不过,这份期刊此后经历了一段低迷期。
大量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现最初是在此类聚会上进入公众视野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小猎犬”号旅途中写信,亨斯洛在1835年11月向剑桥哲学学会成员宣读了这些信,此时,达尔文正身处塔希提岛。许多物理学发现都是在这个学会上首先亮相,包括J.J.汤姆逊(J.J.Thomson)寻找电子的实验、劳伦斯·布拉格(Lawrence Bragg)对其提出的晶体X射线衍射定律的解释、查尔斯·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云室发明以及鲁道夫·皮尔斯(Rudolf Peierls)对启动链式反应所需铀的临界质量的估算。
当时,几乎所有剑桥大学的活跃研究者都是剑桥哲学学会成员,而那些在学会会议上表现出众的年轻人也更有机会谋得剑桥大学教职。这个双向通道为将实验科学逐步纳入本科生教学体系开辟了道路。剑桥大学开始以兴建实验室、设立研究奖学金和研究生学位的形式为科研提供正式支持。剑桥哲学学会还把其精心分类和编制目录的博物学标本捐献出来,帮助剑桥大学建立动物学博物馆。该标本包括博物学家伦纳德·杰宁斯(Leonard Jenyns)在剑桥郡发现的大量动物标本以及达尔文在“小猎犬”号之旅中收集到的鱼类标本。

博物学家约翰·史蒂文斯·亨斯洛
剑桥哲学学会还建立了与全世界学术团体(其中包括美国哲学学会和法兰西学院)进行期刊交流的系统,并因此以极低成本建立剑桥无与伦比的合订本期刊图书馆。1866年,当学会因员工资产管理不善而被迫出售房产时,剑桥大学为许多书卷提供了储存之地。自此,剑桥哲学学会图书馆实际上已经成为剑桥大学的科学图书馆,并且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纳入剑桥大学图书馆系统。
虽然学会会员可以在聚会时携女性(以客人身份)前来,但学会的前瞻性思潮并没有立刻延伸到性别平等这个方向上来。1831年,塞奇威克曾竭力推动女性数学家、作家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入会,但最终以失败告终。在剑桥哲学学会发表论文的第一位女性是爱丽丝·约翰逊(Alice Johnson),她是剑桥大学纽汉姆学院毕业生,于1883年在学会会议上作了鸟类与恐龙解剖比较的论文报告。纽汉姆学院是1871年专为女性成立的学校,并且拥有自己的实验室。另一位纽汉姆学院毕业生安娜·贝特森(Anna Bateson)也向学会提交了数篇论文,不过,往往是由她的兄长、遗传学家威廉·贝特森(William Bateson)代她在学会会议上宣读。1929年,剑桥哲学学会终于开始接收女性成为会员,比英国皇家学会早了16年,也比大学授予女性正式荣誉学位早19年。
吉布森仔细研究了2014年归档的学会相关档案,研究结果巩固了她“剑桥哲学学会影响力巨大”的论断。大量信件、会议记录、财务账目以及图书目录让我们得以从日常生活的独特视角看待伦敦哲学学会会员的研究发展之路。当然,我们同时也会看到一些启发意义不那么强的“旁门左道”。受统计学家、优生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开创的人体测量学热潮影响,学会于1886年建立了测量本科生及其他人群头部大小的实验室,试图借此将人类头颅大小和智商联系起来,这显然是误入歧途。记载着原始实验数据的卡片如今仍旧保存在档案中,最初分析这些数据的是约翰·韦恩(John Venn),后来则改由统计学家罗纳德·费舍尔(Ronald Fisher)进行更为严格的分析。
吉布森不止一次在书中提到,剑桥哲学学会是当时科学发展的“缩影”。这个词汇用得颇为恰当,但吉布森还是反复提及,并且这也不是她在书中反复提及的唯一词汇,似乎这位作者不太相信读者的记忆力。
那么,如今这个学会自身又变成什么样了呢?它仍旧是每两周举行一次会员聚会,只是现在的聚会已经把关注重点部分转移到公众参与,而不只是单纯讨论最新研究成果。此外,学会还会给处于科研生涯初期的科学家提供一些津贴。正如吉布森在书中描述的那样,剑桥哲学学会已经“成为剑桥大学宏伟科学事业的一小部分,而这也是学会取得成功的真正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