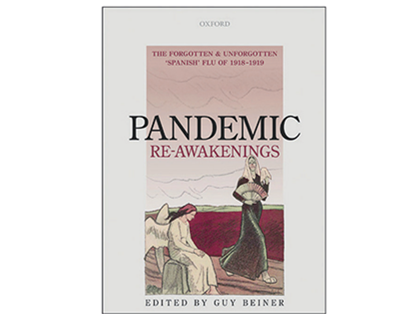《大流行的再觉醒:被忘却和未被忘却的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盖伊·贝纳编著,牛津大学出版社,2022年
1989年,医学史学家查尔斯 · 罗森伯格(Charles Rosenberg)写下了一段著名的话语:“流行病需要强调的决定性特征是它们的事件性。真正的流行病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种趋势。它引起即时、广泛的反应。它是高度可见的,并且,不同于人类生物史的某些方面,它并不会悄无声息地推进,直到事后才被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回顾性地发现。”不过,在盖伊 · 贝纳(Guy Beiner)编著的文集《大流行的再觉醒:被忘却和未被忘却的1918—1919年“西班牙”流感》中,罗森伯格颇具说服力的观点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
本书是2019年在法兰克福举办的两场研讨会的成果,以纪念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一百周年。与会的历史学家们讨论了这场流感大流行如何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开来,从而以全球性的视角看待那个“传染之年”里发生的种种事件。书中所有的文章都是在“记住”这些“被忘却”的事件这一前提框架下所写的。本书提供了这样一个视角:第一次世界大战如何将病毒扩散和传播到了全世界?这场冲突又是如何将爱国主义战争精神与公共卫生努力和公民责任结合了起来?作者们对比了人们庆祝和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方式,这些庆祝和纪念的喧闹往往掩盖了受讨论较少但与之同时发生的流感大流行。
贝纳这本书中的文章也尝试捕捉受难的幸存者、护士、医生、少数群体成员和士兵的声音,而这些仅仅是历史舞台上众多“无名演员”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历史学家的典型工坊(即档案室)中存放的相关证词非常之少,而且,正如书中各章节所呈现的那样,研究这场大流行的医学史学家必须时常依赖当事人传给亲属和后代的故事,这自然是一种记忆的形式,但比起个人回忆录、明信片和信件更为不准确。
除去新冠大流行之外,1918—1919年的流感大流行很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研究最广的大流行。至少自1919年起,流行病学家、病毒学家、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就一直在分析这场传染性危机,并且这项工作从未真正停止过。在报道更近期的季节性流行病时,记者们也经常引用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期间的老故事。这场大流行也激发人们创作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和短篇故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医学史学家反而要被提醒才能想起,这是迄今为止全球经历过的最致命的大流行。
“忘却和记忆”算得上是个具有挑战性的主题。毕竟,公众中有谁能够详细回忆起1957年、1968年,或是最近的2009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呢?谁还记得1858年的英国猩红热暴发呢?当时的疫情吓坏了一位富有的、名叫查尔斯 · 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维多利亚时代人士,他带着家人离开了位于肯特郡唐恩的家,前往怀特岛。除了一些学者之外,还有谁能背出1892年霍乱大流行的相关史实呢?除了研究该领域的历史学家以及仍然在世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家人,谁还记得1916年和1932年两次可怕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呢?仅在美国,该病就致使数万儿童死亡、导致更多儿童瘫痪。谁还记得1954—1955年的脊髓灰质炎疫情?那次疫情在美国感染了近4万名儿童,使其中近2万名瘫痪,而就在短短一年后,乔纳斯 · 索尔克(Jonas Salk)的福尔马林灭活脊髓灰质炎疫苗便会问世。人们当然记得索尔克疫苗,但是20世纪上半叶这么多个夏天所见证的病例和死亡却很少为人们所纪念。
我本来还希望,在这本出版于新冠疫情阴影下的书中,能对一些相关的当代背景进行更多的讨论。我想知道为什么很少有人提到公共卫生官员如何与医学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合作,协助发明了“拉平曲线”的概念、研究出了它的证据基础——“拉平曲线”指的是通过保持人身距离、检疫隔离和医学隔离来减少病例,从而降低高峰期的入院人数,减轻对医务人员和医疗基础设施的压力,以争取时间,直到开发出疫苗。这些方法的重新出现,部分是基于对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历史-流行病学和统计研究,以及超过43个美国城市的经验,当时,这些城市采用了检疫隔离和医学隔离的非药物干预措施、禁止大型公共集会并关闭了学校。从事这些研究的历史学家,包括我在内,访问了数百个档案馆,收集了数以万计的文件、报告、科学和流行病学研究、日记、报纸报道和其他材料,以表明虽然这些城市都采取了一定的非药物干预措施,但并非每个城市都发挥出了这些措施的最大优势(甚至是任何优势)。事实证明,那些及早、同时、长期实施不止一项非药物干预措施的城市,其发病率和死亡率远远低于那些没有这么做的城市。这些研究是在2006年由时任美国总统乔治 · 布什(George Bush)下令开展的,研究结果在2007年公开发表,成为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大流行准备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研究的结论不仅可以在模型研究中重现,还在2009年H1N1流感大流行早期于墨西哥传播时得到了重现,当然,在新冠全球大流行期间,这些结论也再次得到证实:封锁令、保持人身距离和其他新冠控制措施拯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降低了感染率。所有这些努力都在所谓“历史的初稿”,也就是纸媒、科学和医学期刊,以及全球的电子媒体上得到了广泛的报道。然而,本书中唯一一次提到“拉平曲线”这个字眼是在引用某位新西兰官员的一句话时,而这位官员显然不明白检疫隔离是这个概念的组成部分之一。哎呀!我猜他们是忘却了。
撰写这本书的历史学家们似乎未能充分注意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诸如流感和新冠等流行病及大流行的最终结果总是让那些参与保护公众健康的人感到烦恼,因为它们的结尾往往和看起来一样模糊。有时候,像新冠这样,是政客们声称危机已经结束,其动机也许是经济问题、政治游戏,又或者他们只是感觉到公民已经厌倦了遵守规则和政策,尽管这些方法有助于保护公民们、让他们保持健康。一旦流行病销声匿迹,易感人群或是死去,或是康复,或是逃过感染,生活最终会恢复到大流行前的模式。很多时候,这些事件的结尾是平淡而反高潮的。借用艾略特(Eliot)的诗句,公共卫生危机淡出视野的方式通常“并非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自阿尔弗雷德 · 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出版有关1918—1919年流感大流行的权威历史书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十年:1976年的第一版题为《流行病与和平》,1989年的第二版题为《被遗忘的传染病》。从那时起,一大批医学史学家、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编剧以及其他许多人一直在“提醒”他们的读者一场似乎没有人能够忘记的大流行,而这些著作都出现在新冠病毒潜入地球之前,其中一些甚至在克罗斯比的书出版之前就已经问世了。因此,在我看来,《大流行的再觉醒》是一本令人困惑的书,它借鉴了本书许多撰稿人之前在其他出版物上已经提出过的论点。
传染性危机几乎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告终:人们健忘地回归到同一套社会和公共卫生环境中,尽管最初或许就是这样的环境滋生了这场危机。阿尔伯特 · 加缪(Albert Camus)那富有感染力的杰作《鼠疫》(La Peste)在其结尾的数句话中记下这种全球性的健忘症。正是这种心态威胁着未来仍将遭遇流行病和大流行的世界。“里厄倾听着城中震天的欢呼声,心中却沉思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因为这些兴高采烈的人群所看不到的东西,他却一目了然。他知道,人们能够在书中看到这些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
当我们反思新冠病毒如何彻底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时,加缪《鼠疫》的最后几句话很可能是现代文学中最悲伤、最雄辩的结尾之一。
《大流行的再觉醒》为“发现过往大流行”这一已经人满为患的历史研究领域添上了一份新材料。这些危机应该提醒我们的是我们不敢忘记的事情:我们需要处理的那份漫长的传染犯罪嫌疑人名单——无论是携带传染病的动物、高傲的政府,还是隐瞒或加剧正在酝酿的流行病、全球化、气候变化的不诚实而好斗的政客,甚至可能是试图将微生物武器化的恐怖分子。新冠大流行还暴露出许多我们必须立即解决的问题,例如健康差距和太多人无法获得足够的医疗服务(这加剧了新冠对全球最贫困人群所造成的过于严重的影响),例如对基本公共卫生规划和执行的投资不足,以及各城市、各州和各个国家之间的过多互斗,这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推迟或阻碍了医疗和公共卫生反应。这些威胁,以及更多的威胁,都代表着21世纪生活所面临的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危险。当然,难以忘却的教训是,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以预防或至少是遏制下一次大流行。
资料来源 The Lancet
——————
本文作者霍华德·马克尔(Howard Markel)是美国医学史学家、医生、密歇根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