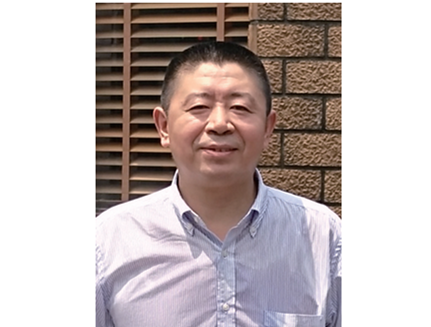李侠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教授
进步概念是启蒙运动的产物,自18世纪以来,这种乐观的信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并被拓展到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科学领域自然是这种信念的最坚定捍卫者。近代科学的400年间一次次伟大的科学发现巩固与强化了这种信念,美国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更是用实证的方法指出,在剥离资本和劳动对经济增长贡献后的剩余部分完全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因此,全方位审视科学进步的发展路径与模式,实现科技进步加速,逐渐成为当下科技管理部门的关切,这也是制定高质量科技政策的基础。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少应思考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是通过缓慢的积累还是激进的革命模式实现进步的?结合本期专稿相关观点,笔者认为科学沿着进化与革命交替出现的方式发展,在宏观上呈现为“间断性平衡”的特点,即科学进步主要以逐渐进化为主,科学革命则是稀少的。第二,小科学时代和大科学时代的科学进步模式有何区别?二战以后,科学完成了从小科学到大科学的转变,知识生产的复杂性快速增加,科学主体也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向集体合作的转变,如16世纪哥白尼的日心说,17世纪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到20世纪初普朗克与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与相对论等。而大科学时代,科学进步严重依赖资源,科学成就大多呈现为由国家或机构主导的跨部门集体合作取得,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以及“人类基因组计划”等。这些资源包括政策支持、经济投入、配置仪器设备、培育人才以及构建友好科研生态等,这些都是小科学时代所不具备的,甚至是不需要的。当知识生产链条越来越长也越来越复杂时,协同就越发困难,这也可能是大科学时代不容易出现科学革命的深层原因之一。第三,当下应如何构建短期改革路径以及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来推动科学进步?笔者认为科学进步正呈现以下趋势:其一,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是按照渐进模式发展,而大科学时代,常规科学的持续时间将缩短,科学革命的频率将加快;其二,人类获取新知识的能力也在增强,借助各种仪器设备技术的强大功能,原有范式快速到达其内在的边界与天花板(知识的纵向拓展)。在这些趋势中,科技管理可侧重创建优良科研生态系统,清除科研规范系统的“藤壶效应”。
由于当下的知识生产是集体合作的产物,而全世界在科技领域尚未形成一套公认的成熟且完备的集体行为组织范式,为了规避这种困境,各种评价体系与激励机制日趋复杂,规范层层嵌套与累加,最后导致科研生态系统出现不堪重负的“藤壶效应”,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扼杀了科技建制与科技共同体的活力与创造力。建议清除各种不合理规范和不合时宜的繁文缛节,增加科技伦理等符合时代发展的新规范。2018年以来推出的破四唯/破五唯就属于清除藤壶行动的代表举措。同时,应坚持长期主义,提供稳定的政策与资源支持,推进制度与组织创新,快速形成比较优势。以往的研究已经证明,哪里率先形成最优科研生态环境,哪里就更容易促进科技进步,甚至会出现科学革命。对于中国科技界而言,充分利用已有知识与创新优势,最大限度地缩短常规科学时间,加快科学进步的间断性平衡的频率与进程,以期尽早引发科学革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