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罗姆 • 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富有意义的行动(Acts of Meaning,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一书中写道,自传是一种奇特的文学体裁,“是由作者在一定时间一定 场合对在某时某地负有其名的故事主角所作的叙述。......这种长篇大论往往词藻华丽而又巧言善辩,似乎是要证明故事主角走上一条特别的人生之路是必然的。作为讲述者自己,不仅要进行详细叙述而且要证明其非常正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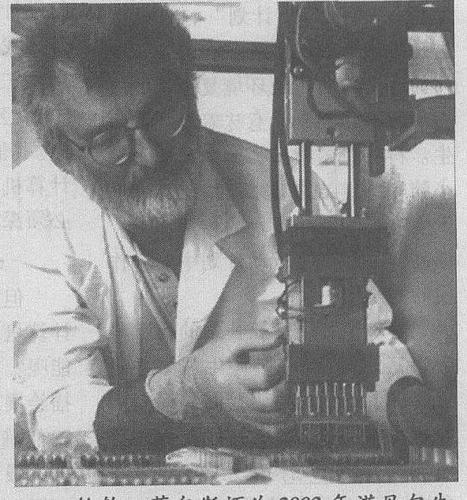
约翰 • 萨尔斯顿为2002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自传总是那样掺入了各种预想成分,约翰 • 萨尔斯顿的《共同的生命线》也不例外(萨尔斯顿虽然有一位合著者——科学作家乔治娜 • 菲莉,但全书是他以第一人称方式进行叙述的)。首先他在书中叙述了他个人的各种预想,如他本人为人谦和而从不摆架子的个性、他“对物质财富的冷漠,......人应以大众利益为重的超然意识”等等。萨尔斯顿说,这些准则已经构成了他对待科学研究特别是对待沟通科学信息的观念。其次是他自己的专业发展可以向人们提供对人类基因组计划历史了解的设想。萨尔斯顿通过提供这一大规模科学计划的进程和探讨其从一个小型集体活动到一项庞大商业冒险的转变过程而把个人经历与专业发展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既有颂扬又有评论的故事。
萨尔斯顿成为一位研究基因组学的科学家生涯是从1969年开始的,那年他加入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设于剑桥的分子生物学实验室(LMB)。他怀着对过去非常留恋的心情回忆说,他一度从事线虫遗传学的研究,其研究是纯学术性的,不存在经济利益或什么其他目的。对于萨尔斯顿来说,LMB是一个以信息互通和密切合作为特征的理想环境。线虫研究人员都把LMB线虫研究课题组看作是“麦加圣地”。
那种科研氛围显然是富有成效的,孕育出了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萨尔斯顿也是诺贝尔奖得主之一,后来他在绘制和测序人类基因组这项国际性合作攻关中成了主力队员,并最终成为著名的剑桥桑格中心主任。
萨尔斯顿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来描述在这项大规模基因组计划背景下他I约自己的战略决策。其中最麻烦的问题,以及他在书中所叙述的问题,都和基因组学的商业方向有关,这种获利的可能性使正常科学竞争的影响、颇具争议的专利权问题,特别是关于使用基因序列数据的争论都扩大了。萨尔斯顿的早期研究经历使他始终关注着共享科学信息和思想的重要性。他详细追溯了詹姆斯 • 沃森(James Watson)和克雷格 • 温特(Craig Venter)之间关于基因序列能否获取专利的著名争论,并很挑剔地调查了美国专利局过早授予的基因序列专利。萨尔斯顿虽然很留恋他那老式的研究实验室,他自己却被人拉进了依赖于各个商业组织并将决定这个发展中领域进程的大型管理机构。1989年,他在100万英镑的津贴面前就“卑躬屈膝”地接受了,而且仅3年之后,他就申请要5000万英镑的津贴。
萨尔斯顿的平铺直叙传达了关于他自己与这个迅速变化的科研领域所涉及事件的某种自我意识。他谈到必须穿着“不习惯的衣服”来面对媒体,以保持他作为一位临时科学家的自我形象。但是他把他作出的决定解释为“对线虫进行深入研究”的唯一途径。 他担心大家专心于科研“竞赛”只是为了获取财利而不是为了它的潜在意义。但他又发问,一个人怎能对国际合作组织强加限制呢?他悲叹那种视科学为技术开发的观点,并且担心科学家们会被鼓动只图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去利用他们的发现。他一直对专利授予惯例持批评态度,坚持“对待人类基因序列的唯一合理途径是,它属于我们大家——它是人类的共同遗产”。
萨尔斯顿断言,如果是商业需要规定了我们所涉及的研究项目,那科学本身将是可怜可鄙的。但是在这本书中,萨尔斯顿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即科学家,特别是他在书中所叙述的主要角色,都是具有选择权利并有可能做出决定的人,而他们的选择和决定,从根本上说,并非是先前就确定好了的。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同的生命线》具有自传的特点,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它有一个误区,因为这不仅仅是作者自己的故事,也是关于一项重大科学事业的故事,而这项科学事业已经(或许永远)改变了我们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考虑方式。
本文作者多萝西 • 纳尔金(Dorothy Nelkin)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共同的生命线(The Common Thread)》:一个关于科学、政治、伦理和人类基因组的故事。约翰 • 萨尔斯顿(John Sulston)和乔治娜 • 菲莉(Georgina Ferry)合著,约瑟夫 • 亨利出版社2002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