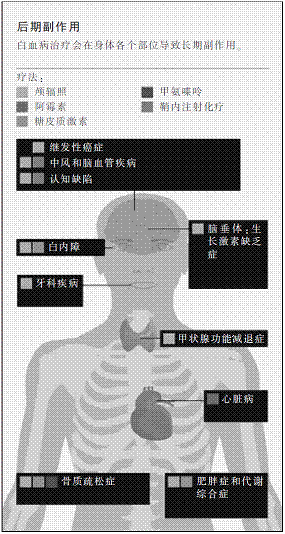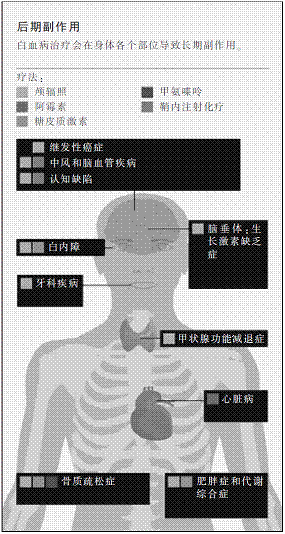小儿白血病可医治程度很高,但是许多幸存者遭受了严重的、甚至有生命威胁的长期的药物副作用。科学家正在寻找一种更安全的治疗途径。

乔伦娜·汉森(右)在童年时期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治疗
乔伦娜·汉森(Jolene Hanson)的最早记忆之一,是在明尼苏达大学医学中心,坐在轮椅上吃生日蛋糕,那是在1976年3月13日,她4岁生日那天。仅仅16天后,她被诊断患上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那个年代,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夺走了2/3患病儿童的生命。
关于白血病治疗,汉森记忆甚少,除了记得她妈妈碾碎了一颗药丸放到冰淇淋里给她吃。但是她的医疗记录显示,她服用了长春新碱、氨甲喋呤、阿霉素、门冬酰胺酶、泼尼松、环磷酰胺和阿糖胞苷等药物,并且她尚在发育的大脑接受了12轮的放射治疗。
这样高强度的治疗治愈了她的白血病,但是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诅咒:长期的副作用纠缠了她37年之久。她只有4英尺8英寸高――放射治疗导致了她生长激素缺乏并且永远秃头。她的医学日记记录了长达9页的劫难:1987年10月15日,“英格沃德斯塔特医生(Dr Ingvaldstat)排干了我的右侧卵巢囊肿,有橘子那么大”;1999年7月20日,“我有一个基底细胞癌从第3、第4腰椎区当场切除了”;2004年8月,“几个月服用导致不孕不育的药物、看高风险的医生之后,诊断结果是我不能怀孕了。”
尽管遇到这么多医疗问题,她竭力保持坚强,不被打倒。“有时我只能付之一笑,”她说,“不然我还能怎么样呢?”
“我还能怎么样?”这个问题也是那些寻找能治好白血病而不给患者留下持续几十年的心脏损伤、认知缺陷、继发性癌症和中风等后遗症的治疗方法的医生们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长期危害
如今,许多白血病的病例都是可治愈的:超过85%的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患者都幸存下来了,ALL是最常见的小儿白血病。但是超过1/4的小儿癌症幸存者在接受治疗之后的起初25年里,报告了至少是严重的、威胁到生命的或是致残的健康状况。
研究者面临的挑战是寻找到在不降低治疗的有效性的同时,能降低这些治疗带来的副作用风险的疗法。为了让副作用风险最小化,他们介绍了能保护患者免受一些危害的药物,替换有害的疗法,并寻找能指示出哪些病人最脆弱的生物标记物。
“过去的哲学是你能活下来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治疗带来的问题你就全盘接受吧,”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的弗雷德哈钦森癌症研究中心的儿科肿瘤医生K.斯科特·贝克(K.Scott Baker)说,“但是过去患者的那种心态现在已经改变了。”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对小儿白血病进行大脑放射治疗的医生们对复发可能性的关心更甚于对继发效应的关心。许多化疗药物使大脑容易受到白血病细胞的入侵,因为这些药物一般不穿越血脑屏障。
“那时候的医生们没有真的思考过他们的病人20或30年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治愈病人,”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达纳法勃癌症研究所领导一个幸存者研究项目的儿科肿瘤医生丽莎·迪勒(Lisa Diller)说。只有当儿童幸存者达到一定数量时,放射治疗对发育中的大脑的风险才变得清晰:它造成了脑肿瘤、生长激素缺乏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及学习和记忆障碍问题。
降低风险
现在,很多医院只有当大脑有很高的旧病复发风险时――例如,白血病细胞已经扩散到脑部,或者该疾病通常是一种影响T淋巴细胞的来势凶猛的类型,才对儿童实施放射治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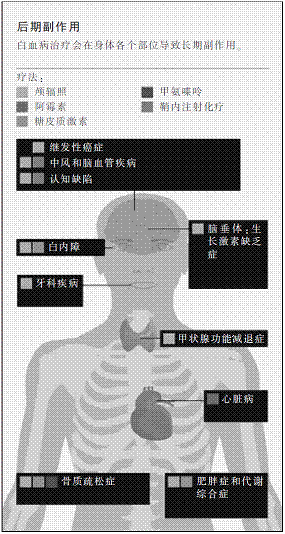
如今,医院也通过管制减少了放射治疗――放射量鲜有超过1 200厘戈瑞的,是汉森所接受的累积剂量的一半。大多数儿童不接受放射治疗:医生们宁愿选择在儿童患者的脊髓液中注射甲氨喋呤和阿糖胞苷之类的药物,来保护他们的年轻病人的大脑免受白血病细胞的入侵。
但是这些药物可能导致长期认知缺陷,并有它们自己的其他后期副作用。例如,甲氨喋呤可能损害平衡和正常行走的能力。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圣犹大儿童研究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癌症研究员莱斯·罗比森(Les Robison)说,甲氨喋呤这种药物与如此多的问题有关,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像现在看待大脑放射治疗一样看待它,把它视为一种有如此多长期副作用的疗法,所以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该避免使用。
另一类药物――包括广泛使用的阿霉素在内的蒽环类抗生素,则与另一种威胁到生命的后期副作用有关。几十年前,医生们就已经知道阿霉素和另一个类似药物――柔红霉素,会使左心室壁薄弱,从而导致一些患者充血性心脏衰竭。
医生们只需减少用药剂量,就能避免一些这样的后期副作用。例如,大剂量的阿霉素会使30%的成年人罹患充血性心脏衰竭,但是剂量减半,就会使致病比例大幅缩减。但是,儿童就没有如此幸运了,因为即使是低剂量的用药也会增加心脏病的风险,而减少剂量又可能降低药物的有效性。
“如果你去掉一些治疗,以避免毒性,与此同时,你也在冒降低疗效的风险,”达纳法勃癌症研究所的儿科肿瘤医生斯蒂芬·萨兰(Stephen Sallan)说。更好的策略也许是增加一种能克制阿霉素伤害、保护健康细胞的药物。但是过去三年的研究渐渐表明,这是一件棘手的事情。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阿霉素对心肌有害,一个可能性是因为阿霉素抑制了拓扑异构酶II,这是一种有助于放松DNA螺旋的酶。研究发现,心脏细胞中缺少这种酶的老鼠在接受阿霉素治疗后不会有心肌损伤。但是许多研究者,包括萨兰,都说阿霉素的毒性可能来自它产生的自由基――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给患者施加抗氧化剂就会有帮助。
一种具有抗氧化剂特性的药物――血管紧张素转化酶(ACE)抑制剂――在老鼠实验上已经取得了诱人的结果,包括发现两个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可能“几乎完全阻止”几种类型的心肌损伤。在成年患者的临床试验中,也有一些有希望的结果,但是这些药物貌似对儿童就没有这么有效了。萨兰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在接受蒽环类药物治疗之后,服用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的儿童,一开始能看到他们的左心室壁有所加强,但是疗效不能持久。
萨兰更喜欢使用另一种不同的保护心脏的药物――右丙亚胺,这是一种用于正在接受乳腺癌治疗的妇女的自由基清除剂。这种药物好像有帮助,但是对其使用却有争议。欧洲药品管理局在临床试验表明一些儿童相继产生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和影响骨髓干细胞的障碍之后,于2011年禁止医生给儿童开此药处方。
萨兰驳斥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是扯淡,指出那些孩子同样也服用了另一种与这种并发症有关的药物。但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却对欧洲药品管理局的决定足够认真对待以致向医生建议,还加一句说禁止将右丙亚胺用于儿童。
限制阿霉素的伤害的另一个策略是,只对具有正确基因、能安全地控制此药的患者使用。对于具有一个特定的调节阿霉素代谢的CBR3基因变量的儿童来说,阿霉素治疗可能比白血病本身更可怕。对于这些儿童,“似乎根本不存在阿霉素的安全剂量。”研究者说。
后来的生活
躲过放射治疗和化疗的后期副作用的患者未必就脱离了生命危险。如果他们的治疗包括骨髓移植,他们仍然可能面临其他风险。“有一整套很独特的问题,其中有一些还相当长期。”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的血液学家和肿瘤医生大卫·艾维冈(David Avigan)说。
就像所有的移植一样,骨髓移植的风险是供体组织的免疫细胞会把接受骨髓移植者识别成是“外来的”,从而攻击人体,出现免疫排斥反应。这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包括对肝脏、肺、皮肤和消化道的长期损害。一个更惊人的后期副作用是接受骨髓移植的白血病幸存者,其瘦肌肉质量会被脂肪代替。这个过程本来是自然衰老的一部分,但是在骨髓移植之后,这个过程似乎被加速了,贝克说。他的研究团队表明,进行骨髓移植的患者还产生了胰岛素抗性,这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以及其他属于“代谢综合症”的广泛类别里的疾病有关,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幸存者罹患这些疾病的风险本来就已经增加了。
尽管后期副作用如此广泛,但是令人吃惊的是这个问题却很少被研究,尤其是对除了小儿白血病之外的白血病幸存者的研究。罗比森领导的小儿癌症幸存者研究项目,跟踪研究了两万多名儿童患者,提供了丰富的数据。但是这样的研究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而对小儿急性髓细胞白血病的幸存者的首个长期研究直到2008年才发表。
同样地,对成年白血病幸存者的后期副作用的研究数据也很少。“儿科医生们已经领先于我们了,”达纳法勃癌症研究所的研究成年幸存者的肿瘤内科医生安·帕特里奇(Ann Partridge)说,“显而易见,既然我们有成年的幸存者,我们就应该为成年幸存者做得更好。”
那些受到历史上最恶劣治疗的乔伦娜·汉森那一代的患者,如今已经40或50岁了,可能产生了一拨如同过早衰老的后期副作用。例如,迪勒提醒说,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幸存者的骨头密度损失,会导致他们在中年时骨折的风险增加。
美国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儿童医院的儿科血液病学家和肿瘤医生罗伯特·林(Robert Hayashi)担心,高强度的类固醇化疗(例如汉森受到的泼尼松化疗),会使儿童过早得关节炎。罗比斯发现一群三四十岁的幸存者,有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惊人的肺部高血压,导致了呼吸困难。
萨兰说,一些心脏受到蒽环类药物损伤的儿童,也许最初几十年可能避免充血性心脏衰竭,只不过是晚些年再发病。“有后期副作用,”他说,“有很晚才出现的后期副作用。”
汉森的病例,当然是如此。几年前,她说,她的身体还算健康,但在2012年年底,她的右眼后面出现了一个脑瘤,需要动手术。她可能宁愿用放射治疗切除肿瘤,但是放射首先就可能致癌,她已经接受过太多的放射治疗了。汉森说,她已经准备好了新一轮的后期副作用,“但是,我真的希望我的身体能让我清净一会儿。”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