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剧照
大卫·利恩(David Lean)执导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开头,有个关键性的场景,T.E.劳伦斯与他的上司布赖顿上校拜访了阿拉伯起义领导人费萨尔王子的沙漠营地。费萨尔王子的帐篷既简单又奢华,编织了花纹的织物从低矮的帐篷顶上垂挂下来,硕大的黄铜水壶在烛光下闪耀光泽,地上铺着华丽的地毯。帐篷内没有家具;男人们直接坐在地毯上。布赖顿上校穿着贴身的军服,佩戴着锃亮的斜挎式武装带,脚上穿着皮靴,看上去坐得格外不自在,双腿笨拙地伸出,放在身前。劳伦斯是名中尉,穿着没那么正式,显然坐得更加舒服,双腿叠向一侧。费萨尔王子穿着黑色袍子,头上戴着白色的阿拉伯头巾,倚靠在一堆绵羊毛皮上,而他的同僚谢里夫?阿里随意地靠在帐篷的一根柱子上。五花八门的坐姿以电影的方式强调了一个重点:放松的贝都因人在沙漠这个地方很自在,而身体僵硬的英国上校是个外来的干涉者。劳伦斯介于两者之间。
世界分成席地而坐的人和坐在椅子上的人。在一项对全球人类姿势的经典研究中,人类学家戈登·休斯(Gordon W.Hewes)确定了不少于一百种的常见坐姿。“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人类会习惯性地深蹲下来,好让双脚减轻负荷,他们在休息和工作时都会这么做。”休斯评述道。深蹲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都受到人们的喜爱,但盘腿坐在地上几乎一样常见。许多南亚人烹饪、用餐、工作和休闲时都会采用这种坐姿。美国西南部的某些美洲原住民部落以及美拉尼西亚人习惯坐在地上,双腿笔直前伸,或者在脚踝处交叉。双腿叠在一起倾向一侧的坐姿――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劳伦斯的坐姿――被休斯描述为许多部落社会里女性的主要坐姿。
导致世界各地不同坐姿千变万化的原因,可能是气候、穿着或生活方式的不同。寒冷或潮湿的地面使人们不会跪在或蹲在地上,可能促使人们寻求坐在较高的地方;紧身的衣服会倾向于阻碍深蹲和盘腿坐姿;游牧民族和城市社会相比起来,就不太会使用家具;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然而,因果关系解释不了为什么折叠凳起源于古埃及这一有着暖和、干燥气候的地区。或者,为何日本人和韩国人传统上都会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着寒冷的冬天。又或者,为什么游牧的蒙古人出行时会带着可折叠的家具?同样属于游牧民族的贝都因人则不会那么做。
休斯解释说,他没有将倚靠坐姿包含进他的研究,因为他没有找到充足的图片证据。这很遗憾,因为对于休息时的身躯而言,倚靠坐姿一直是种舒服的坐姿。古埃及人使用床铺,可能会倚靠在长榻上,尽管这些并没有出现在壁画中――壁画的宴会场景显示,埃及人坐在椅子上或地上。至于在倚靠坐姿下用餐的画面,最早的证据是一幅存放于大英博物馆的公元前七世纪的浅浮雕作品。这幅雕刻在条纹大理石上的作品有时被称作《花园宴会》,展现了亚述人国王和王后在室外享用食物与饮品――他们在庆祝一场战斗的胜利。国王倚靠在类似于贵妃椅的长榻上,而王后坐在近旁的一张扶手椅上;两人共用一张摆满了食物的桌子。家具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其非常之高:长榻离地大约有五英尺,而王后坐的扶手椅让我联想起救生员坐的高椅,有齐腰高,需要配上脚凳。设置成这种高度的原因是让国王和王后高高在上,高于那些挥动拂尘(柄长得像扫帚柄一样)为君主夫妇扇风的仆人。还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被国王打败的敌人的首级就挂在附近的一棵树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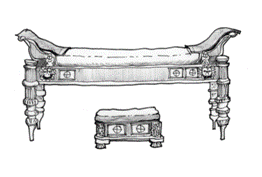
罗马人的长榻
奥地利建筑师伯纳德·鲁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最被人铭记的,便是一系列引起诸多争论的著作,其中包括了《没有建筑师的建筑》(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这本书是基于1964年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内举办的一次展览,伯纳德当时是该馆馆长。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设计界的牛虻,赞赏了俯卧用餐的习俗。他观察到,古罗马时代的用餐者只有一只手空着,无需用到刀叉,因此摆脱了他称之为的“凌乱餐桌”。鲁道夫斯基是个离经叛道者,厌恶实用的当代卫生间,也不喜欢大多数能节省劳力的家用设备。他尤其看不起椅子。“我们之中更敏感的人清楚地觉察到坐在椅子上的荒谬一面――好比是被刺穿在四根牙签上,或者像牡蛎一样柔软地垂下来,而椅子就像一片超大号的贝壳。”对于那些认为从文化上来讲,坐在椅子上优于坐在地板上的人,鲁道夫斯基的这句相当过分的描述是种故意的挑战。椅子的缺位并不代表原始或愚昧,他在这一点上当然是对的。文雅的日本人和韩国人很久以前就知道那些供人坐的家具,但他们选择坐在地板的垫子上。在印度,两个多世纪以前,英国人引进了“正襟危坐”的坐姿,然而大多数印度人仍然在做许多种活计――烹饪、用餐、工作时――会盘腿坐在地板上。
选择哪一种坐姿,而不是另一种坐姿,这有着深远的后果。如果你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垫子上,你就很可能会制定出一条礼节,要求进屋之前脱去鞋子。你也更可能会穿拖鞋或凉鞋,而不是要系带的鞋子;还会穿上宽松的衣服,使得你能够蹲下来或盘腿坐。习惯坐在地上的人不太会使用高大的衣柜――更方便的做法是把物品存放在距离地面更近的箱子和低矮的橱柜里。坐在垫子上的人更可能会睡在垫子上,正如坐在椅子上的人更可能会睡在床上。(在印度,许多人坐在地上,却会使用床铺,这是个例外。)习惯坐在椅子上的社会发展出五花八门的家具,譬如餐桌、梳妆台、咖啡桌、写字台和餐具柜。坐在地板上的习惯也会影响建筑:光着脚或者穿着袜子在房子里走来走去的话,需要地板很光滑――不能有碎片――因此保温的木材比石材更合适;坐的地方很可能会覆盖着柔软的垫子或编织出来的毯子;高窗台和高房顶的吸引力也会大减。
任何一个决定坐在椅子上的文明必须解决一项现实中的挑战:人类的姿势。第一个认识到坐和姿势之间关联的人,是18世纪的法国医生尼古拉·安德里·德布瓦勒加尔(Nicolas Andry de Boisregard)。安德里是整形外科领域的先驱,就连“整形外科”这个词也是他创造的。在发表于1741年的论文中,他描述了健康坐姿与椅子之间的关系。“当一个人坐的时候身体会向后弯的话,后背一定向内侧弯曲,”他写道,“当一个人坐在一张凹陷的座椅上时,无需任何特意的设计,人自然而然会让身体保持平衡,而这必然让后背更加弯曲。”凹陷的座椅是指普通椅子用灯芯草编织出来的内凹底座,随着时间流逝容易下陷。为了改善坐姿,安德里建议增加一个可调节的螺杆,能从底下把座椅底座往上推,保持椅面始终平整。
两百年后,俄克拉何马州大学的一位体育学教授埃伦·戴维斯·凯利(Ellen Davis Kelly)在一本教学手册中简洁地归纳了人类姿势面对的生理学挑战:

拥有腰部支撑的椅子
“姿势对于人类来说,显然是个难题,因为人体骨骼在直立状态下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四条腿或者甚至是三条腿的椅凳可以是相当稳定,但谁听说过两条腿的家具?两条腿的人类身体在维持平衡时带来持续不断的问题,这个问题又因为一件事而变得严重:人类的双脚对于人类躯干这个高耸的上部结构来说,是非常小的支撑基底。仿佛这还不算是难题似的,人体的上身、脑袋和手臂从臀部往上,只由一根脊椎来支撑。”
椅子的意图是向人类提供暂时的歇息,可以避开这类不稳当的艰难时刻。但凯利描述的这种不稳定性假如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当人坐下来时,影响会加重。身体的重量集中施压于骨盆底部的坐骨结节上,或者宽泛地称之为坐骨。这些骨骼酷似摇椅的弧形弯脚,只提供侧面支撑,允许身体在其他方向前后摇动。椅背提供的支撑允许肌肉松弛下来,但是太过垂直的靠背导致坐下的人低头垂肩,而简单地让椅背呈现弧角,会催生出不自然的向后倚靠的坐姿。假如椅子太过坚硬,会导致坐骨很不舒服,假如椅子太过柔软,就会让臀部的肌肉扭曲变形,会施压于坐骨,这样同样会引起不适。假如椅子过低,身体的重量会全部集中在坐骨上,而不会被大腿分担一部分;假如椅子过高,坐在上面的人往往会倾身向前,把双脚放在更稳定的位置上(即地面),但这样会压迫呼吸,引起脖颈肌肉紧张。
1884年,一位德国整形外科手术医生弗朗茨·施塔费尔(Franz Staffel)判断,大多数座椅“是为眼睛而建造的,而不是为了背脊”,他提出低靠背能支撑人体的腰部区域。施塔费尔被称为“现代课椅之父”,他建议大家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后背应该尽可能地贴近直立时脊椎的双S曲线。在19世纪期间,初等教育变成强制性,儿童们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坐在教室里,研究者提议了好多种桌椅组合方案,打算以此来改善坐姿。有些设计方案中包括了座椅安全带、额头束缚带和脸庞托架,尽管很难想象这样严苛的装置真的被人使用过。
1913年,一位瑞士解剖学家汉斯·施特拉塞尔(Hans Strasser)发表了一份座椅设计方案,靠背上部微微弯曲,椅面倾斜,以便更好地支撑大腿下侧。施特拉塞尔的发现被一位瑞典研究者本特·阿克布卢姆(Bengt Akerblom)予以确认,本特使用X射线和肌电图研究人坐着时的身体力学。阿克布卢姆设计了好几种椅子,它们的弯曲靠背后来被冠以“阿克布卢姆曲线”之名。
站起和坐下的动作也是种挑战。我们都体验过错误估算椅子的高度时突然的震动,因为跌坐进一张椅子等于在短暂的瞬间对脊椎施加两倍于体重的压力。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给椅子装上扶手,这样当我们坐进椅子里的时候,扶手能提供一些支撑,而当我们起身时,扶手也是个方便的借力处。假如椅子过低的话(譬如休闲椅),这点尤为重要。从没有扶手的低矮椅子里起身是很困难的,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而言。扶手提供了另一项用途:当我们坐在椅上的时候,通过一些倚靠的地方,从而减轻肩膀位置的压力。
英国心理学家保罗·布兰顿(Paul Branton)形容坐在椅中的身体“不仅仅是个了无生气、装着骨骼的臭皮囊,被丢在椅子里待上一段时间,而是个活生生的有机体,处在活动连续不断的动态状态”。我们不会纹丝不动地坐着,我们会坐立不安,会变换重心,还会交叉双腿和双臂,动弹下挤在一起的肌肉,尽管幅度会十分微小。我们和椅子发生互动:我们坐在椅子上面,向后靠,向前靠,经常会倚靠在座椅边沿。我们用腿盘住一条椅子腿;将一条胳膊悬在椅背上,或者把一条腿架在扶手上。
我们人类擅长步行和奔跑,我们因为睡觉时能躺倒而快乐。引发问题的,是介于二者间的姿势。就算我们坐在地上,这句论述仍然是真实的――有着坐于地上习惯的文明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垫子、垫枕、扶手和坐垫可供证明。当我们选择坐在椅子上时,这句论述甚至变得更加正确。每一把椅子都代表了一次努力,一次试图解决地心引力和人类解剖学特征之间冲突的努力。坐起身总是个挑战。
资料来源 The Paris Review
责任编辑 彦 隐
――――――――
本文作者维托尔德·雷布琴斯基(Witold Rybczynski),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