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对《生命是什么?》这本提出了当代分子生物学中许多重要概念的著作进行了重温和述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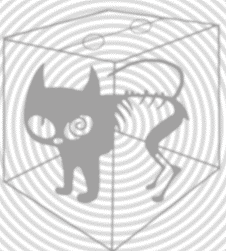

物理学家埃尔温·薛定谔对于分子生物学提出了许多自己的创见
《生命是什么?》(1944),奥地利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埃尔温·薛定谔(ErwinSchrodinger)利用这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提出了一个更具体但同样具有挑衅性的问题。他问道,是什么让生命系统与已知的物理定律相悖?他给出的答案现在看来是有先见之明的:生命以指导细胞组织和遗传的“代码脚本”而著称,同时明显地使生物体能够暂停热力学第二定律。
这些想法鼓舞了公众和一些科学界名人,但也激怒了其他人。尽管它们的成分并非原创,但这一构想出色地预见了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1953年的发现,他们发现了DNA的双螺旋结构是如何编码基因的。正如克里克当年写给薛定谔的信中所说,他和沃森“都受到了这本小书的影响”。
《生命是什么?》这本书优雅而平易近人,是由薛定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于1943年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发表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公开演讲讲稿组成的。当奥地利被纳粹德国吞并时,薛定谔被流放,他被邀请到爱尔兰帮助建立都柏林高级研究所。2018年9月份,圣三一学院以“生物学的未来”为题盛大庆祝薛定谔发表《生命是什么?》75周年。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生物学已经从一个很大程度上描述性的科学转变为一个关注机制的科学。由于遗传学家托马斯·摩尔根对果蝇进行的研究,研究人员开始从基因传递的角度来理解遗传,即设想成染色体上排列的大分子。许多人认为基因是蛋白质。然而,就在薛定谔准备演讲的时候,微生物学家奥斯瓦尔德·埃弗里却在发现证据,证明它们是核酸。因此,《生命是什么?》在科学意义上和社会政治意义上都陷带来了一个混乱的时期。
薛定谔小心翼翼地踏入这些跨学科领域。他宣称自己是一个“天真的物理学家”,思考着生命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命并在不同的世代之间稳定地传递基因突变的。他在量子力学方面的研究为他赢得了1933年的诺贝尔奖,但这并不是他评论生物学的资格。在生物学领域,薛定谔此前除了对视觉生理学的探索之外,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可以说,这种天真是这本书的优点和缺点的来源。
书名中的谜题源自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当时是如何认为分子世界完全由统计行为控制的。在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和路德维希·玻尔兹曼的经典分子物理学中,原子运动是随机的。从数不清的原子的平均行为中可以发现精确而有力的物理定律,例如那些将温度、压强和气体体积联系起来的定律。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特定的宏观结果――一种表型,一个生物体可观察到的遗传特征――是如何从分子水平上的单个基因突变中产生的?这里,也许是薛定谔猫的精灵,形成于1935年,它的宏观生死取决于一个量子事件。数学家罗杰·彭罗斯在谈到这个思想实验时说,“如果薛定谔在写作《生命是什么?》一书时一定程度上想到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感到惊讶。”看着遗传特征(比如欧洲哈布斯堡王朝成员常见的突出的下颌),薛定谔问道,该等位基因是如何“几个世纪以来不受热量运动无序倾向的干扰”的?
在这里,他引用了另一位前量子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的实验,德尔布吕克利用高能辐射诱发基因突变,使他能够估算出约1000个原子的基因大小。薛定谔声称,对于“合法的活性”――持久的遗传性――来说,这似乎太小了,无法在统计波动面前持续存在。但他断言量子力学可以解释这个问题。分子中的原子通常可以以许多种稳定的方式排列,每种构型都有相应的能量,这就是薛定谔对不同基因等位基因的设想。但它们之间的“量子跃迁”通常会受到高能屏障的抑制。
他接着提出,这种基因编码分子(他是那些怀疑它们是大型蛋白质的人之一)在其构型中有足够的潜在多样性,可以编码大量信息,而且这种多样性可以提供细胞的“代码脚本”。每个原子的位置很重要,但模式不会重复――因此他将分子描述为非周期(不规则)固体。这不是一个全新的想法;1935年,德尔布吕克提出了类似的建议。生物学家赫尔曼?穆勒和霍尔丹独立地提出,染色体可能作为它们自身复制的模板,就像新的晶体层在已有的晶体层上形成一样。
薛定谔承认,所有这些都没有回答“遗传物质是如何工作的”这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如何在发育和新陈代谢中被使用的,使一个有机体能够每时每刻建立和维持自己,就像薛定谔所说的“四维空间时间模式”,但是他从热力学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不是能量的问题(生物体的能量摄入和产出必须平衡,否则它们就会燃烧),而是熵的问题,这是衡量原子无序程度的指标。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在所有的变化过程中熵都必须增加。但是生物以某种方式延缓了熵增现象。正如薛定谔所说,它们以“负熵”为食,利用“负熵”维持细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同时通过加热环境来支付它们的热力学费用。
他无法指出的是,它们是如何开采负熵的。他被迫提出,在生命系统中,“我们必须准备好找到一种新的物理定律。”如今,似乎不需要如此极端的解决方案。
他的分析缺少的概念是信息。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克劳德?香农的信息论和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开始填补这一空白,尽管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开始了解信息在生物学中的真实特性。正如薛定谔关于负熵的谈话所暗示的,生命是开放系统中一个不平衡秩序的口袋,而DNA密码只是维持它的一部分。很遗憾薛定谔没有接触到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关于麦克斯韦之妖的研究。麦克斯韦之妖是一个思想实验,揭示了如何利用分子水平的信息来消除熵失调,而分子水平的信息在宏观上看起来只是统计学噪声。
更重要的是,薛定谔通过想象它的读数直接映射到表型上,给了他的代码太多的代理。这不是它的工作原理:你不能读懂人体器官在基因组中的排列。信息的作用是作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步一步的指南。要获得意义,它必须有背景:细胞的历史和环境。追踪表型是如何在基因相互作用和环境中产生的,这是现代基因组学的关键难题。
在《生命是什么?》的影响下,克里克、西摩·本泽和莫里斯·威尔金斯等几位物理学家成为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但是,从当代的评论来看,并没有迹象表明许多生物学家理解薛定谔的代码脚本作为一种活跃的有机体程序的真正意义。在新兴的分子生物学科学中,有些人持批评态度。莱纳斯·鲍林和马克斯·佩鲁茨都曾在1987年薛定谔出生100周年之际谴责过这本书。鲍林认为负熵是对生物学的“负面贡献”,并指责薛定谔对生命热力学的“模糊和肤浅”的处理。佩鲁茨抱怨说,“他书中真实的东西并不是原创的,即使是写书的时候,大多数原创的东西也不是真的。”
虽然这些判决是无情的,但也并非没有实质内容。那么,为什么这本书如此有影响力呢?修辞理论家利亚·切卡雷利(LeahCeccarelli)认为,这要归功于薛定谔的写作风格:他成功地架起了物理学和生物学之间的桥梁,而没有给予任何特权。薛定谔关于生命熵平衡的思想可以被看作是研究生物特权,如复制、记忆、衰老、表观遗传修饰和自我调节,如何被理解为不可忽视环境的非平衡复杂性过程的先驱。令人感兴趣的是,环境和偶然性的类似考虑现在被认为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其思想是纠缠、退相干和语境。这是否不仅仅是巧合,我们还言之过早。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