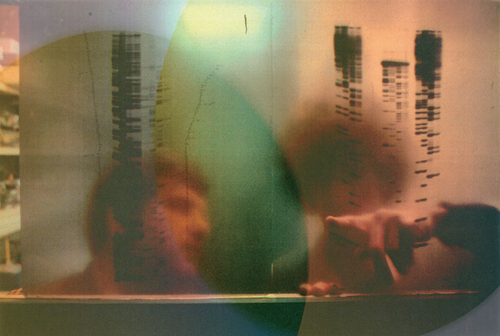1995年,《连线》杂志的一位联合创始人向一位笃信卢德派思想的灾难预言者发起挑战。就科技与文明的命运立下赌约。今天,他们的裁判要做出裁决了。
左上方为凯利,右下方为塞尔,中间为两人打赌的支票
1995年3月6日,美国《连线》杂志执行主编、技术乐观主义者凯文 · 凯利(Kevin Kelly)走进了作家柯克帕特里克 · 塞尔(Kirkpatrick Sale)的公寓。凯利曾请求过采访塞尔,但他计划来一个突然袭击。
此前,凯利刚刚读过塞尔即将出版的新书《反未来者》的早期版本。该书讲述了19世纪卢德分子的故事,那是一场工人反对工业革命使用机器的运动。在工人们的叛乱被镇压,他们的首领被绞死之前,他们确实捣毁了部分机械化织布机。这些人认为,机器会将他们变成用于大规模生产的非人性化机械中的一个齿轮。
塞尔崇尚卢德派思想。1995年初,亚马逊成立还不到一年,苹果的业绩依然停滞不前,微软尚未推出Windows95,用手机的人还寥寥无几。多年来,塞尔一直坚持著书抱怨现代化,主张回归能维持生存的经济。他认为,计算机技术将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糟。
凯利对塞尔的书深恶痛绝。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技术持有不同意见,更觉得塞尔的观点侮辱了自己的世界观。因此,他去塞尔的家里不只是想吵一架,还打算揭露塞尔的错误观念。
据塞尔回忆,那次采访完全是公事公办。在凯利联系他之前,塞尔从未听说过《连线》杂志,因此预计这次采访会很艰难。他们争论的焦点包括阿米什人是否应该过深居简出的生活,印刷机是否使森林退化,以及技术对工作的影响。在塞尔看来,技术窃取了人们的体面工作。而凯利则认为,技术帮助我们制造出了用其他方式无法制造的新产品。塞尔表示:“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微不足道。”塞尔认为社会正处于崩溃边缘,但同时又觉得这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他说:“历史上,诸多文明都走向了崩溃。我之所以保持乐观,是因为我认为文明肯定终将崩溃。”
塞尔在其有关卢德运动一书的最后,预言社会将在几十年内崩溃。凯利的观点则恰恰相反,他认为技术具有强大的力量,社会将因此而蓬勃发展。为了设下圈套,凯利问塞尔社会将何时崩溃。塞尔对此有些猝不及防——他从未为此设定期限。最后,他脱口而出:2020年。
凯利接着问道,在未来25年,人们如何才能确定塞尔所言是否正确。塞尔临时列举了三个因素:一场使美元一文不值的经济灾难造成比1930年更严重的大萧条;穷人奋起反抗富人;层出不穷的环境灾难。
“我们就此打个赌吧。”凯利提议道。“没问题。”塞尔答应了。
之后,凯利布下了他的圈套。他此次来塞尔的公寓,带来了一张从他与妻子的联名账户上开立的1 000美元支票。当他把支票递给塞尔时,塞尔着实吃了一惊。“我跟你赌1000美元,到2020年,我们连边都沾不上你所说的那些灾难。”
当时,塞尔的银行账户里连1000美元都没有。但他认为,即便输了,这笔钱届时也会大大缩水,于是就同意了。凯利建议将支票寄给威廉 · 帕特里克(William Patrick)保管——帕特里克是一位编辑,既编辑过塞尔有关卢德运动的书,也编辑过凯利最近撰写的关于机器人和人造生命的大著作。塞尔对此没有异议。
25年过去了,曾经看似遥远的最后期限终于到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那笔钱花落谁家。随着赌约期限的临近,凯利和塞尔都同意由支票持有人帕特里克在2020年12月31日决定获胜者。赌注可远不只是1000美元,它还关系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有关人类进步本质的观点谁占上风。在一个充斥着诸如气候危机、疫情横行和资本主义掠夺成性等问题的时代,我们还有理由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吗?凯利和塞尔各自代表了这一分歧的两个极端。对于他们来说,这场赌约的结果将是对他们毕生所求的认同或否定。
塞尔的《反未来者》具有煽动性,但也只是众多主张人们回归前工业时代生活的著作之一。他成长于纽约伊萨卡一个邻里关系密切的郊区,早年就对简朴生活充满向往。他的父亲小威廉 · 塞尔(William M. Sale Jr.)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文学,是该领域的传奇人物,美国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 · 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和文学理论家哈罗德 · 布鲁姆(Harold Bloom)都是他的学生。塞尔认为,他所在的小型社区就如同世外桃源。当有人提议将他就读的学校并入伊萨卡区时,年轻的塞尔公然表示反对。
塞尔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他学习历史,但却有意进军新闻界。在那时,他就已经是个反叛者。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出台了一项名为“代替父母”的政策,授权学校管理者负责培养孩子的道德操守。曾担任学生报编辑的塞尔对禁止无人监护的女学生参加校外聚会的提议感到愤慨,并带头煽动近1500人举行示威。最终,塞尔与其室友、未来小说家理查德 · 法里纳(Richard Fari?a)一起被停学。
即使在那时,塞尔对电脑也持怀疑态度。他和另一位同学合写了一部科幻音乐剧,讲述如何逃离IBM统治下的反乌托邦美国,剧中的主角就是一台邪恶的电脑。剧中的一句台词预示着塞尔后来的作品。“我们要的是在我们每次转弯的地方,不会看到那个白痴一样的机器在盯着我们看。”一个角色这样抱怨道。这是在1958年。
大学毕业后,塞尔为一家左派刊物工作,并在非洲待了一段时间。他回到美国时,反主流文化方兴未艾。他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反战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撰写了一本关于该组织的权威著作。他后来承认,“这种沉迷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激进”。
20世纪70年代,他开始从刚刚萌芽的环境运动中汲取灵感,形成自己的哲学。“一天早晨,我坐在餐桌旁,思考着建筑中的人类尺度,以及现代建筑如何完全失去了这个尺度。”他说。这让他想到城市规划的不足以及国家组织形式的弊病。塞尔一直怀念自己童年时代生活的宛如世外桃源的乡村,于是开始倡导建立自给自足的去中心化系统,以“人类尺度”构建生活。
塞尔的作品交织着两条主线:一是强烈谴责所谓的进步文明,二是构建简约生活的田园式蓝图。为了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他写了《天堂沦陷》这本书,悲叹北美的毁灭。在另一本书《伊甸园之后》中,他提出了一种假设:当人类开始猎杀大型动物,进而引发毁灭自然世界的无情趋势时,一切都会开始走下坡路。
再后来,《反未来者》问世。塞尔对于卢德运动的理解与媒体对新兴互联网的狂热形成鲜明对比。在该书中,塞尔提出了他研究多年的“文明崩溃论”。他在书中写道:“如果工业文明的大厦最终没有因为其内部的坚决抵抗而崩塌,那么它似乎肯定也会因为自身日积月累的超负荷和不稳定而在几十年内(甚至可能更早)倒塌。”
据帕特里克说,有关卢德运动的书并不怎么畅销。有一本书曾在出版前被四处传阅,但最终被《连线》的执行主编凯利搁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当时,《连线》刚刚创刊两年。在杂志创办之初,凯利是一个关键人物。在他的领导下,《连线》不仅成为见证新一波科技和互联网浪潮的旗舰刊物,也是技术乐观主义思维方式的前沿阵地。
凯利成长于新泽西的一个郊区,鲜有机会走出家门。但在罗得岛大学的第一年(也是唯一一年),他读了很多书。这些书让他确信,在旅行中自己可以受教更多。他决定去亚洲旅行,拍摄他能找到的最偏远地区的照片,磨炼自己对摄影的热情。
这段旅程持续了近十年,并彻底改变了他。他说:“我到过亚洲非常偏远的地方,其中一些在服饰、建筑、信仰、行为等各个方面都还停留在中世纪。我见过完全没有车辆的城市,人们在街上乱扔垃圾,而且还没有厕所。还有一些村庄,连金属都找不到。”当他在1979年回到美国时,他对让生活变得更便利的技术深为感激。
凯利在佐治亚大学的生物实验室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开始写书,介绍自己的旅行见闻和思想观点。在发现可以用自己的Apple IIe电脑与精彩的社区联系起来后,他成了一名电脑迷。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早期的在线会议系统——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并通过该系统结识了《全球概览》创始人斯图尔特 · 布兰德(Stewart Brand)。布兰德对凯利的文章印象深刻,于是为他提供了一份公司内部杂志《共同进化季刊》的编辑工作。该杂志仍然秉承《全球概览》创刊时“以工具为生”的理念。后来,凯利将这份环保杂志与另一份介绍软件的品牌刊物合并,并将其命名为《全球评论》。他说:“我体验过没有科技的世界。因此,当人们说要摒弃科技时,我会明确表示反对,因为他们不知道没有科技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正因如此,凯利觉得《反未来者》的结尾章节非常令人不快。凯利并不介意对技术进行批评。他曾编辑过一期主题为“电脑即毒药”的《全球评论》,即便是《连线》杂志也会不时偏离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指出科技世界的缺陷和弱点。但是,塞尔对他所谓的“人类尺度”太过狂热,甚至于对“进步”进行攻击。在他的旅行中,凯利看到了现代工业和技术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他喜欢回到年轻时访问过的偏远村庄,他发现,原本是稻田的地方突然冒出了一家工厂,而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还光着脚丫的村民现在都穿上了凉鞋。随着工业在城市的发展,人们会去追求一些不同的东西。
当他为塞尔宣扬的观点烦恼时,一个想法涌上心头。他曾读过有关科学界赌约的历史,其中最特别的要数朱利安 · 西蒙(Julian Simon)在1980年挑战生物学家保罗 · 埃利希(Paul Erlich)提出的关于资源短缺迫在眉睫的说法。他也喜欢意见相左的知识分子公开表达立场的做法。“我不知道我们要赌什么,但我想让他为自己连篇累牍的无稽之谈付出代价。”凯利说。
塞尔可不这么看。他说:“我知道整件事都是一个圈套。”尽管觉得自己被骗了,塞尔也从未想过把凯利扔出去。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两位“赌徒”都没有找对方交谈。但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凯利开始与塞尔联系。凯利说:“他好像从世界上消失了。”当凯利最终通过电子邮件联系上塞尔时,塞尔对收到老对手的来信惊讶不已。
塞尔并没有忘记这次赌约。他在各种采访中都提及此事,每次都仿佛是在讲述一件趣事。但在赌约期限来临之际,他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入思考。
塞尔仍然坚信,人类文明注定要消亡。几年前,他曾建议自己的两个女儿不要生孩子,但她们对此置若罔闻。如今,他有一个外孙女已经成年,将来他可能会对她提出同样的建议。他曾对一位采访者说:“她可能也不会听取我的建议。”
因此,凯利不应该对塞尔在2019年3月说的话感到惊讶,那是他们数十年来第一次接触。塞尔当时声称,“崩溃即将来临”。然后,塞尔告诉凯利,他正在写一本关于此次赌约的书。
这本书叫《2020年的崩溃》。事实上,塞尔已经对技术做出了妥协。最近,他和妻子搬回了伊萨卡,以便离家人近一点。他有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部固定电话、一个炉子、两台电视和四台收音机,但拒绝使用微波炉和智能手机。尽管他认为社交媒体会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但他在Facebook上注册了个人主页。
2020年5月,塞尔和凯利就赌约输赢的具体条款达成一致。他们的编辑帕特里克将宣布获胜者。凯利建议帕特里克等到2020年的最后一天再公布最终结果,以便让文明社会有机会自我毁灭,他写了一篇长达四页的文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塞尔则建议帕特里克读读他的书。不过,帕特里克可以自由地做出决定。
塞尔和凯利打赌时,他们都认为,到2020年,很容易确定谁输谁赢。也许只需要环顾四周,看一看文明是否仍然存在就够了。很明显,文明依然存在。但是,新冠疫情及其经济后果和不断恶化的气候危机,让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帕特里克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帕特里克居住于波士顿郊外,是一名自由职业者,从事编辑、自由撰稿工作。很久以前,他曾任职于一家教科书出版商,并在那里他认识了凯利和塞尔。当凯利问他是否还保留着25年前的赌约支票时,他立刻想起来要去哪儿找。他打开居家办公室的文件柜,翻开一个文件夹,看到了装在自封袋里的两张支票。
对于技术,帕特里克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曾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当计算机问世时,我并不认为它们是下一波解放浪潮。”他欣赏工程之美,但看不惯技术人员的傲慢。他没有Facebook账户,不使用智能手机,而只使用简单的手机。
他站在司法的角度裁决这场赌约,认为自己的角色更多的是两个人观点的批判性读者,而非世界的评估者。他说:“我只是一个普通人,不是传达神谕的祭司。”他决定依照塞尔在1995年3月6日仓促提出的条款进行裁决,即使这样做对塞尔不太公平。帕特里克很同情塞尔,但又觉得塞尔的极端主义伤害了他的事业。帕特里克说:“我希望塞尔能花更多时间成为一个更有见地的评论家,塞尔对技术的强烈排斥让他脱离了现实。塞尔太天真了,竟然当场接受了赌约。”
塞尔说:“即使现在回想起来,我也想不出一个更好的答案。”此外,在《2020年的崩溃》一书中,塞尔过早地做出了退让。他在书中写道,如果社会真的已经崩溃了,他的书——无论出版与否——都不会存在。“因此,让我承认我错了吧,”他写道,“但错的不是太离谱,更不是满盘皆输。”然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全球性大事件似乎在向塞尔倾斜。新冠疫情对健康和经济的影响,特朗普对西方民主的践踏,以及更极端的气候状况,都将人类文明推向了悬崖边缘。难道我们还没有退回到洞穴和茅屋时代,塞尔的预测就已经成真?
帕特里克必须对此做出决定。12月初,他开始撰写自己的裁决书。尽管他对科技持谨慎态度,但并不打算追随目前的科技抵制潮。该赌约建立在三个明确的条件之上,帕特里克会分别考量每一个条件,就像逐轮评判一场拳击比赛一样。
经济崩溃。塞尔曾断言,到2020年,美元和其他通用货币将一文不值。帕特里克指出,道琼斯指数达到3万点,比特币等新货币取得了成功,这里没有太多争议。凯利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
全球环境灾难。凯利在他长达4页的论述中争辩道:“尽管气候变化加剧,但人们仍然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如果这是一场灾难,那么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70亿居民来说,这一点并不明显。”但帕特里克对此不以为然。他在裁决书中写道:“火灾、洪灾和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使人们流离失所;疫病向北半球传播;冰盖消融,北极熊无处可去;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飓风季节和最温暖的年份。毋庸置疑,我们至少已经‘接近’全球环境灾难。”因此,这一回合塞尔胜出。
贫富战争。塞尔在书中援引了关于收入不平等和社会结构遭受破坏的毁灭性统计数据。如果他是在新冠疫情结束后写这本书,情况将会更糟。但是,这是贫富阶层之间的战争吗?帕特里克指出,在凯利和塞尔立下赌约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以惊人的经济发展速度改变了原有面貌;另一方面,即使在美国,也不可否认地出现了社会动荡。所以,他觉得这一轮难分胜负,但胜负的天平在向塞尔倾斜。
经过三轮角逐,两人似乎打成了平手。但在做最后决定时,帕特里克还是坚持采用赌约最初的评判标准。在那次决定性的会面中,塞尔提出了三种灾难纷至沓来的主张。“塞尔必须连胜三轮才能获胜。他的三个预言中,只有一个如其所愿,一个伯仲难分,还有一个并没有实现。”帕特里克写道。
因此,在2020年12月31日,帕特里克在给两个下注者的电子邮件中宣布凯利获胜。他总结道:“凯利只是侥幸胜出,没有什么值得庆祝。”
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对于人类文明的命运以及未来25年的走向,2020年并未告诉我们明确的答案。
这既是由于2020年的非比寻常,也是由于赌约双方自身的局限性。他们在一个总是可能回归均值的世界中表达的立场都很极端。塞尔未能解释人类智慧如何使我们免于被扔进森林和洞穴,而凯利没有考虑到科技公司会不计后果地滥用权力,或是在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方面存在不足(有时甚至是火上浇油)。
对于自己的主张,凯利和塞尔仍然像以往一样深信不疑。尽管2020年堪称悲惨的一年,但凯利的乐观情绪却更为高涨。他相信,在技术的帮助下,世界性灾难将得到化解。他在给帕特里克的信中写道:“25年后,贫困将会消失殆尽,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将成为常态;国家之间的战争也将销声匿迹;我们使用的大部分能源将是可再生能源,由此减缓气候变暖的步伐;人的寿命会继续延长。”他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就叫《进托邦》。
塞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信,社会大体上正在走向崩溃。不过,崩溃的进程还不够深远,不足以将我们从公寓大楼赶进乡村小屋。他说:“社会的坍塌并不像一座建筑内爆的倒塌,而是像一场缓慢的雪崩,能够摧毁沿途的一切,直到最后永远将整个村庄掩埋。”
在2021年元旦那天,凯利给塞尔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将1000美元捐给国际小母牛组织(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旨在向贫困家庭捐赠繁殖用家禽和家畜)。塞尔回复道:“我并没有输。”凯利以为他没有看到帕特里克的裁决书,于是让帕特里克给他重发邮件。但实际上塞尔已经看过邮件,但拒绝承认失败。
就像白宫中盛气凌人的否认论者一样,这个坏脾气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最后得分稍逊一筹的情况下退出了比赛。塞尔说,他正在寻求某种形式的上诉,并寄希望于公众舆论,而事实上,当初订立的规则并不包括这种“复议”。凯利对此怒不可遏。他说:“这是绅士的赌约,他就是个无赖。”凯利警告塞尔:历史会让人们记住他是一个不信守诺言的人。但塞尔不相信会有这样的历史。对他而言,社会正在崩塌,所有的赌注都一并作废。
资料来源W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