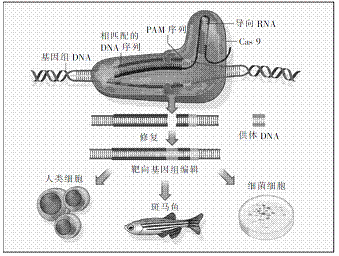2012年,伊曼纽尔·查朋特(Emmanuelle Charpentier)在研究中与他人共同发现了CRISPR-Cas9系统:一个正在改变着基因组学、遗传学和基因工程领域的工具。CRISPR-Cas系统是由RNA和蛋白质构成,可以识别入侵病毒DNA并可将其分解(CRISPR表示成簇规则性排列的短回文间隔重复序列,用于描述基因的排列方式)。对于许多细菌和古细菌而言,该系统就相当于一个有效的免疫系统,可以广泛运用于医学、农业和工业领域中。在一次与《美国科学家》杂志副主编凯蒂·伯克(Katie L. Burke)的访谈中,查朋特谈及了她目前的研究方向以及CRISPR-Cas9系统未来的应用前景。

伊曼纽尔·查朋特
CRISPR:一种多用途工具
问:当开始研究CRISPR时,它还属于一个鲜为人知的领域。是什么吸引你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什么时候意识到它的重要性的?
答:当我在实验室开始研究CRISPR时,其实我们的兴趣在酿脓链球菌是如何引发疾病的。我们试图破译细菌是如何致命的,以及如何在人体内存活下来的调节机制。我们观察了酿脓链球菌的基因组序列中是否有产生调节性核糖核酸(RNA)的片段。众所周知,RNA能把基因转换成蛋白分子,但也能调节基因的表达。我们发现了大量的RNA,包括CRISPR系统中的RNA,以及一个位于CRISPR位点旁的示踪RNA。
在2006至2007年间,我们发现CRISPR是由DNA构成的一种保护细菌不受病毒侵害的防御系统。由于细菌的进化和发展,可以入侵基因组的不同防御系统。CRISPR就是这样的一个系统,有点类似人类的获得性免疫系统。其过程是:先识别入侵的基因组,当发生第二次感染时,就摧毁这个外源DNA。
当入侵的基因组进入到细菌过程中,含有噬菌体签名的RNA分子能识别出。其中一个与CRISPR相关的蛋白,即Cas蛋白会对噬菌体基因组进行切割,而这是噬菌体基因组表达和繁殖的死穴。
CRISPR系统有不同的类型,其中CRISPR-Cas9是最简单的一种。它是由两个RNAs[CRISPR]和一个蛋白[Cas9]构成,共同裂解入侵的DNA,其过程我们分别在2011、2012年的《自然》和《科学》杂志上阐述过。
问:CRISPR-Cas9系统为什么对基因组工程和基因组编辑如此重要?
答:理论上,科学家可以对任何有机体的遗传密码进行测序或破译,但在寻找准确的操作基因组工具的能力仍非常有限。虽然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研究出一些重组方法,但这些方法不是很精确。所谓的基因组工程,特别是基因组编辑,只是在十多年前才出现的,当时发现了一些meganucleases类型的核酸酶。
这些核酸酶对于科学家很有吸引力,它们可以精确地诱导和修饰真核细胞基因组的突变,或改变和交换基因乃至敲除序列。然而,每次操作一个特定的序列时必须设计一个新的蛋白。这一过程成本高,需要时间,也并不总是奏效,效率低。
而CRISPR-Cas9就不一样了。它能识别包裹在DNA中的微小RNA分子,科学家只需根据靶DNA序列来操作RNA。这一特点使得CRISPR既廉价,又高效,已被证明可以在任何细胞和有机体中发挥作用。相比于只能导入突变或互换基因的meganucleases,CRISPR-Cas9更像是一种多用途工具,不仅能修饰DNA,也可以用作改变DNA表达的工具。
对生殖细胞编辑应有国际禁令
问:目前你具体在做什么?
答:我有三个与CRISPR有关的研究方向。除了继续探索CRISPR-Cas9的生物化学特性外,我们也在研究酿脓链球菌以外的其他细菌的CRISPR-Cas9系统,包括CRISPR-Cas与DNA靶向机制无关的方面。另外,在一些合作研究中,我们正在研发把CRISPR-Cas9导入到人体某些特定细胞中的技术,希望能治疗人类的遗传病。我已经创办了一个“CRISPR Therapeutics”的生物技术公司。
问:除了CRISPR,你是否在研究其他的系统?
答:是的。我们正在研究RNA介导的调节机制,例如蛋白质降解过程中的调节机制,包括细胞之间是如何通信的,以及人类宿主是如何自行防御细菌的。尽管我对研究CRISPR-Cas很感兴趣,但并不仅限于此。我想把部分时间花在基础研究上,去破解那些对医学有潜在作用的新机制。
问:你认为CRISPR最令人期待的前景是什么?
答:CRISPR对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意义重大。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它来构建受损人类细胞(基因缺失细胞)文库,试图筛选出新的靶点用于新的疗法,包括构建动物模型对新疗法进行检验。因为模型可以更准确地模拟人体内发生的一切。
有了CRISPR-Cas9,我认为人类遗传病有可能会得到治愈。但在此之前,需要研制出能把这个系统传送到细胞中的工具。对于只能利用细胞替换才能治愈的一些遗传病来说,这一技术有可能会奏效。
问:对于CRISPR如何使用,你最大的担心是什么?
答:我最担心的是对这个工具的误用。举例来说,对人体生殖细胞系的操作,或者那些非环境友好型的操作。我并不是反对针对植物的操作,但这要取决于改变的是什么。这项技术真正用于人类还需要多年时间,欧洲的一些伦理委员会在禁止对人类生殖细胞系基因操作的宣传已经奋战了十多年。尽管在美国可能还不是那么严格,但肯定会引发一些争论。
问:中国研究人员最近发表了一篇论文,显示CRISPR-Cas9可用来编辑人类的生殖细胞系。这项工作吸引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被一些人看成是医学史上的里程碑。对此你有何看法?
答:这篇特殊的文章投给杂志社后,一天之内就被接受了,这意味着文章没有经过严格评审。我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
这篇文章发出了一个信号。现在有些人试图编辑人类胚胎,这或许是讨论它的意义的最佳时期。因为政策的制定总是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科学家与研发者、制药业、临床医生、伦理学家以及公众一道,需要就这个工具如何运用达成一种共识。公众不应该害怕,因为这个工具也有好的方面,重要的是让每个人明白它是什么,它能做什么以及它的工作原理。我们需要在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国际范围内,针对某些应用的禁止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问:基因组工程研究进展迅速,公众从中需要了解些是什么?
答:我认为人们首先需要了解的是,这项技术是源于科学家正在进行的纯粹的基础科学研究。政治家和基金部门需要支持基础科学,因为所有的发现,不管它是关乎生物、化学、物理还是其他领域,都源于这类基础性的研究。
第二,虽然这个工具有可能被误用,但它会在不同层面上对生物学家们提供帮助。目前,仍然有大量的基因其功能尚不明了,我们甚至还不完全了解分子之间是以怎样一种协同方式工作的。第三,这个工具将给遗传学研究带来便利,因为公众真正害怕的是转基因这个词。包括在诊疗中,CRISPR-Cas9有可能比现行许多的药物疗效更好,副作用更少。
问:您认为对生殖细胞编辑国际上应该有一个禁令,就像詹尼弗·杜德纳在《科学》上呼吁的那样?
答:是的,肯定要禁止。特别是避免最近我们在相关报刊上看到的那些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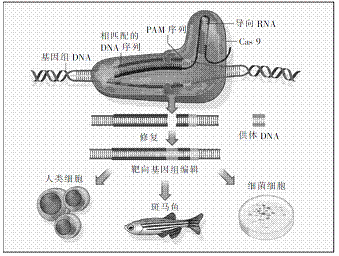
在细菌中发现的CRISPR-Cas9,是RNA和蛋白的复合体,它能准确识别并删除DNA序列。由于其在各种有机体中的有效性、靶向性和多用途,正在推进基因组工程和相关领域测序方法的革命
给予科学家充分的自由和时间
问:你的CRISPR-Cas9专利引发了争议。有没有更好的解决途径?
答:是的。这一技术可以广泛运用于包括人体在内的许多不同领域。因此,为保护这一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知识产权,我认为解决这些争端需要花点时间。
对于目前出现的这种情况,我认为这并非是件坏事。因为它原本可能对这一技术的研发产生不利影响。但情况却并非如此,关键是大家都在用它,人人都想开发它,事实上人们在研发的过程中,没有受到过阻止。
问:创建CRISPR Therapeutics公司后,是否意味着你的这一成果可以商业化了?
答:在CRISPR-Cas9之前,我已经在研究细菌引发疾病的若干分子机制。我与几家生物技术公司都有联系,同时也在关注着这些公司的整个研发过程,它们当时都在研发抗菌和抗感染药物。但有一点我很明白:那就是假如我创办一家公司,我需要有一个可以被转化的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很快,有了CRISPR-Cas9后,我就意识到这个系统确实有多重用途――可用于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领域。甚至在证明这个系统是如何裂解DNA之前,我就有这个想法了。
我跟我的合作者詹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共同申请了专利,我当时在瑞典――瑞典或许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集发明与知识产权拥有者于一身的国家――认识了一些有兴趣跟我合作的人,很快吸引了一些投资者。
相比一些科学创始人,我很幸运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为这个项目投入了很多精力,也想自己亲历这个项目的整个过程。就像自己的婴儿,你想看到它迈出的最初几步,以及它能走多远。
问:CRISPR给你带来了声誉和丰厚的奖金。你从中体验到了什么?
答:我的研究方法总会受到一些批评,因为我与常人的行事方法不同。对CRISPR-Cas9而言,最终证明是成功的。在研究过程中,利用自己过去获得的不同专业知识和思维方式,包括多学科的经历,尤其是接触到生物学的方方面面,现在看来还是件蛮不错的事。
有时我还在怀疑,对我想做的研究,即我提出的研究方案(破解CRISPR-Cas9系统)是否会有人资助。然而,我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给科学家提供资金支持,让他们做一些重要的甚至是异想天开的研究。无疑,一个人需要有自己的兴趣、方向或某种大胆假设。如果你想把一些东西组合在一起进行实验,甚至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疯狂的实验,但你就想这样做,看看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我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因此,给予科学家充分的自由和时间进行类似的研究非常重要。科学家们需要支持和理解。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