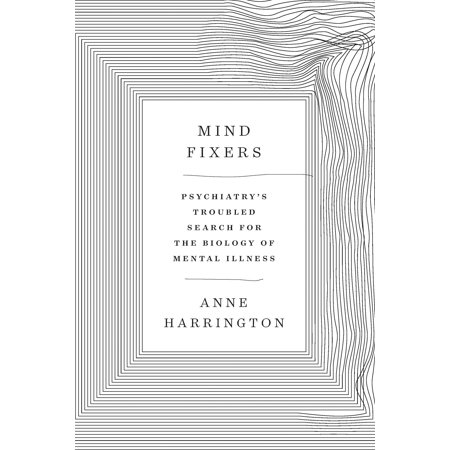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仍迷雾重重,而精神病医师们对此矢口否认。
心灵维修工:精神病学无法找出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
1886年,纽约法医协会期刊编辑克拉克•贝尔(Clark Bell)向普林尼•厄尔(Pliny Earle)医师提出了一个读者们都相当感兴趣的问题:究竟哪一种精神疾病能称得上真实存在?厄尔作为精神病医师已经执业了50年,期间给医学生开设了有关精神疾病的课程,参与建立了第一个精神病医师的专业组织,也是美国首批私人开业的精神医生。他也运营着几家精神病院,并在其中尝试了一些新疗法,譬如对精神疾病患者进行教育。显而易见,如果要回答贝尔的问题,普林尼•厄尔会是不二之选。
然而厄尔的回信并没有令贝尔满意。“现阶段就我们所知,”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不能根据病理基础对任何精神疾病进行分类,原因很简单,我们对这些疾病的病理基础几乎一无所知。”厄尔想必对此也相当悲观,在他的职业生涯中,看到医学从依赖传统和经验的学科,演变成一门基于科学的学科。医生们过去曾通过放血疗法和芥末膏药来治疗疟疾和水肿,甚至对这些疾病本身的定义都相当模糊。厄尔所在的时代,医生们已经鉴定出了这些疾病的生物学病因,并据此发明了疫苗。而对于精神疾患,精神病医师们只猜测其起源于脑,厄尔也深知不能通过显微镜看到病患们痛苦的原因。精神病医师们仿佛停留在了过去,只能通过厄尔强调的所谓“从外在症状进行判断的、显然的精神状况”来进行诊断和治疗。
安妮•哈林顿(Anne Harrington)在她的著作《心灵维修工:探究精神疾病生物学的困顿之路》(Mind Fixers:Psychiatry’s Troubled Search for the Biology of Mental Illness)中,描述了将精神病学现代化的种种尝试。正如书的副标题所言,这一过程绝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可以说,这是个从期许坠入绝望的故事:曾经看似奇迹般有效的疗法,如今看来是如此野蛮;而令人踌躇满志的公共健康政策,最终却成为一场灾难。
哈林顿书中的一些故事我们耳熟能详,譬如伊格斯•莫尼兹(Egas Moniz)发明了脑叶切除术,并在1949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同一时期,沃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周游美国,用以冰锥为原型的手术器械对精神病院中悲惨的精神病人进行手术。哈林顿还发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像在19世纪30年代,胰岛素曾被用于治疗精神病,医生们希望精神病人从胰岛素昏迷中醒来后,疾患会被治愈。她也给了我们看待历史的一些新角度,像对于19世纪60和70年代的精神病人去机构化运动,她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法:这次运动并非由那些确信一些氯丙嗪就能治愈患者的精神病医师(他们乐于开些药就解决问题)带头的,而是由弗洛伊德学派挑起大梁的:19世纪50年代,许多抗精神病药物问世,而精神分析学家察觉到他们的技术结合药物,能更好地在门诊治疗患者。
在哈林顿的描述中,从冰浴到百忧解,技术的发明者与追随者无一例外地吹嘘其伟大。这不无道理,有些人确实在从胰岛素昏迷中醒来后不再有幻觉;也有些人在一轮电休克疗法或抗抑郁药物治疗后,不再受严重抑郁症的困扰。但几乎每次在一种新疗法出现后,就会出现事故,也没有人出面解释。现如今,我们对几乎所有精神疾病的病理学基础仍然与1886年一样一无所知——不过无可厚非,脑是宇宙中最为复杂的物体之一。即使精神病医师使用着形形色色的疗法,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阐明其疗法的生物学基础。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精神病医师们也不能明确哪种患者和什么情况下这些疗法有效。因此,精神病医师有时会给抑郁症患者开安定类药物,而有时给焦虑症患者开抗抑郁药物。精神病学是经验主义的,从业医师们依据自己或同事们的经验进行治疗,这似乎与普林尼•厄尔时代如出一辙。然而,却少有人指出:精神病学这门学科过于依靠医学科学权威,有时甚至缺乏足够的科学证据,而其历史关键词不仅仅有希望和失望,也有无法治愈的傲慢。
这一关键词没有出现在哈林顿的书中,历史上却是一目了然:一个个狂热的医生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理论的错误。哈林顿最初就亮出了自己的观点:要保持克制力。“英雄般的一家独大和不接受任何质疑的权威虽然让我们感到暂时的满足,”她在书中写道,“但其结果却是——目光狭隘、互相揭丑、陷入僵局。”哈林顿实事求是地描述了探明精神疾病生物学基础,尤其有关大脑的种种尝试,她希望精神病学这一“令人担忧的”学科能够重回发展的正轨。
哈林顿无奈于长久以来两种势力之间的争论——胸怀大志的专家们相信精神病学正大刀阔斧地取得进步,不断理解精神疾病的发病原理;而反对的学者们认为这往好了说是在帮助患者的路上误入歧途,说难听些就是以人的尊严为代价,实行社会控制的伪科学——二者皆声嘶力竭却又对对方充耳不闻。事实上,这二者在半世纪前就磨刀霍霍,但至今也没有认真听取过对方的意见。
安妮·哈林顿所著《心灵维修工:探究精神疾病生物学的困顿之路》
哈林顿有关历史上一系列窘境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专家们依旧无法回答克拉克•贝尔的问题。其中就有197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在投票后宣布同性恋不再是精神疾病。问题所在很显然,批评家们也常常抓住这点不放——通过民主投票来决定这种重要问题能有多少科学性呢?同时,保险公司和政府官员们也掺和进来,大声质疑精神病学是否值得信赖,而他们提供的那些资金是否打了水漂。
学会的对策则是“清洗”了以弗洛伊德的学说为基础的《精神疾病的诊断与统计手册》(DSM),它最初就将同性恋包含在内。当第三版DSM于1980年出版后,作者们表示他们已经精确地列出了精神疾病:他们摆脱了曾经分类学上先入为主的观念,以非理论化的症状描述作为分类基础。但哈林顿指出,他们仍然保持着这样的观点——精神疾病不过是脑部病理变化的表现。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行为,哈林顿认为:“他们的做法很虚伪。他们相信所有真正的精神疾病都能找到生物学上的标记和解释。他们不过是将新的描述性分类视作发现这些的前哨。”
历史证明,DSM-3展现的科学姿态恢复了专家们的名誉,但并没有进一步的科学发现能够撑门拄户。事实上,DSM(现如今发展到第五版)依旧是临床精神病学的金科玉律,是精神疾病诊断的指南,而其中列出的精神疾病生物学基础又极其模糊不清,甚至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所(NIMH)在2013年表示将会“脱离DSM分类重新调整研究方向”。
哈林顿还在书中指出需要阐明的另一个对象,大众曾对此有广泛的疑问: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的“化学物质失衡”理论。其最初于20世纪50年代得到发展,得益于化学神经递质原理得到阐释;而改变意识状态的药物药理学上的新发现,如LSD能够靶向血清素和其他神经递质,又成为支持它的证据。这一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广泛进入公众的视线,那时出现了这类处方药——尤其是抗抑郁药物——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广告。哈林顿记录了百忧解和左洛复(Zoloft)的广告,他们言之凿凿地向机敏的消费者宣传道,这类药物并非简单地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缓解患者症状——这些消遣性毒品也能做到——它们能够真正修复症状背后的生物学问题。
这一精明的策略在市场中相当奏效,但却是个圈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公众们正逐渐接受‘血清素失衡’理论时,”哈林顿写道,“研究者们却达成了新的共识”,即这一理论“破绽百出,甚至可能完全错误”。而药物公司们却从中作梗,如今他们也不再寻找精神疾病的新疗法,而是用一成不变的广告词宣传以前的药物。于是至今,这一新共识没有广泛为人所知,也没有影响到消费者。最近一次统计显示,12岁及以上的美国人中,有多于12%的人在服用抗抑郁药物。化学物质失衡理论,正如同DSM的“翻新”,在科学上可能根本站不住脚,其花言巧语却有了极大的成功。
哈林顿用公正冷静的口吻描述了各种精神疾病生物学理论的大起大落,在医学史研究上有相当的价值。这本书甚至能让生物精神病学的批评家和支持者一同对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有更深的理解,不再试图消灭对方。但她表现出的克制力也可能导致她对重要问题的描述过于轻描淡写。
现代医学所持的观点是,将人类遭受的痛苦视作生物学上的疾病有助于他们洞察并治愈疾病。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具有社会政治的维度。如果我们的痛苦能够(也应该)属于医学的范畴,含蓄地说即是展现出了一种视角:有关人类施为、有关美好生活的本质、有关谁应该得到譬如金钱和同情等珍贵的社会资源。这类问题当然并非迫切需要回答,譬如认为摔断了腿只在需要流动的社会中是个问题并没有多大意义。
但精神病学关注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尤其是我们对世界和自身的客观经验,相对其他医学专业,涉及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活着的问题。简而言之,它提出了道德问题。如果你要说服他人人类的情感仅仅是电化学噪声,那同时你就是在说何为人类,即便你的目的是缓解他人的痛苦。
在这种意义上,尝试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物学基础,与研究癌症或心血管疾病是完全不同的。意识产生需要脑,再加上脑仅仅是一团浸泡在化学液体中的肉块的事实,并不能推断出意识上的痛苦就是纯粹生物性的,虽然这种看法被看作是处理精神疾病的好方法。这些仍未解决,或许可能无法回答的道德问题在哈林顿描述的历史中若隐若现。她选择的道路或许需要她回避一些棘手的问题,譬如意识和脑的关系,以及政治秩序和精神疾病的关系。但她并没有绕开她责难的那些争论,她更是指出了一些情况下精神病医师忽视了这些问题,或通过科学上的花言巧语隐瞒了这些问题。
虽然可能引起争议,但我认为哈林顿的“虚伪”一词还不足以描述DSM-3编者罗伯特•斯皮策(Robert Spitzer)所持的犬儒主义,他告诉我他会回应“精神病学被认为是虚假的”这一看法,也告诉我这本书很成功是因为它“看上去很科学。翻开它,看起来里面会有些东西。”而“讽刺意味”仍不足以准确描述一个企业兜售产品的方法是吹嘘他们自己都不再相信的、所谓治愈生物化学物质的失衡——这称得上是犯罪。很显然这就是恶意,它掺杂在希望救助病人的希望中,甚至到了令人咂舌的程度,赤裸裸地展现出人对权力和利益的追求。
哈林顿在书的最后也辩护道,如今的精神病学“在着眼处有所谦逊”,并将学科的注意力转移到严重的精神疾病上,譬如精神分裂症,如今在监狱和流浪汉收容中心进行了不少治疗,她认为这一领域需要“克服一贯还原主义的看法,并与社会科学和其他人文学科建立持续的交流。”这一提议相当合理,提示了除药物治疗外的其他道路,譬如重新尝试建立人道而有效的长期收容治疗。但无论哈林顿的设计如何公正而可赞,如果精神病学领域不愿对这一雄心壮志和它的不足之处进行充分考量,它终将落入被熟视无睹的境地。
资料来源 The Atlantic
____________________
本文作者加里·格林伯格(Gary Greenberg)是执业精神医师,著有《悲哀之书: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和精神病学的毁灭》(The Book of Woe: The DSM and the Unmaking of Psychia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