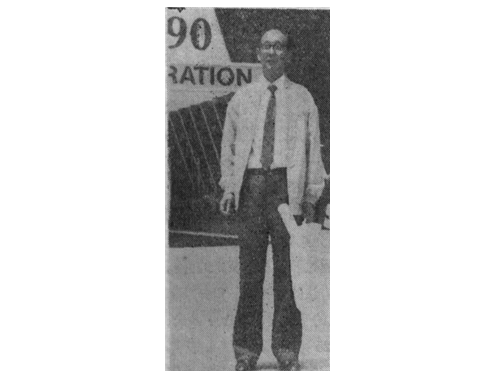说到我们上海的优势,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地理条件、巨大的生产能力,这些无疑是构成经济实力的支柱。但人们往往对科学家、科研机构的作用知之不多。而上海,乃至我们中国令世人瞩目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国拥有一批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科研机构。科学家的作用不仅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思想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动上,同时,科学家个人作为社会最优秀的成员,他们的人格、风范也不失为人们的楷模,是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工作关系,我有幸采访一些科学家,每一次采访归来常令我激动不已。因为这些采访不仅使我有机会了解了他们的工作,我更从中看到了凝结在这些成果之中的科学家本人的人格风采。我上周在采访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王育竹研究员时,再次体味到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击。
“王育竹50年代中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其后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学习量子电子学。60年代初回国后,先在中科院电子所,W64年起在中科院上海光机所从事研究工作。他是我国原子钟研制工作的开拓者之一。30年来,王育竹在量子电子学和量子光学领域做了系统的工作,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不少成果属首创。1988年,被诺贝尔奖获得者、第三世界科学院院长萨拉姆教授聘为国际理论物理中心成员(聘期6年),同年8月,由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聘为中国高等科技中心(世界实验室)特别成员。王育竹现为光机所量子光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以上这段文字概略表明了王先生的工作和学术地位。作为一名有很深造诣的光物理专家,王先生在国内外他所从事的学术领域有很高的知名度,但在科学圈外就鲜有人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
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4月12日我采访王先生的主旨就是请他向我们《世界科学》的广大读者比较通俗地介绍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工作。下面是根据王先生的讲话录音整理的采访内容,为了不打断读者阅读,采访人只是在文中的个别地方和文末掺入一点个人的体会。
原子钟是我搞的第一项科研工作,我个人在这方面有三项贡献,一是所谓的轴向通光微波谐振腔。微波谐振腔是指电磁波可以在里面存在的全封闭的一块空间。由于我们的原子钟是利用光抽运效应,即光和微波要同时和原子作用,这就要找到一种场合,使原子和光能同时存在。微波可以在谐振腔内存在,但谐振腔是封闭的,光不能通过,随便开孔会把沿壁传播的电流截断。但在膜的轴向部位可以开孔,里面的电流在壁上是圆环形的,而强度的分布在中心点最小,边上逐渐增大,这就满足了磁场分量均匀性的要求。开孔后,我在孔上装了一段截止波导(当电磁波的波长长到一定量时,波导不能再通过称为截止波导),光的波长非常短,在波导里是可以通过的。因此我们的工作意在创造一种条件让光通过截止波导打入谐振腔内,再从另一孔输出,这一孔同样装一截止波导。这样对微波来讲,这一孔就相当于是全封闭的,这就满足了原子钟(特别是原子)对原子进行光磁双共振的要求。这是我在较年轻时(1958年)在苏联做研究生时做的一项工作。回国后,我们就沿用这种谐振腔,一直到以后的铷原子钟都是用这一原理。后来国内一些单位搞原子钟也都利用这一谐振腔。从这点来讲,可能对国内原子钟的研制起了一点作用,我后来在1974年看到美国的一个阿波罗专利,它里面谐振腔的结构和计算方法都与我们做的完全相同。当时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发表文章(国内那时正在批名利思想),认为只要可以用就行了。这种微波谐振腔我们始终都在用。
我们的原子钟1976年交付给远洋测量船远望1号、2号使用,此外在卫星发射中心、上海天文台原子时系统、甚长波发射台等都用了我们的原子钟。特别是远望1号、远望2号,作为整个卫星测量船的指挥中心,时间就是由这一原子钟给定的,在离岸前和上海天文台的秒信号对准时刻。发射中心何时发射,何时发射到什么位置以及要测量和时间有关的数据,如速度等,都要求有很好的时间同步,如果原子钟出问题,那整个发射工作就难以进行了。开始发射的那几次,每次我都很紧张,以后慢慢习惯了,因为每次发射都很正常。我们的原子钟保证了历次重大发射的成功,从导弹发射到同步卫星发射等一系列活动。我们这项工作作为远洋测量船的一部分,获得了1986年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此外原子钟还获得多项其他奖。
王先生—口纯熟的普通话,他以极平缓的语气道出了他近三十年的部分工作。我想任何人只要有王先生工作中的一小部分成就就足以在光物理领域立足。
1976年后,我逐步转向辐射压力(即光压力)的研究,这也与原子钟有关。原子钟牵涉到能级间隔准确测量问题涉及众多基本物理过程,它们限制了原子钟的准确度,如一次多普勒效应、二次多普勒效应等都与原子运动速度有关。如能把原子速度减低到非常小的程度,以致最好不动,这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状态,因为这样能对原子做长时间的各种探测,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如能把原子速度减下来,那也可能对原子钟的准确度、精确度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样我就转向辐射压力研究,即利用光子的动量和原子交换试图将原子速度减下来。这好像一个小球飞过来时,朝它打过去很多子弹,碰撞的结果使小球减速。这当然是很简单的比喻,实际上这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光和原子咱互作用过程中涉及各种物理问题、各种条件。我个人在这方面有特色的工作是,我第一次把光频移的概念引入了激光冷却这一技术中。当原子上下两个能级在光强作用下移动到相近位置时,让原子吸收能量,从基态跃迁到激发态。在高激发态时,使能级移动的光束去掉了,原子能级恢复到原状,能级间隔又趋大,原子再自发辐射出一个光子。好像吸收的光子能量小,发射的光子能量大,这当中的差值是由于原子在能级移动时要爬坡,提高势能,这就要损耗动能,由此造成冷却。这一过程是我在1979年国内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即所谓的利用交流斯塔克效应激光冷却气体原子。这一设想1980年发表在国内的《科学通报》上,以后1982年又系统地发表于《中国激光》上,美国的Chinese Physies杂志也作了全文转载。1985年法国人Cohen-Tannoudji发表了“受激发射的光学‘粘胶’”—文,这一工作的思想与我们相同,但具体做法不一(他是二能级,我们是三能级),我们的工作早于他4~5年。
以后我做了激光偏转原子束。这一工作与美国贝尔实验室同时起步,他们发表文章比我们快,但我们的方法和他们有不同,我们采用多光束。我利用两面镜子中光的传播方向完全一致的特征做出多光束偏转原子束。这一做法的好处是,在单光束偏转原子束实验中,由于原子束的偏转量不够,这就要求扩大光束,而扩大光束又要求功率增大。国内的现实条件是激光功率都很弱,我就想到让它多次作用,所以想到了多光束。这一实验相当成功,无论在信号噪声比,还是在偏转量方面都比贝尔实验室高出1个数量级。我们与贝尔实验室的另一个很重要区别是,贝尔实验室是采用热丝测量原子束位置的传统方法(即原子束飞过来时打在热丝上,让原子离化,离化后再探测离子流,哪一个地方原子多,离子流也多,空间的位置是靠热丝探测的),我是用光学探测法,即用光束和原子束共振,由此原子要在空间发光,发光时通过照相机把荧光的强弱呈现在二极管阵列上。这一方法的信噪比、角分辨率都比贝尔的高得多,因为热丝的宽度最小要100微米,而我们的二极管阵列间只有25微米。这个结果表明我们的原子束系统是相当精密的,可以做一些更为深入的工作。
接下来的工作差不多是一个挑战,即是验证亚泊松光子统计。理论上讲,单位时间内发射的光子的统计分布满足于所谓的泊松分布,而共振荧光被认为是亚泊松分布,这是量子电动力学预言的结果,但是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一事件的存在。我就利用多光束方法来试图验证,美国的Mandel教授(正是他计算出亚泊松)也在做这一实验。他的方法是利用光子计数法。由于他是用单个原子的发光来计算,所以他的信号噪声比相当差,平均光子数只有3,只看到Q~-10-4非常微弱的亚泊松分布。我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即多光束偏转原子束。考虑到光子统计和原子动量的变化紧密相关,因此我就利用原子的动量变化来检测分布状态。我们得到了非常强烈的亚泊松分布,约为Q=-0.74+0.14,这非常接近于理论值,证实亚泊松光子统计的存在。国外科学家5年后又重复了我们的工作,国际上承认是我们首次作出以上结果。这一工作做好后,我们向1985年在夏威夷召开的国际第6届激光光谱会议投了稿,会议将我们的工作列为大会邀请报告,我去做了报告。报告后,很多科学家跑来向我祝贺,说你做了相当出色的工作。会后,美国著名科学家沈元穰先生(也是大会主席)说,你讲得太好了。我讲你好,不是我个人讲你好,是很多科学家讲你好。我接触到的许多科学家都讲你的工作好。他说,我的眼光没有看错。他会后来信说,你的报告为会议增色不少。你向大家表明,中国也有很好的科技工作。在此之前,在这一学术会议上,中国没有人应邀作邀请报告,我是第一个在这种会议上应邀作报告的中国科学家。从那以后,我们每次都参加(每两年一次)并每次都应邀作报告。我觉得从我们国家来讲,能有机会到国际上去讲一讲,这不是我个人的荣耀,而表明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出很好的工作,去参与国际竞争,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和为祖国争光。但由于我们实验条件等的限制,不少工作不能做完,否则一鼓作气,我们可以做更多工作,在国际上争得我们的地位。
王先生在以上的介绍中提到了与贝尔实验室某项工作的比较 · 结果,提到了国际激光光谱学术会议上外国同行的评价,尽管他说得很平淡,甚至在一开始采访时他对我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常的工作,但我想任何一个稍具科学常识的读者都会惊叹王先生这些年来工作的价值。
接下来的一件工作是驻波场中的激光冷却问题。这一工作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做,但由于我们的系统相当好,因而我们看到的一些结果是国际上未看到的。比如在正失谐条件下,过去认为不能实现深度冷却,但我们却得到了非常低的温度,约在60μK,突破了理论上的冷却极限。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理论结果与实验结果不―致?我们的看法是,理论假定原子是二能级原子(原子只有两个能级),而实际的原子是多能级的,所以原子在通过沟道时,原子的多能级参与了冷却过程,因此原子在驻波场内除作振荡运动外,仍能被进一步冷却。经过驻波场后,原子就形成了所谓的沟道化原子,即沿着驻波场的波谷进行运动的原子,这就改变了原子原有的速度分布。我和我的学生提出了一种“能级交叉”的冷却机制。这一工作的理论分析证明可能得到深度冷却。这项工作在美国召开的QELS(量子电子学与激光科学会议)上作了报告,其后部分内容发表在Physics Review A上。我们看到了一些较新的现象,如剩余Bragg衍射现象,看到了原子束在驻波场中分裂成两个峰。这些结果都是国际上未曾报道的。我们看到的沟道原子,其图像比国外的清晰得多。
更近一点的工作中有两项很鼓舞人心,一是腔内量子电动力学效应研究,这是当前量子光学领域中的前沿课题,很受国际上重视。它所研究的是光与物质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一些非常基本的现象。通俗地讲,如原子可以处于基态,也可以处于激发态,如处于激发态,那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从激发态上掉下来,这个问题就是量子电动力学要研究的问题。量子电动力学认为,原子在激发态上受到真空场的作用(所谓真空场指完全黑暗、不存在光能量时所存在的杂乱无章的电磁场,又称为零点起伏场,它具有半个光子能量的场,即使没有一个光子,这个场依然存在)。处在高激发态上的原子就是由于这个场的扰动而从上面掉下来,这是量子电动力学所解决的原子为什么发光的问题。而腔内量子电动力学则试图说明,如果原子处于一个谐振腔内,由于腔的存在,就改变了真空场的边界条件。如果原子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内(谐振腔内),由于真空场的变化,它就改变了原子的自发辐射几率,即爱因斯坦系数A可能改变,这是科学家非常想从实验室中看到的现象。这一现象首先在微波段看到了,因为此时自发辐射系数变化主要与Q值有关。为使能在光波段也看到这一现象,我们选用一种铷玻璃小球作为谐振腔。我们的设想是利用腔内电动力学效应来增大辐射跃迁几率,使原来不能发光的能级使它发光,这样就改变了铷玻璃的发光特性。我们大胆作了这样的设想并进行了实验,结果令人鼓舞。我们看到了自发辐射增强现象,而且由于原先不能发光或者说发光很弱的能级现在发出较强的荧光。当激发功率加大时,荧光就变成激光,使非常小的玻璃球变成了一具激光器。我们这一激光器可能是现在世界上最小的仅60微米大小。此外,我们从铷玻璃小球中看到了量子电动力学的空间效应,在以前只是理论上知道,实验上一直没有证实。这方面的工作将是今年5月在法国召开的国际会议的邀请报告的内容。这是我们首先做出来的,国外没有报道。
另外,我注意到激光二极管可能在激光光谱或激光物理研究中具有重要价值,我就和我的学生黎永青博士合作,开展了利用半导体二极管研究光场的量子性质。经过反复讨论,我们首先想重复日本人Yamamoto振幅压缩态的工作,这是量子光学中的一个前沿课题。压缩态光是指光的噪声比量子噪声更小的光场(量子噪声一直被认为是探索事物的极限)。Yamamoto的工作是利用电流反馈来做的,但由于在引出时会掺入了损耗的作用,从而破坏了压缩特性,因而不能应用。我们原以为我们做的工作只是重复了日本人的工作,后经分析,知道我们的工作和Yamamoto的工作不同,我们是把一个光束分成两个光束,然后相减,相减时,量子噪声是减不掉的。然后把剩余的量子噪声反馈到激光管上,并控制发光二极管中电流的发射,电子流的波动反过来又影响到光的波动。光的波动经两束又分开,如此使得两光束具有很强的非经典相关性,我们这里做的不是在一个回路里的反馈,而是两个光束减后的反馈,所以和Yamamoto的工作有本质区别。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孪生光束,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得到的噪声就比量子噪声低得多,可以压低到90%,国际上的工作为85%,我们这一结果可能是目前国际上最好的。这一方法的特征在于非常简单又可用。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一工作深入做好,如能证明这是可用的压缩量子噪声的方法,其意义就非常之大。目前在我们实验室召开的国内量子光学学术会议上,国内不少专家对这两项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们说,过去一直认为压缩态的工作是很难的,做实验也是非常复杂非常庞大,没想到你们用这么简单的方法就能做出来。专家们认为,这一研究提出了许多理论问题,有可能影响国内量子光学的研究方向。
虽然这次采访王先生是我首次有机会向他请教,但我曾在中国物理学会的《物理》杂志上经常读到王先生的工作,实际上国际上著名的物理杂志如Physics Review,Optics Letter等也时有刊载王先生的工作,因此光机所王育竹的名字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我们对体育、电影方面人士在国际上获奖很重视,但对自己的科学家在国际上的成就却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对科学家的宣传也不够。像王先生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在我们国家还是有相当一批的,他们的工作不但大大扩展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了解,同时他们也是激励国人奋力进取的楷模。
最后王先生应我之邀谈了他和他的开放实验室下一步的研究计划。“接下来的工作中有一个是激光冷却气体原子。我想着重做一下三能级系统(这很可能是获得更低温度的途径),这方面的理论工作正在深入做,实验上也在准备,我们想看到这种方式的冷却效果究竟如何,下一步还要开展超冷原子物理方面的工作。另外一项工作是QED小球效应扩展问题,如小球间的耦合、小球发光的其他特性等。估计这一小球是一个快速器件,如是这样就可能在光计算上起重要作用,如作为开关,与非门等。半导体非经典光场的噪声压缩也将更深入地做下去。现在这一现象已提出一系列理论、实验问题。要做以上这些工作,我们本身的力量不够,因此要吸收更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来做。”听王先生提到青年科学家问题,我又问王先生对青年科研人员出国热的看法。王先生说:“我们的开放实验室成立已经3年了,情况是可以的,特别是青年人发挥了很大作用,好多课题是由青年人唱主角的。我非常希望把青年同志送到国外去锻炼,增加见识,培养自己,但我又希望他们学成后再回来,建设自己的实验室,建树自己的科学事业。我这个实验室也有不少同志出去,有去也有回来的。总之,我希望青年同志不断出去,不断回来。我们这里的年轻人是相当优秀、出色的。”
坐落在上海嘉定清河路上的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大楼从外面看上去已经陈旧,那天我告辞了王先生,走在清河路上再次驻足回视光机所大楼时,我突然强烈感受到,这幢建筑物里的科学家——王育竹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正在做的工作为中国科学、为中国人增添了那么多光彩。我将长久地记忆起这次给了我那么多科学美感享受的采访,谢谢您,王老师。
(本刊记者江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