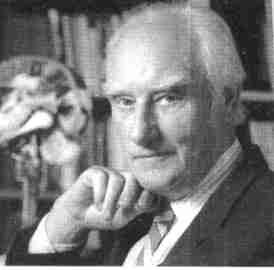2004年7月28日,弗朗西斯 · 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美国加州圣迭戈市一家医院去世,享年88岁。克里克是1962年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获得者、著名的DNA双螺旋结构揭示者之一。当这一不幸的消息传来,各国生命科学界人士反应强烈,一些著名科学家纷纷发表声明,追忆和悼念这位生物学巨擘,称他的去世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
好学而反叛的童年时代
弗朗西斯 · 克里克于1916年6月8日出生于英格兰北安普敦(Northampton),他的父亲与伯父共同经营一座祖传的制鞋工厂,中等的家庭环境并没有让克里克接受特别的所谓精英教育。不过,克里克幼年时就是个好奇心很强的孩子,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困惑和求知的渴望,这样的科学研究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克里克从小就像爱迪生一样,总是好问为什么。幸运的是,他的母亲也和爱迪生的母亲一样了解他的孩子,非但没有加以责难,而且为了满足他的求知欲特地给他买来一套《儿童百科全书》。书中内容五花八门,包括艺术、科学、历史、神话、文学等各方面领域,然而,最能够引起他兴趣的莫过于科学领域。当他了解到地球以外还有个浩瀚无际的宇宙;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还有原子这样的微小粒子存在;以及生命千变万化、生生不息的奥秘时,这套伴随着克里克度过童年的书就成了培养他探索自然界谜团的兴趣的启蒙老师。
虽然克里克也信仰宗教,但却不算是非常虔诚的教徒,他说,他对于科学渐增的兴趣,使得他在12岁左右就开始成为一个怀疑论者,一个有强烈无神倾向的不可知论者。宗教学家关于上帝创造万物的说法已经无法满足他强烈的好奇心,这对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生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说:“毫无疑问,对基督教失去信仰与对科学的逐渐执着是我科学生涯关键的一部分,这种影响倒不是在日常行事上而在于我认为什么是有趣又重要的事情。”
乏善可陈的青年时代
1933年,克里克进入伦敦大学学院深造,但他当时主修的是物理,那时的物理课程教的都还是古典物理学领域的范畴,很少有他真正想了解的如玻尔原子模型等量子力学领域。不过,他还是继续刻苦学习,在6年后如愿取得硕士学位,正打算攻读博士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被迫中断学业,转而进入海军部门研究制造鱼雷,在英国海军总部实验室参与磁性鱼雷与声控鱼雷的研发工作。
战争结束时,克里克已到了而立之年,此时才选择要投身基础科学研究工作,博士学位还未取得。因此,在天才如林的现代科学界,克里克是极为罕见的大器晚成者。此时的他面临了人生的抉择,到底要进行什么样的研究工作呢?他可以留在海军部队,但他不想一辈子都在设计武器。他在求学过程中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大学时主修物理,辅修数学,却没有具优势的成绩,仅仅了解一些他不甚感兴趣的物理学,如磁学和流体力学,却连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有。在思索人生方向的这段时间里,他对各学科的相关书籍进行大量阅读,他发现到他对“生物与非生物的区别”这类的课题特别感兴趣,于是开始自学生物领域的背景知识,然而,生物学领域博大精深,任何一个分支领域都可以消耗一个人短暂的一生,要选择什么领域进行深入研究呢?
自创“闲聊检验法”
克里克自创的“闲聊检验法”解决了他的问题,确定了他接下来的方向。他说,平常和朋友聊天时自己常提起的问题,就是内心深处最想解决的问题。通过这个方法,他找到了一生最想探讨的两个主题:生命的本质与大脑的奥秘。克里克反省了一下,发现到这两个领域都是许多人连碰都不会去碰的遥不可及的方向,但他却直觉性地朝这两个领域来发展,看来他天生对于宗教权威的挑战的性格已经在此时发挥了影响力。
克里克事后回想,他的一些与一般人不同的想法可能会使他在待人处事上不是那么讨人喜欢,但在科学研究上却有相当的助益。比如,他求学生涯中纪录的空白,对别人来说,实在是不学无术、一事无成,但对他来说,却反而代表了自己人生方向的无所牵挂,因为此时与他同龄的科学家,都已经在他们各自的领域小有成果,要他们在此时从自己已投资了将近十年的研究领域跳脱出来,重新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领域,试问又有多少人有这种勇气呢?他的空白纪录象征着人生的自由,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中,给了他重新起步的机会。
此外,克里克的“闲聊检验法”起源于他在军中时对抗生素的关注。一天晚上,他在一本科学杂志上看到有关抗生素的最新研究报导,虽然他对于抗生素一点都不了解,他在和朋友聊天时,却不经意地谈及了相关的研究情形。克里克说:“这一点认知对我是个启示,我发现了闲聊测试法。”在此之后,克里克将这个方法运用在他日后的研究方向的决定上,才找到了足以影响他一生的科学领域。
来自薛定谔的影响
影响克里克一生方向的还有一个人,就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薛定谔。薛定谔在1944年出版的《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提到了生命现象以物理化学原理来加以阐释的可能性,并号召物理学家积极投入生命科学领域,从分子层次探讨生命奥秘,克里克天生有着挑战权威、颠覆传统的个性,这本书的问世更将他对于宗教反感的消极想法升华为对于生命本质的积极探索,他意识到自己选择的领域还没有重大的突破存在,还没有足以深入探讨生命本质的核心价值产生。
“是书中包含的神秘吸引了我,生命的神秘和认知的神秘。”克里克激动地回忆当时的感受,“我想更确切得知在这个领域当中,那些神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晚年的克里克(左)和沃森在一起
如果最终我能发现它们某些结构,那将是多么辉煌的事业啊!”强烈而不可遏制的热情带给他无比的智慧与使命感,这本书发动了生物学的革命。克里克与他的工作伙伴沃森都曾因此受到薛定谔的精神感召,全心投入这场空前绝后的历史圣战。确定了人生的方向,接下来的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
揭示DNA的双螺旋结构
1947年,从海军退役后,克里克得到英国医学研究理事学会的资助,进入剑桥大学的斯坦格威斯研究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天资的聪颖与勤奋的研究使得他获得赏识,顺利进入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攻读生物学博士,1954年他以“X射线衍射——多肽类和蛋白质”这篇论文,取得博士学位。
DNA的双螺旋结构发现之旅就此如火如荼地正式展开。克里克在卡文迪许实验室遇见了他终生的工作伙伴——沃森,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式作风:热络、即兴,与即兴的热络;另一个则是英国作风:冷静、矜持、好思考。看似有性情上的不同,却对于DNA都抱有相同的直观与品味:他们都认为DNA的结构是生物学最根本的问题,并凭着直觉掌握了解开DNA核心问题的钥匙。
克里克和沃森一开始就将焦点集中在当时生物学界一个即将被解开的谜团:形成人类基因的分子结构,即脱氧核糖核酸(DNA)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模样呢?他们明白,只要解决DNA结构之谜,那么生命是如何遗传繁衍,以及其它一些相关的基本问题,就有了正确的答案。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决定用X光射线来探寻DNA的分子结构。
起初,克里克与沃森认为DNA的螺旋结构应该是三螺旋,因为当时的生化权威鲍林(L. C. Pauling,1901~1994,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根据量子力学原理,提出了作为量子化学基石的化学键理论,在蛋白质结构研究中提出肽类折叠透过氢键形成α螺旋的学说,鲍林透过多肽链的键结原理,建构出符合晶体X射线衍射分析图的结构模型,并提出了所谓的“第一性原理”,又称逼近法,以作为结构分析的依据。此法从最基本的结构出发,找出所有可能形成的分子结构排列方式,特别考虑到对整个大分子结构与形状具一定影响力的氢键的形成方式;再将所建立起的理论模式与实际X射线图像加以比对,不断修正至最可能的结构。两人运用此法测定各碱基的大小、排列、氢键作用力,以及DNA分子直径、螺距、键角等结构数据,再与衍射图形相比对,以求逼近鲍林所认为的三股螺旋结构。
当时威尔金斯也在研究DNA的晶体结构,但其思路与鲍林不同,他找出DNA三螺旋结构模型的漏洞。之后,克里克与沃森放弃了鲍林这位生化权威的假设,朝另一个方向来发展,改从X光衍射图像来进行分析,考虑衍射点的分布特点,再由数学变换,计算出分子中各种化学键的键长、键角等结构要素。
1953年2月,克里克和沃森从富兰克林的X光衍射图判定DNA的糖-磷酸基骨架在外侧,碱基在内部,而非鲍林所认为的糖-磷酸基骨架在分子中央。
根据许多实验室的研究结果,他们已经推测出合理的DNA模型,在其他研究小组还认为数据不足,还需要更多详尽的研究来支持而犹豫不决时,他们已在1953年4月25日,将他们构筑出的DNA模型发表于英国《自然》(Nature)杂志上,接着他们在5月30日的《自然》杂志上又发表了《DNA的遗传学意义》一文,更加详尽地阐述了DNA双螺旋模型在功能上的意义。但是,当年这个成就并没有立即引起社会大众的注意。这年《自然》共刊出20篇讨论DNA的论文,却只有7篇对DNA的结构进行讨论,克里克与沃森提出的双螺旋模型,不但符合X光衍射的实际数据资料,甚至还隐含着阐释生物遗传物质对于信息的储存与复制的相关机制。
然而,生物学家们就是没有立即看出它惊人的重要性:遗传学的分子基础已经建立。就连鲍林也只是认为他们的模型“看起来很不错”,但仍不认为遗传学的分子基础终于有了扎实的根基。这种情形正和孟德尔当年提出他长年来对于豌豆的遗传学研究,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狭义相对论及质能互换理论如出一辙,都没有引起大众媒体立即的关注。
直到后来有愈来愈多的科学家发现到这个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带来的生物学上无与伦比的重大意义,才渐渐为人所接受。1957年,克里克提出了分子生物学中的重要定理──“中心法则”(central dogma),说明了遗传信息传递的途径,是生命信息从基因单方向传递到蛋白质。1962年,克里克和沃森终于因其在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以及揭开生物遗传信息秘密方面所做的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双螺旋模型的价值与地位于是正式确立。
克里克在事后回忆道:“彼此坦诚相待是合作者之间最基本的一条原则。不管是跟身分比你低很多的人合作,还是跟身份比你高很多的人合作,都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和你之间不可能坦诚相待,其中掺杂了太多的礼数,不能实话实说,这往往就是许多优秀科学家之间的合作最后以失败告终的原因。”
外星细菌研究引发争议
克里克传奇性的一生并未到此画下句点,克里克在1962荣获诺贝尔奖之后,认为分子生物学的框架已经有了,要开创新的领域。此时,他心底那股不可遏制的好奇心又被重新激发起来,他心想分子遗传学的开拓工作已经完成,生命的基本奥秘已经找到了,后续的工作该由其他人来进行。
20世纪60年代末,他将目光转向宇宙中的生命起源问题。1971年9月,克里克在地外文明通信会议上说,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于宇宙高级文明,用无人飞船送到地球上的微生物。有两个事实支持这个理论:一是遗传密码的一致性,表明生命进化中曾在某个阶段越过了一个小种群的环节;另一个是宇宙年龄可能是地球年龄的两倍多,所以生命有足够长时间,第二次从简单的起点进化到高度复杂的文明。克里克用定向生源说表示,某种高级生命有意识地用某种方法把微生物发送到地球上来。
克里克说,如果他的理论是对的,世上的细菌细胞应该是突然出现的,而不会有任何比这些生物更简单形式的前身。因此,这些生物的前身应该是由其来源行星来决定的,不可能在地球上于这么短暂的时间内由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克里克最蔑视的就是支持创造论者的科学家,因为他认为把生命的诞生归功于一位超自然的造物者,而不去从事科学研究,实在是非常不负责任。当然批评者则说,既然外星人无法亲自来到地球,而人类也无法亲自到他们的星球观察生命的来源,那么他的“有方向的泛生源论”不也和“创造论”一样不负责任?而且同样无法解决“第一个生命的诞生”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神经科学研究令人疑惑
进入80年代,克里克又选择再度转换跑道,当时还有两个领域处于蒙昧状态,值得去开天辟地,即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克里克选择了神经生物学,尤其是关于大脑这个他仍一无所知的领域,他的余生也都呆在沙克生物研究所进行有关大脑方面的研究。
克里克在2003年《自然》杂志“神经科学”分卷上发表论文,宣称他的研究小组找到了人类的“灵魂细胞”,并认为人的灵魂与意识的确存在,但不是像一些宗教学家所说的“人类具有永恒的灵魂,肉体只不过是灵魂居住的场所”这样先天就有的,而是由人体大脑中的某群神经元产生和控制的,当时克里克写道:“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哲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将神经细胞和意识产生完美地联结。我们的研究显示,人类的意识不过是由大脑中一小群神经细胞所形成的,这些神经细胞正位于大脑皮质后部到前缘的一小块区域。”这项说法更是受到一些科学家的嘲讽。
2003年6月,克里克(中)获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生命科学院首个生命科学成就奖
此外,克里克还尝试以脑神经生理学的角度来解释梦的产生,他认为做梦是为了进行记忆的整理,在快速眼动状态的快波睡眠时期摒弃无用的信息,避免因信息的过度累积而造成思绪的混乱,而不是为了提醒我们一些重要的事。大脑的脑干产生兴奋,发出信号并引起脑视觉区出现影像,前脑把这些影像勉强编织成梦。
1988年,72岁高龄的克里克说,他已几乎不敢期望自己能再提出任何崭新的观念,“但在我有生之日,我有权去做我觉得开心的事”。后来,他在1994年出了一本备受推崇的畅销书《惊异的假说》。书中提到,克里克提出思维就是一群脑细胞共同作用的结果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的脑功能,包括意识,都是一大群脑细胞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脑细胞的数目太多,它们的相互作用产生了难以解释的功能,这也许正是一加一不等于二这种非线性关系的最生动表现。大脑能够对于大量的图像信息进行立即而快速的处理,也许应归功于其完美的生物配置与大量脑细胞的相互作用。
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
克里克的一生充满了传奇,他是位对知识的狂热永远难以满足的科学家。二战时期,他痴迷于鱼雷的研究与改进;1953年,他发现了DNA双螺旋,1957年,他提出了分子生物学中的重要定理——“中心法则”,说明了遗传信息传递的途径,是生命信息从基因单方向传递到蛋白质。20世纪60年代末,他将目光转向宇宙中的生命起源问题。进入20世纪80年代,他又突然跳到了神经科学领域。
克里克一生荣膺美国国家科学院、英国皇家学院、法国科学院以及爱尔兰学院的院士,当然最重要的莫过于至高无上的诺贝尔奖。伦敦大学学院教授琼斯称克里克是“20世纪的达尔文”,他说:“20世纪有两大象征符号,一是原子弹的蘑菇云,另一个是DNA双螺旋。”这位“分子生物学之父”的突破带来的重大变革,即使至今,一样对我们影响很大。
今天“生命科学”所有领域,无论是基改生物、基因疗法、DNA指纹乃至于生物学的圣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都要归源于最初1953年那一场重要性不亚于达尔文的演化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生物学革命。
虽然克里克晚年时期的研究多遭人诟病,但是在克里克曾任教的圣达戈索尔克生物研究院,现任院长里查德 · 墨非还是说:“历史将证明克里克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生物学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