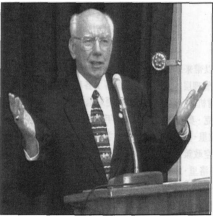1974年,来自美国凯尔文学院的核物理学家赢得了肯特郡议会议员的席位,这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他就是弗农·埃勒斯(Vernon Ehlers,下图)博士。当时他的竞选对手包括两位独立竞选人和一位市议员,结果埃勒斯大获全胜,之后在密歇根州服务了20年,1993年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
埃勒斯是美国国会中倾力支持科学项目的代表之一,提倡在科学教育上引入更多的责任追究制和更高的检测标准以及科学家要对社区责任身体力行,同时他也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局长迈克尔·格里芬(Michael Griffin)的坚定支持者。不久前,他接受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克里斯·威尔森(Chris Wilson)的采访,回答了关于为什么科学家可以成为有责任感议员等提问。
记者:作为一名科学家,您的政治主张和您的同行有什么不同?
埃勒斯:科学家习惯于与事实而非构想打交道。对拉什·霍特(Rush Holt,物理学家、国会议员)来说是这样,对我也是如此。我们并不想卷入政治游戏,虽然我们完全有能力玩好这个游戏。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比很多人更加懂得其中的规则,但我们视其为对生命的浪费。我们也许已经是超负荷运行了,因为国会中科学家或者与科学相关的议员屈指可数,而有太多的议案又涉及到科学方面,人手严重不足。
记者:最近,国会某委员会就NASA向媒体隐瞒一桩航空安全问题召开了听证会,公开对该委员会将迈克尔·格里芬从正在进行的航天飞行任务的关注中强行召回的做法表示质疑。原因是什么?
埃勒斯:我不满地是他们抓小放大,白白浪费了NASA局长的时间。而且据我所知,这场听证会只不过是为了在政治上争取主动,让布什政府蒙羞。我对于这类事情向来不能容忍。
记者:您这种”就事论事”的作风,在您的科学家良心说不的时候,是不是容易与您的党派在投票上产生争议?
埃勒斯:假如从科学的角度看一个议案,我认为没什么不好,我会投赞成票。不然的话,我肯定投反对票。曾经有好几次,我被要求投票赞成某些看似根本是胡说八道的提案,我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不能投”。
去年,有个将宾西法尼亚某小镇命名为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美国著名作家)的提案。反对的人到处散发诋毁卡森的传单,声称她不人道,认为卡森呼吁禁用农药DDT后,上百万本不该死去的非洲儿童(传单中如是说)死于疟疾疾。这根本是胡说八道。我无法理解这些人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并向一些人解释了其中的道理,说服了他们,然而对于舆论的导向我回天乏力。
记者:最近,我们报道了前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Sputnik)的50周年纪念活动,不少人觉得美国人需要另一场刺激才能意识到加强科学教育的重要性。你的观点是什么?
埃勒斯:这个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当年“旅伴“发射的时候,只不过现在没有那么令人瞩目。我在倡导加强数学和科技教育方面花了不计其数的心血,从学龄前儿童到大学生(主要集中在小学和中学阶段)。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今天我作为议员在这里接受你的采访就是其中之一。科技教育已经被列人“有教无类"(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中,今年将会开始科技方面的全国统考。同时我们也在努力让科技统考的成绩列入学校“年度进展”考评的内容。我不知道是否能得到通过,因为支持和反对的声音都有。
记者:您是否认为科技教育应“物理优先”,学生们应该先学物理然后再接触化学和生物学?
埃勒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先学物理在某些方面可以为生物学和化学做准
备,从这个角度看确实有道理。如果让我来选择,我会让学生们在九年级的时候从物理入门,然后学习化学,之后是生物学。这样他们升入高年级后就可以系统地学习一些有意义的物理课程,即严谨的物理科学。也就是说,九年级学生学到了一些人门的概念和定义,之后逐渐接触到物理学的真正内涵。不过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小学教育上,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开始,后面的一切都是浪费。
真正重要的阶段是社区大学。学生们高中毕业以后都觉得:“哦,天哪!我不得不找个工作了。”于是,他们就会上社区大学,接受更多的数学、物理以及其他的科技教育。
记者:这一切都是怎么开始的?
埃勒斯:当我进入议会后,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众议院议长)让我写一篇有关科技政策的报告,同时还让我负责众议院的电脑化办公,这可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工作。当我写完报告后,大多数人只是礼节性的表示:“嗯,报告不错。”只有一个人说报告很糟糕。现在,越来越多的文章然后引用我的报告来阐述美国的科技政策。因此,要让大部分人接受无非是个时间问题。当我成为国会教育委员会成员后,科技教育被列入”有教无类“法案,这和我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其间,我的一位好友山迪·克莱斯(Sandy Cress)给了我很大的帮助,他是布什总统的朋友,志愿为白宫推动“有教无类”法案并担任了联络人。我和他非常熟识,他的科技教育理念与我完全一致,因此也影响到了总统。
众议院原先提出的“有教无类“法案非常完善,但在参议院审核时受到了一些阻碍,不得不做出部分修改。该法案没原先那么尽善尽美了,也因为我没能出席那次的审核会,所以没办法提出反对意见。
记者:现在的大人物们是不是比以前更加怀疑科学了?
埃勒斯:我认为情况向来如此,伽利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人们乐于接受那些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基本世界观或者信仰的科学。温室效应也很能说明问题。我经常想说的是,在很多情况下理智的对立面不是蛮不讲理,而是情绪化。我对每个人的宗教信仰都非常支待,如果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会直说:“我觉得你是错的。”但我肯定是非常郑重地说这些话的,不像卡尔·萨根(Carl Sagan)以及其他某些人,会嘲笑挖苦他们。进化论就是主要的一个争议,但是我会跟别人说:“你看,我们也许50年后还说不清楚谁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还有很多研究工作需要做。”
在美国众议院科学和技术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期间,埃勒斯与比尔·盖茨谈论美国的科学与创新问题
记者:那么,一位热心公益的科学家应该做些什么?
埃勒斯:当我和科学家或工程师们交谈的时候,会鼓励他们从一些小事做起。首先,和当地社区交流。我总是向他们讲述吉姆·山森布雷纳(Gim Sensenbrenner)的事例。他是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科学家经常找他要研究经费。他总是先问:“你跟当地的扶轮社谈过你的项目了吗?”这总让他们措手不及。然后他就会说:“如果你连当地社区的支持都得不到,又怎么能够指望得到国会的支持呢?”所以我鼓励科学家去当地社区传播科学,解释现象,阐明其中的好处和不足,尤其是目前大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
同时,我也支持他们去自己孩子的学校,为学生们讲解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我本人直到进了
大学才真正接触到科学家。我在一个800人的小镇中长大,从小对科学感兴趣,但我从来没有成为科学家的梦想。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他们和孩子们进行交谈,带孩子们去他们工作的实验室和建造的大桥参观游览,这都将有助于孩子的发展。
记者:我们还能有幸在政府中看到更多的科学家面孔吗?
埃勒斯:我也鼓励这些科学家在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但他们经常一笑置之。他们尊重我的作为,但是他们不想如此。我认为他们的根本问题在于喜欢和合理的流程打交道,而国会中往往缺乏这点,这也是他们不愿意介人政治的原因。
记者:您是如何成功的?
埃勒斯:当初我参加竞选时没人看好我,我只不过是个无名之辈。我的一名竞选对手是千万富豪,另一个是千万富豪的公子,还有一位是市议员。不过我知道怎么竞选,那时我正在主持一个环境保护的项目,因此得到了环境保护组织的支持。
如果你只是挨家挨户的散发竞选传单,那传单转身就会被丢进垃圾桶里。我的竞选策略中的一条是,“当挨家挨户宣传时,给点人家不会扔掉的东西。“我在主持环保项目时想到了这个主意,在一个保丽龙杯子里种了1棵云杉树的幼苗,然后在杯子上贴了一个标签写着“保持肯特郡的绿色,种下这棵树,投弗农一票”。
我还指导他们如何种植云杉,比如要放在厨房的窗台边,需要的水量是多少,到了11月中旬就必须种到土里去等等。市议员们非常惊讶,他们没想到我在政治上还挺有一套。
记者: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会对立法过程大失所望吗?
埃勒斯:我在环境保护上取得了不少成果,包括在密歇根州通过的环境法案比其他各州的都要完备。此前我从来没碰到过立法上的问题,原因是我致力于立法程序本身,而非政治博弈。现在到了华盛顿,这边的政治完全不同。要使一项法案得到通过,你需要耗费最大精力,必须说服很多观点不同的人,而利益相关的集团数不胜数。尤其是环境保护方面,要得到一致的意见难上加难。我主要的成绩就是通过了《美国大湖遗产法》,为了让其通过,我用了在密歇根州的老办法,把所有的利益相关方拉到一起。
这一套在华盛顿就行不通了,这边的人看起来很享受这种“僵持”的风格。具体到某一项涉及民生的工程,商业大亨们希望事情在自己的掌控中,环境保护者们则筹措了大量资金上下游说,而此时你要做的是协调种种利益的相关者,才能让某项法案纳入立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