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于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中,物理学家绕着一条17英里长的轨道射出质子,让它们以几乎等于光速的速度对撞在一起。这是全球最需要精细调节的科学实验之一,但是当物理学家试图理解量子残骸时,他们开始使用一种异常简单的名叫“费曼图”的工具,它与一个小孩描绘这一情况的方式并没有多少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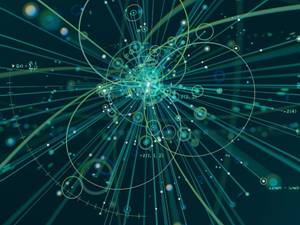
粒子对撞以某种方式与数学中的“主题”产生了联系
20世纪40年代,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设计出了费曼图。费曼图中的线条代表基本粒子,它们会合于一处顶点(这代表了对撞),接着从那儿分离,代表对撞中出现的东西。那些线条要么独自发射,要么再次会合。连锁碰撞可以像一位物理学家敢于认为的那么漫长。
物理学家给示意图添加上代表相关粒子质量、动量和方向的数字。接下来,他们开始一段费力的计算步骤――求这些量的积分,加上那个量,求这个量的平方。最终的结果是一个数,名叫费曼概率,它量化了粒子对撞如示意图中一样进行到底的概率。
“在某种程度上,费曼发明了这种示意图是为了把复杂的数学编码成一种账目登记方法。”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谢尔盖·古科夫(Sergei Gukov)说道。
费曼图多年以来一直服务于物理学家,不过它们也有局限之处。第一个局限是它需要严格的步骤。物理学家在追踪越来越高能的粒子的对撞,这要求有更高的测量精确度――随着精确度的提高,需要通过计算来得出预测结果的费曼图的复杂程度也随之增加。
第二个局限是费曼图的更加基础的性质。费曼图建立在一条假定之上:越多潜在的粒子碰撞和次碰撞被囊括进来的话,它们的数字预测值会更加准确。这种计算步骤被称为“摄动展开”,对于电子的粒子对撞分析的效果非常好。(在这类情况下,弱力和电磁力占据主导地位。)它对高能对撞分析――如质子之间的对撞,在这种情形下,强核力占据上风――效果就不怎么好。在这些案例中,囊括进更广泛范围的碰撞――通过绘制更加错综复杂的费曼图――事实上能让物理学家误入歧途。
“我们知道一个事实,到某个节骨眼上,费曼图开始(与现实世界的物理学)产生分歧,”牛津大学的一位数学家弗朗西斯·布朗(Francis Brown)说道,“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如何估量到哪个节骨眼时应该停止计算示意图。”
然而,我们有理由保持乐观。在最近十年里,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已经在探索一种让人惊讶的通信方式,有可能会让可敬的费曼图获得新生,在物理和数学两个领域都产生影响深远的洞见。这与一项奇特的事实有关,即从费曼图中计算得出的数值看起来正好与一个名叫“代数几何学”的数学分支中出现的一些最重要数字相匹配。这些值被称为“主题周期”(periods of motives),而且没有明显的原因表明为何相同的数字要出现在两种背景中。实际上,这点的奇特程度堪比你每次测量一杯稻米,观察到稻米的数量都是质数这种假设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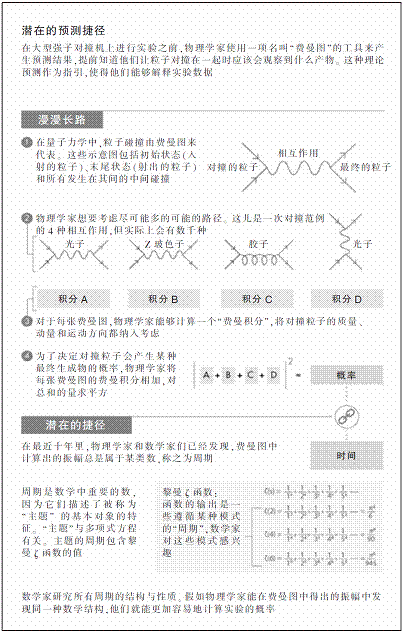
“从自然到代数几何学再到周期,存在着一种联系,以后知之明来看,这并非巧合。”柏林洪堡大学物理学家迪尔克·克赖默(Dirk Kreimer)说道。
如今,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正在合力解开这种巧合。对于数学家而言,物理学让一类特别的数字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想要弄明白这些发生在物理学中的周期是否有着一种隐藏的结构?这类数可能拥有什么特殊的性质?对于物理学家而言,那类数学领悟的回报会是一种全新的先见,帮助预期某些事件在紊乱的量子世界会如何运行。
再现的主题
今时今日,周期是数学中最抽象的研究主题之一,但它们一开始诞生是出于更具体的利害关系。17世纪早期,伽利略·伽利莱等科学家饶有兴趣地琢磨要如何计算钟摆完成一次摆动所需的时间长度。他们意识到,计算可以归结为取得一个函数的积分(一种无限项和),这个函数里包含了有关钟摆长度和释放角度的信息。同时,约翰内斯·开普勒使用类似的计算方法,确定了一颗行星要绕着太阳周转所需的时间。他们称这些度量值为“周期”,确定它们是与运动相关的最重要测量值之一。
在18和19世纪,数学家们普遍变得有兴趣来研究周期这回事――不仅是因为周期与钟摆或行星有关,也是因为对x2+2x-6和3x3-4x2-2x+6多项函数求积分而生成的一类数。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诸如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和莱昂哈德·欧拉等著名数学家探索了周期的领域,发现它包含了许多特征,指向某种潜在的秩序。在某种意义上,代数几何学――它是研究多项式方程的几何形式――在20世纪作为一种追踪那种隐藏结构的方法而得以发展。
20世纪60年代,这一努力获得快速发展。在那时,数学家已经完成了他们经常会做的事情:他们把方程式这类相对具体的对象转变成更为抽象的对象,他们希望这样会允许他们确定起初并不明显的关系。
这一步骤首先是要研究多项式函数类型的解所定义的几何对象(也被称为代数簇),而不是研究函数本身。接下来,数学家们试图理解这些几何对象的基本性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发展了一种被称为上同调理论的工具――用这种方式能确定几何对象的结构特征,又不用考虑用来生成对象的特定多项式方程。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上同调理论已经激增到了开枝散叶的程度――奇异上同调、德拉姆上同调、平展上同调,诸如此类。看起来每个人都对代数簇的最重要特征有着不同的看法。
在这片混乱的研究领域,2014年过世的前沿数学家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Alexander Grothendieck)意识到,所有上同调理论都是同一样东西的不同版本。
“格罗滕迪克观察到的东西是,在代数簇的例子里,无论你如何计算这些不同的上同调理论,你总是不知怎么地发现相同的答案。”弗朗西斯·布朗说。
这个相同的答案是所有这些上同调理论核心的独一无二的东西,被格罗滕迪克称之为“motive”。“在音乐中,motive的意思是再三出现的主题。对于格罗滕迪克而言,主题是以不同形式反复出现、但其实一模一样的东西。”皮埃尔·卡蒂埃(Pierre Cartier)说道,他是一位在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工作的数学家,也是格罗滕迪克的昔日同事。
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多项式方程的基本建筑材料,正如质因子是更大的数的基本成分。主题也有与它们相关的数据。正如你可以把物质分解成元素,指明每种元素的特征――原子数、原子质量,诸如此类――数学家们也把本质的测度归属于某个主题。在这些测度中,最重要的一项是主题的周期。假如某个多项式方程的系统中产生的主题的周期等同于另一个不同系统中产生的主题的周期,你就知道这两个主题是一样的。
“一旦你知道了周期(这是特定的数字),那几乎等于知道了主题本身。”牛津大学的一位数学家金明迥(Minhyong Kim)说道。
要看到相同的周期在出人意料的背景下出现,一个直接的方式是看π的情况。“这是获得周期的最著名的例子。”卡蒂埃说道。π在几何学的许多伪装中出现:在定义单维圆的函数的积分中,在定义双维圆的函数的积分中,在定义球体的函数的积分中。这个相同的值会在看起来如此不同的积分中反复出现,对于古代的思想家来说,这很可能是个谜团。“现代的解释是,球体和实心圆有着相同的主题,因此必定有着基本上相同的周期。”布朗在一封电邮中写道。
费曼的艰辛之路
如果说在很久以前,好奇的头脑想要知道为什么π这类数值在圆形和球体的计算中突然出现,那么今天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会想要知道为什么那些值在不同种类的几何对象(费曼图)中出现。
费曼图有着基本的几何学特征,由线段、射线和顶点构成。为了理解它们是如何构造的,它们为何在物理学上有用处,请想象一个简单的实验安排,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对撞,生成一个渺子和一个反渺子。为了计算这种结果发生的概率,一名物理学家会需要知道每个入射粒子的质量和动量,也要对粒子所沿的路径有所了解。在量子力学中,粒子所走的路径可以想成是它可能遵循的所有可能路径的平均。计算那条路径变成了对所有路径的集合求积分,这个积分被称为费曼路径积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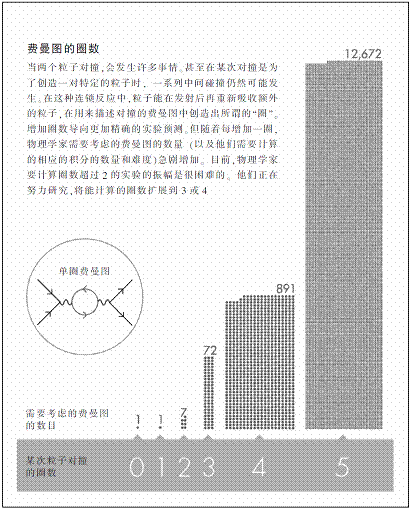
粒子对撞从开始到结束可能遵循的每一条路径能用一张费曼图来代表,每一张费曼图都有它与自身相关的积分。(费曼图与它的积分是等同的。)要从一组特定的起始情况中计算某种特定的结果的发生概率,得要考虑能描述对撞过程的所有可能的费曼图,求得每个积分,再把那些积分相加。那个数字是费曼图的振幅。物理学家接着求这个数的平方,获得概率。
对于一个电子和一个正电子入射、一个渺子和一个反渺子射出的情况,这个计算步骤很容易执行。但那属于无聊的物理学。物理学家真正关心的实验是和带圈的费曼图有关的实验。所谓的圈代表这种情况:粒子射出后重新吸收额外的粒子。当一个电子与一个正电子对撞,在最终的那对渺子和反渺子出现之前,可能有无数次的中间碰撞发生。在这些中间碰撞中,光子之类新粒子被创造出来,它们在被观察到之前就湮灭了。入射和射出的粒子与之前描述中一样,但事实是那些没有被观察到的碰撞仍然对最终产物有着细微的影响。
“这就像Tinkertoy玩具。一旦你画了一幅费曼图,根据理论规则,你就能连接上更多线条。”弗利普·塔尼多(Flip Tanedo)说道,他是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一位物理学家,“你可以连上更多的短棒、更多的节点,让它变得更加复杂。”
通过把圈考虑进去,物理学家们提高了实验的精确度。(增加1圈就像把1个值计算到重要的位数。)但他们每次增加1圈,需要考虑的费曼图的数量――相应的积分的难度――随之急剧增加。譬如说,一个简单系统的2圈版本可能只需要1张费曼图。同个系统的两圈版本需要7张费曼图。3圈版本就需要72张费曼图。增加到5圈的话,计算要求考虑大约12 000个积分――这个计算量简直要用几年时间来解决。
相比于费力地计算这么多乏味的积分,物理学家会想要光看下某个给定的费曼图的结构,就能对最终的振幅有所感觉――正如数学家可以将周期与主题建立联系。
“这个步骤如此复杂,积分是如此困难,所以我们想要做的事是只用看一眼费曼图,就能窥见最终的答案,最终的周期积分。”布朗说。
令人惊讶的关联
1994年,周期和振幅被首次呈现在一起,这是迪尔克·克赖默和英国公开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大卫·布罗德赫斯特(David Broadhurst)合作的成果,他们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这一工作让数学家们推断,所有振幅都是混合泰特主题的周期,泰特主题是一种以哈佛大学荣休教授约翰·泰特(John Tate)命名的特定主题,其中所有周期都是数论中最具影响力的黎曼ζ函数的多值。在1对电子-正电子入射、1对渺子和反渺子射出的情况下,振幅的主要部分结果是黎曼ζ函数在赋值为3时计算结果的6倍。
假如所有振幅都乘以ζ值,这会给予物理学家一类定义良好的数字,让他们可以着手工作。但在2012年,布朗与他的合作者奥利弗·施内茨(Oliver Schnetz)证明实情不是那样。尽管今日的物理学家们遇到的所有振幅都可能是混合泰特主题的周期,“有一些怪物潜藏在暗处,会给研究造成阻碍。”布朗说,那些怪物“肯定是周期,但它们不是人们所企盼的那种美妙和简单的周期。”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们确凿知道的是,看起来费曼图的圈数和数学中称为“权”的概念之间存在着关联。权是一个与被积分空间的维度有关的数字:在一维空间上的周期积分可以有0,1或2的权;在二维空间上的周期积分可以有最高为4的权,依此类推。权也可以用来把周期分成不同类型:所有权为0的周期据推测是代数数,可能是多项式方程的解(这还未被证明);钟摆的周期的权总是为1;π是权为2的周期;黎曼ζ函数的值的权总是为输入值的2倍(所以ζ函数在赋值为3时有着为6的权)。
这种依照权对周期的分类可以沿用到费曼图上,费曼图中的圈数不知为何与它的振幅的权相关。没有圈的费曼图有着权为0的振幅;带1圈的费曼图的振幅都是混合泰特主题的周期,有着至多为4的权。对于圈数更高的费曼图,数学家们怀疑这种关系会延续下去,尽管他们还无法窥见其中的奥秘。
“我们研究到更高的圈数,我们看见更为普遍类型的周期,”克赖默说道,“数学家对此真的很感兴趣,因为他们对不属于混合泰特主题的主题了解不多。”
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目前在前溯后推,试图为这个问题建立范围,寻找精巧的解答。数学家们向物理学家们推荐使用函数(和它们的积分)来描述费曼图。物理学家构思出粒子对撞的配置方案,以此来超越数学家得要提供的方程。“看到他们那么快地吸收相当具有技术性的数学想法,这点让人惊奇,”布朗说,“我们已经用完了经典的数和方程,没什么好给物理学家了。”
大自然的群
自从微积分在17世纪创立起,在物理学世界中出现的数字推动了数学进步。如今也是这样。事实是,从物理学中得出的周期“有点上帝赐予的味道,来自于物理学理论意味着它们有许多结构,一位数学家一定不会想到或试图创造的便是结构。”布朗说道。
克赖默补充说:“看起来,大自然想要的周期是比数学家能定义的周期更小的集合,但我们无法非常清楚地定义这个子集其实是什么。”
布朗指望能证明有一种数学群――一种伽罗瓦群――对来自费曼图的周期集合发挥影响。“在至今每一个被计算过的案例中,这种解答看起来都很正确。”他说道,但要证明这种关系绝对成立仍然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假如这是真的,确实存在一个群对出自物理学的数施加影响力,那意味着你寻找到一类数目庞大的对称。”布朗说,“假如那是真的,那么下一步是探问为何存在这么大的对称群,它可能具有什么潜在的物理学含义。”
此外,它会从两个十分不同的背景下加深基础几何构造间早已存在的刺激关系:一个是主题,它是数学家在50年前设计出的,为的是理解多项式方程的解答;一个是费曼图,它是对粒子对撞如何进行的图解呈现。每一张费曼图都有附着的主题,但某个主题的结构对于相关费曼图的结构到底能告诉我们什么内容,这点仍然未知,有待各位的猜想。
资料来源 Wired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