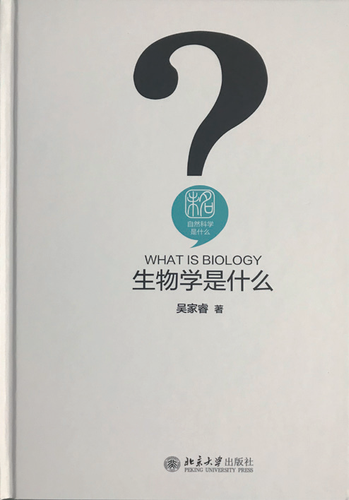在他书中探讨的五个问题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对生命系统不确定性的讨论。 他在书中指出:“生物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研究者的决定论思维与生命的偶然性特征之间的冲突。”他所提出的这个命题,其意义远远超出生物学的范畴。
《生物学是什么》吴家睿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近日,收到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吴家睿教授签名赠送的大作《生物学是什么》。之前,看到他在朋友圈介绍此书的出版:“几十年的感悟、近十年的打磨,终于出了个细活了。”欣慰与欣喜之情跃然屏上。看到他的大作真身,的确让人眼前一亮——全书五部分,每一部分都指向当下生物学的一个关键问题:解析生命的有序性、破译生命的信息流、建立生命的统一性、揭示生命的区域化、重构生命的复杂观。的确有高屋建瓴之势。
说来惭愧,我迄今与吴教授还无缘谋面。但多年前就从芝加哥大学龙漫远教授那里听到对他的激赏之词。后来,因为龙教授约我为吴教授作为副主编的《新生物学年鉴2015》写一篇稿子,承蒙该书编辑、科学出版社的王静把我拉到一个微信群中,我得以和吴教授有了微信交流的渠道。从吴教授在朋友圈所发布信息中,我知道他对精准医学有系统的思考。他在其公众号《吾家睿见》发布的“后基因组时代的生命观”一文中还引用过我和葛颢、钱纮2018年发表在Science China Life Science上的有关“活”是“结构换能量循环”的观点,表明他也在关注我的一些研究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虽然他研究人类疾病,我研究植物形态建成,从各自研究领域来说不在一个圈子,但在对生命现象的深层次思考中多少有些交集。这使得我可以不揣冒昧地对他的大作表达一些我粗浅的感受。
坊间提到生物学问题,大家都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生命是什么”。在亚马逊网站上,我查到的以“What Is Life”为书名的名家著作起码有6本。但以“生物学是什么”为书名的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当然之前曾经看到过著名的演化生物学家和生物学史家恩斯特 · 迈尔(Ernst Mayr)用霸气侧漏的“This Is Biology”为书名的书。用一个在飞速发展的研究领域(生物学)为书名来写书,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从书的出版信息页我得知,这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策划的《未名 · 自然科学是什么》丛书中的一本。通过向该丛书的策划编辑杨书澜老师请教,得知她策划此套丛书的初衷,是为希望了解这个世界的人提供一个高品质的入口。为此,她经过精心权衡,请到业内高水平专家,希望他们从“是什么、为什么、如何做”这些涉及学科本质的方面,为读者勾勒出一个学科的基本框架。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吴教授非常巧妙地以不厚的篇幅,写出这样一本如他自己所说的“供外行看热闹、供内行看门道”,又能表达自己对生物学理解的书。足见作者的学养深厚。
在他书中探讨的五个问题中,我最喜欢的是他对生命系统不确定性的讨论。他在书中指出:“生物学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来自研究者的决定论思维与生命的偶然性特征之间的冲突。”他所提出的这个命题,其意义远远超出生物学的范畴。
决定论思维由来已久。在与人类具有共同祖先的黑猩猩中,就可以发现对确定性的追求。从珍 · 古道尔(Jane Goodell)拍摄的《黑猩猩》视频中可以发现,黑猩猩居群会为保卫它们的无花果树而与入侵者殊死搏斗。为什么?无非因为无花果树是它们确定的食物来源。它们需要确定性来满足自身对安全感的需求。人类有更高的认知能力,于是把对确定性的追求上升为决定论思维。
人类有史(无论是口述的还是文字记载的)以来,以决定论形式表现出来的对确定性的追求一直是认知能力发展的一个主题——从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到上帝崇拜。各种星象占卜,无非都是希望窥视冥冥之中决定人生的“命运”。即使是始自伽利略时代的自然科学,最初的诉求也是希望以探索上帝创世的奥秘来理解上帝的伟大,顺便掌控人类的未来。这种思潮的代表性表述,就是吴教授在他的书中引用的“拉普拉斯妖”。
尽管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量子力学到生物统计的不同时空尺度的自然科学研究中,人们已经意识到,人类生存的大爆炸宇宙,不过是一系列随机事件的结果。令人遗憾的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决定论思维因为其能够在特定时空尺度内提供可预测性,并因此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方式、冲击了之前长达上千年的传统神创论版本而深入人心,甚至被长期地误认为是“科学”的代表。或许对于改变人类认知中已经存在了上万年的决定论思维偏见而言,对随机性认知的一百多年的历史还是太短了。
讲到把牛顿力学误以为是“科学”的典范或者代表,就不免回到本书所属丛书的主题“自然科学是什么”的问题,再讲几句与“科学是什么”有关的话。我在为李峰、王东辉的译著《生命的历程》(Scientific Process and Social Issues in Biology Education)——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生物科学史家和普通生物学著名教授加兰 · 艾伦(Garland Allen)和他的朋友杰弗里 · 贝克(Jeffery Baker)——所写的序中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即“科学”本质上是一种认知形式。与其他认知形式相同之处,在于科学认知也是一种对周边自然的解释,因此也要追求合理性(即合逻辑性)。不同之处,在于科学认知能够以实验为工具,为合理认知提供客观性基础(追求客观性)。这使得科学认知可以帮助人类更接近和理解不依赖于人类解释而存在的自然,从而更好地与之共存。在那个序中我没有提到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科学认知还具有开放性——因为它以实验为工具所检验的是“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科学研究的过程,就是证否所能检验的无效假设,然后不得不接受把“备选假设”(alternative hypothesis)作为暂时的结论;一旦新方法和新信息出现、之前接受的暂时结论被证否,人们又不得不放弃这些结论(虽然常常会经历各种挣扎),接受以新的备选假设作为新的暂时结论。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科学认知可以在探索未知自然的过程中,不断突破既存观念体系(解释)的束缚而获得新的认知空间。如果我们承认科学认知具有开放性,那么就不得不接受一个现实,即在对未知的探索过程中存在多种可能性,于是就不得不面对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决定性思维从逻辑上看,是一种违反科学认知基本特征的非理性思维。
我不知道吴教授是不是认同我对决定性思维的解读和科学认知三个特点的看法。如果读者拨冗去读我在睿n公众号上发布的“白话”专栏,会发现我对生命系统有与吴教授书中所述略有不同的解读。这种不同,不正反映了科学作为一种认知形式的开放性吗?人类的认知,不就是在开放的过程中才得到不断拓展的吗?去读读吴教授的《生物学是什么》,开卷有益!
本文作者白书农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