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双螺旋结构*问世,该模型的构建者J·沃森、F·克里克声称:他俩之所以热衷于探索遗传物质的分子结构,乃得益于薛定谔的著作《生命是什么——活细胞的物理学观》(以下简称为《生命》)的启示。书中有一些卓越的预见。从薛定谔发表这些见解(1943年)到双螺旋模型建立正好十年。薛氏作为量子力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员,对生命本质问题作出深入思考,其影响可算不小;后人常称他为分子生物学的先驱者。五十年来,分子生物学崛起并发展,直至现代生物工程酝酿而形成,都离不开对于物理学的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实验手段的全面应用。
从生命的宝藏中汲取美
薛氏著作里有这样一段引语:“存在是永恒的,因为有许多法则保存了生命的宝藏;而宇宙从这些宝藏中汲取了美。”(歌德的诗句)非生命物质世界里的运动规律很美,而生命物质世界里亦充满着无数宝藏,其美学蕴含或许更为丰厚。DNA结构恰是其鲜明一例。
DNA是双链,并具有双向螺旋对称性,双链之间又通过碱基的互补配对而相互联结。碱基只有四种:腺嘌呤(A)、鸟嘌呤(G)、胸腺嘧啶(T)、胞嘧啶(C)。唯有当A与T、G与C配对时,这双链分子才显得十分规则。双链中的任意哪一条上,四种碱基排列的顺序是一定的;既为互补配对,一条链上的顺序必然决定另一条链上的顺序。这样呈现螺旋对称性和互补对称性的双链结构看起来还相当简洁明了。物理学的理论模型往往富有对称美和简洁美;这DNA结构模型亦然如此。无怪乎沃森等人当该模型一建立,便意识到:“如此雅致美观的结构非存在不可”;的确,生命宝藏赋予全宇宙以无限美妙,其中所遵循的真理法则本是永恒存在着的——薛定谔及其信服他的生物学家们都理解这一点。

图为E·薛定谔
可见,玻尔互补原理在生物学研究中也有实际的效用,正如玻尔本人所料想的那样。DNA螺旋链上的碱基排列决定了遗传信息构成,即遗传因子(基因)编码。而且碱基互补配对使双链之间以氢链相耦合;氢键易被打断(解旋),分离的两条链分别作为模板,仍然按照A-T和G-C的互补配对原则,重又形成新的双链,于是就完成了DNA的复制:一个DNA分子变成两个同样的DNA分子。沃森和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公布这个模型时提及:“我们当然注意到所设想的专一碱基对直接揭示了遗传物质的一种可能的复制机理”。用该模型——既是双链、双链之间又以专一方式相耦合——确实可具体解释生物体中DNA及其所携带的遗传信息所具有的复制功能;这或许就是该模型成立的关键。因此,凭借互补对称性,双螺旋结构成为一个理想、完善的DNA分子模型,它乃分子生物学作为生物学现代发展之重要里程碑的标志。
细胞内的遗传因子编码的载体——染色体由DNA和蛋白质组成;实际上,遗传物质就只是染色体中的DNA。薛定谔在《生命》一书中指出:“活细胞的最重要部分——染色体纤丝,可以恰当地称之为非周期晶体,……那正是生命的物质载体”。“……基因这个名词,把它作为一定的遗传特性的假设性的物质载体”。薛氏明确肯定生命的物质基础,假设生命及其遗传信息的物质载体便是一些非周期晶体;也就是说,遗传基因大分子正是由大量原子按照一定顺序排列起来的非周期晶体。他并指出,晶体结构的稳定性导致基因的不变性。这种晶体与固体物理所研究的周期晶体当然有所区别;薛氏的假设以晶体是否具有周期性而体现了非生命物质与生命物质在分子结构上的异同。他还把这两种结构分别比喻为花纹重复的糊墙纸和巧夺天工的刺绣,后者更复杂精致得多。
显而易见,沃森和克里克等人对DNA分子的螺旋链结构的设想,其起因之一,是受了薛氏假设的一点启发;而这些分子生物学家对基因的定义——基因是一段DNA,基因是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也正符合薛氏的断语。书中还说明,在这非周期晶体的结构中,其原子有种种可能的排列,不同的排列形式就相当于遗传的种种微型密码。那末,可看作非周期晶体的遗传物质分子以及遗传密码这两个概念,后来显然成为分子生物学家研究基因本性、探索携带遗传信息的DNA分子、蛋白质分子和其他生物大分子的结构的出发点;它们恰恰是生命宝藏中的精华,进而便成为现代生物工程的重要根基。它们显示出任何哪种非生命物质都无法与之匹敌的“美妙的规律性和秩序性”。
生命与熵负
生命物质系统有两大特性:自我复制和新陈代谢。二者使生物体(生命有机体)生长、发育,具有生机和活力;否则,生物体就会枯萎、死亡。生物体从外界吸收养料,同时排出废物,吐故而纳新。以运动方式的语言来说,随着生物的进化以及单个机体的生长和发育,其生命运动渐趋复杂、并有序化。薛定谔发展了热力学中的熵概念,藉以描述生命运动的进程。
玻尔兹曼把熵定义为物质系统内分子的无序程度;即熵正比于分子之无序度的对数。而热力学第二定律说明:孤立系统(与外界无物质、能量交换的系统)里发生的自然过程总是沿着熵增加的方向进行,那末该自然过程中分子的空间状态就从有序转向无序。
薛氏在《生命》中指出:“生命似乎是物质的有秩序和有规律的行为,它不是完全以从有序转向无序的倾向为基础的,而是部分地基于那种被保持着的现存秩序”。生物体不是孤立系统,它的熵不总是在增加;反过来说,倘若熵增加,并最终趋于其最大值,则便是死亡。“要摆脱死亡,亦即要活着,唯一的办法就是从环境里不断地汲取负熵”;“有机体是依赖负熵为生的,或更确切地说,新陈代谢中本质的东西,乃是使有机体成功地消除了当它活着时不得不产生全部的熵”。有机体从环境吸收的养料是低熵物质(有序程度高),排出的废物是高熵物质(有序程度低),净收入的便是负熵,以抵偿机体本身的熵增;从而保持甚至提高机体及其生命运动的有序程序,以促使机体生长、发育和健全地生存。
薛定谔将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生命运动进程,提出负熵概念作为生命的热力学基础。鉴于熵的原有定义,他把负熵定义为系统之有序度的对数。从熵到负熵,熵原理及其涵义的拓宽,不仅可用来描述孤立系统,还可用来描述开放系统;不仅可用来描述非生命物质系统,还可用来描述生命物质系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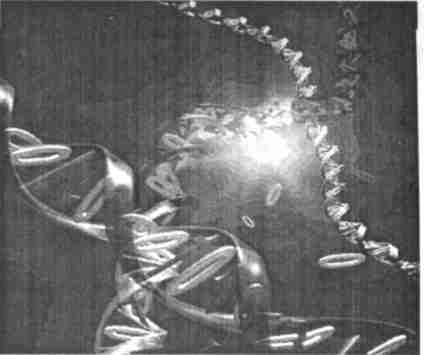
图为DNA双螺旋结构
薛氏立论:有机体以负熵为生,既使高级的生命运动得以凭借物理学定律简洁地解析,又指明了生命物质与非生命物质、孤立系统与开放系统在运动进程上的不同。薛氏的论点受到生物物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的欢迎,例如普利高津所建立的耗散结构理论里就采用了这一负熵概念。如今,其涵义已拓宽了的熵原理被当作应用面广泛的普遍原理,甚至将其用来解释社会发展规律:建立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结构系统,必须不断地抵偿其内部的熵增;即不断地通过各类社会改革克服种种弊端、混乱以取得负熵,从而保持系统本身的稳定并日趋完善。所以说,薛定谔的这个论点或许已成为现代生物工程所需依据的一个基本观念,而其影响所及又远远超出生命科学范畴。
现代生物工程是否会揭示新的物理学定律
与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相比,生命活动是最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它是无法简单地、完全地归结于物理学的普遍定律的;当然,不同的运动形式理应遵循不同的规律。然而,考察生命现象,特别是从分子和亚分子水平上探究生命本质,又往往将物理学的概念、原理、方法、手段加以应用;薛定谔所论述的“非周期晶体”、“负熵”等等,便是物理学基本概念之合乎逻辑的创造性援用和引申。
薛氏以经典统计物理作比照:大量无机分子系统的热运动是无序的,宏观上却呈现经典统计意义上的热力学有序规律,即有序来自无序。但是,生命这种宏观现象与此不同,乃基于有机分子以及分子内原子的有序排列,即有序来自有序。染色体纤丝里的生物大分子,亦即薛氏所谓的非周期晶体,是人们“所知道的最高级的有序的原子集合体”;它“大大地摆脱了热运动的无序”,还比属于无机物质的周期性晶体的有序程度和繁复程度高得多,从而呈现出甚为玄妙、复杂的生命现象。“有序来自无序”以及“有序来自有序”有天壤之别,表明生物大分子系统并不满足经典统计规律。看来,熵和负熵,乃至熵原理,还只是描述性的;虽然说明了生命存在的条件及其生长发育过程中有序度的变化,但并未披露“有序”的微观面貌。而分子生物学五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展示了生命物质在分子层次上具体的有序机制。此外,热力学在生物学领域应用,形成所谓生物热力学;其中,试图以生命物质系统的“自组织”解释生长、发育过程里的熵减、并说明生物分子的有序结构。所以,薛定谔关于生物有序的精辟论断对于这些研究,应当说不无指导意义。
现代生物工程的主体便是基因工程;基因探索成为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主流。就分子生物学而言,以基因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分子遗传学乃是其主杆。理论物理学崇尚简单、统一;薛定谔在讨论生命本质问题时,依然采用这样的思维方式。前述非周期晶体——生物大分子内原子的有序排列,对应于一定的遗传密码以至负载一定的遗传信息;按此观念分析基因,其思路简约而清晰。
现代生物学家通过描绘种种生物的基因组图谱、确定它们的遗传密码,意外地发现这种种生物,无论是最高等的人、还是低等生物(例如噬菌体等),竟有通用的遗传密码和差异甚小的基因组;于是认识到物理学家追求统一的方式在生命科学研究中同样有效,又体会到薛氏利用物理学概念对基因和遗传密码所作的简单化说明,或许倒可作为现代分子遗传学的先导性思想。薛氏断言:“对于基因及其不变性,除了遗传物质的分子解释外,不再有别的解释”;生命科学的深层次研究正在循着这条路径发展,以求得日趋统一的分子解释。
薛定谔还指出:这分子解释表明“生命物质在服从迄今为止已确立的`物理学定律'的同时,”“可能还涉及至今还不了解的`物理学的其他定律',这些定律一旦被揭示出来,将跟以前的定律一样,成为这门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五十年过去,看来分子生物学研究和现代遗传工程构建,尚未揭示出新的物理学定律,然而这并非就能肯定今后将永远如此。
在非生命物质世界里,从19世纪起,分子物理学以及分子化学、原子和亚原子物理学,经过几十年发展,积累起大量的研究成果,从而揭露了量子现象的本性,量子论和量子力学得以建立,物理学便出现根本性的突破(或曰革命),即从经典物理转变为量子物理。而对于复杂的生命运动,恐怕须经过更长期的研究和积累过程,生物分子的结构和属性、生物有序和自组织现象的起因,还需进一步探讨。薛氏预言,可能揭示出的新物理学定律不是别的,“只不过是量子论原理的再次重复”。他把染色体看作“沿着上帝的量子力学路线完成的最精美的杰作”,假设“突变实际上是由于基因分子中的量子跃迁所引起的”(或者说乃由分子内若干原子的位置之不连续变化所致)。
按照他的预见,分子生物学可能向量子生物学转变。要追究生命系统的生物功能和生命运动之复杂性的起源,必须探索生物分子之间以及分子内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对此相互作用的定量探讨,便有赖于量子力学及其非线性的拓展形式。在讨论有机体内微观甚小尺度上的量子效应时,有可能揭示出与原有量子力学体系不尽相同的原理和定律。从长远看,生命科学的深层次研究必然导致物理学产生新的突破;伴随着分子生物学向量子生物学的转变,量子物理学也会出现新的转变。简言之,生命之本质的日趋显露,一定是生物学革命的主要成果;而生物学革命若能深入展开,会促使物理学发生又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比量子物理学之建树更为深刻。
现代生物工程,尤其是现代遗传工程,与人类的生活、健康,与现代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甚于其他科技领域之研究工程更为直接的关系。生物之遗传密码的破译、基因组的测序和解读,特别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实施,乃是遗传工程的重要成就。
尔今业已进入所谓的后基因组时代,对基因组研究的重心则从其结构转向整体水平上的功能,从而试图从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属性导致有机体整体活动的层面上认识生命想象的本质和规律。不管是深层次结构和内部相互作用,还是整体水平的功能和生命运动的进程,都离不了对物理学、化学之概念、原理以及研究方法、实验手段的应用。诚然,二者相比,前者更偏倚于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后者更显现生命运动规律的特殊性;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后者比前者更为复杂。况且,研究重心的转移恐怕是反复的,二者的研究相互关联、相互交替、相互促进;恐怕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
总之,要真正解开生命的奥秘,当然要依靠生物学本身的新的转变,但也需要生物学借以基础的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愈益深入的新进展,以及借以为研究工具的高新技术(如计算技术、信息技术等等)“更上一层楼”,如此方能促成生命科学的伟大革命。因此,从薛定谔关于生物学未来发展可能揭示物理学新定律的预言而论,他的目光是十分犀利而远大的。
兼议还原论和活力论
在科学哲学发展史上,曾批判过关于生物学研究的还原论和活力论。被批判过的还原论是指试图将生命运动形式还原成物理—化学运动形式,用物理—化学运动规律取代生命运动规律的一种学说;活力论是指主张由特殊的非物质因素支配生物体活动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对这两种学说是否应予批判?诚然,批判得不无道理,因为它们二者至少是过于偏颇了。
玻尔在提出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时就将其推广用于讨论生命现象亦所未免的不确定性。他指出,在生命研究中也存在两难局面:要探究生物体的生命本质,须将生物体分解成各个组分的化学系统;但既然分解了,生物体就不能活、不成其为生命系统了。这里便涉及对生命研究的两个层面:从微观上研究生物分子的结构和内部相互作用、乃至自组织形态等;从宏观上研究生物体整体的功能、活动规律以及与环境的关系等。前者着重于分解、还原,考察生物分子运动的物理—化学机制;后者致力于描绘生命系统的活性,抑或生机、活力。
所谓活力,例如表现为生物体所具有的一种接收、处理和主动利用信息进行目的性调控的能力。虽然,生物体分解后就不活了,但无碍于前一种研究,而且可以从分子和亚分子水平上寻觅生命运动的起因;但单有前一种研究,便会陷于纯粹的还原论方式。生命运动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生物体具有活力;从此意义而论,活力是生命物质的特殊功能,它不是一种纯非物质因素,故而活力论不能谓之唯心主义。就如研究生物体的目的性调控能力,当然要在它们活着的时候;这时采用所谓活力论的思维方式殊为必需。因此,对于玻尔所说的两难局面,能以兼顾还原论方式和活力论方式予以解决,二者都不可偏废,而应相互补充。
李政道曾提及,21世纪物理学会采用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式,特别是针对复杂性课题;而物质系统的复杂性已逐渐成为物理学的研究重点。他的这一见解,可能更适合于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因为生物体是复杂性最突出、最集中的物质系统;若凭借宏观与微观相兼顾、相结合的研究方式,会更利于对生物学革命的孕育和促成。当今“系统生物学”兴起,或许就可看作是这种趋势所使然。如果以互补原理的涵义分析还原论和活力论,二者都没有本质上的谬误;但如果强调其一而忽视另一,则就失之偏颇了。
薛定谔在《生命》中既阐明生命运动以物理学定律为基础,又指出不能单纯归结于物理学普遍定律,则说明他所持之观念既为还原论、又非单纯的还原论。薛氏客观地声明,他是在对不太通晓的论题发表见解;尽管关于遗传学的某些具体论述不甚符合后来的实际情况,但上述的那些预见尚可称得上是现代生物工程和现代生命科学研究的先导性思想原则。所以六十年后,在纪念DNA双螺旋结构问世五十周年的日子里重读《生命》这本著作,依然觉得它含义深邃、甚至不乏现实意义。笔者不谙生命科学,故而本文只不过是阅读该书的心得体会罢了。
_________________
* 关于此结构的知识,请参阅本刊2003年第4期上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