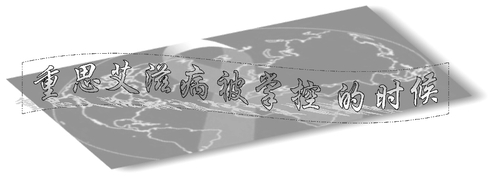新的统计数据表明,专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先生曾经对美国艾滋病前景所作的预见现在可能适用于全球的艾滋病感染:终有一天,艾滋病可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它只捕食人群中那些粗心或弱小的成员,就如同肺炎总是进攻年老体衰的人一样———
2007年11月19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公布了最新的艾滋病年度报告,承认全球感染艾滋病病毒(HIV,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人数被高估了600万。根据新的统计方法,2007年全世界感染HIV人数为3320万(原估计数据为3950万),其中包括250万名儿童。虽然高估来源于取样错误,是一个流行病学家的“Dewey defeats Truman(杜威打败杜鲁门)”事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审视这些年来HIV感染人数数据的修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那就是艾滋病已经过了它的高峰期。
HIV感染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了一个高峰———根据最完善的估计,这一时间是在1998年。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时刻———大约在公元543年,君士坦丁堡终于摆脱了查士丁尼大瘟疫的死亡控制;而中世纪的欧洲在1351年也在“黑死病”的淫威中看到了转机,生存的希望如曙光破晓。
11年前,在艾滋病历史上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当瘟疫结束的时候”的文章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当时发明的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即三药合用的鸡尾酒疗法意味着艾滋病最终可能成为一种慢性疾病,而不是不可避免的死亡。然而,沙利文却遭到艾滋病机构的痛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口诛笔伐中幸存”。预料中的结束则意味着警戒的放松———虽然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意思。
沙利文先生的观点是唯我论的———只庆贺那些以性自由为乐趣的美国男同性恋者生命的延续,却几乎没有提到一个更普遍的事实。那就是在非洲,大量新生的婴儿和忠诚的妻子从来没有享受到任何自由却注定悲惨地死去,人数之众如一股旋风,足以刮飞北美所有男同性恋酒吧的出口大门。
现在,拨开这些旧数据的迷雾,另一个这样的时刻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出现。但专家对此要说的第一句话仍然是,这并不意味着任何人可以放松。
在1998年每年有超过300万的人新感染HIV-1病毒,或者2007年大约有250万新增HIV感染者,“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高兴的‘高原’阶段,”HIV的发现者罗伯特·伽洛(Robert Gallo)博士说。
作为布什政府的全球艾滋病协调员马克·杜伯(Mark R.Dy-bul)博士补充道:“我不认为这会完全改变我们的想法,至少在5~10年以内。我们仍然需要每年防治250万人感染艾滋病,仍然需要每年阻止210万人死于艾滋病。”
然而不管怎样,艾滋病最终给我们的启示是,它的演变将遵循其他瘟疫同样的规律。不同的是,艾滋病的发展比所有借助喷嚏或咳嗽或老鼠或蚊子传播的传染病都要缓慢得多;它可以让感染者毫无症状地生活好几年,然后再像一个施刑者漫不经心地夺去患者的生命。
一般来说,所有的传染病总是首先侵袭那些身处感染前沿的人群:如1347年从克法(黑海港口城市)围攻中逃跑出来的热那瓦商人就把瘟疫带到了欧洲;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在新大陆发现了梅毒。如果禽流感开始大流行,一定是在家禽农场主和幼儿园老师中间出现,因为他们都接触大量的微生物媒介物。在美国男同性恋者中间,最先感染艾滋病的也是空中乘务先生和租赁男孩。
然后,传染病在条件适宜的地带蓬勃生长,如满是老鼠的港口、经历了饥荒的虚弱人群、洪水泛滥的孟加拉国街道以及泰国妓院等。最后,不可避免地是传染病开始大爆发:宿主迅速死亡,而新宿主尚未被发现;最为关键的是,新宿主开始变得更聪明,迅速逃离原来的城市,排干沼泽地,发明疫苗,或者接受自我约束和避孕套。
HIV一直在对抗这种变化规律,直到现在,它的势力范围似乎一直在扩大———中非比美洲糟糕,南非又比中非糟糕,印度似乎形势更恶劣,而中国次之。但现在看来,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处于控制之中好几年了。
在2000年的时候,唐纳德·G·迈克尼尔(Donald G.McNeil)曾写过一篇文章,试图计算如果控制全球的艾滋病感染需要花费多少钱,据说在贫穷国家有3000万人被感染艾滋病(去年11月修正显示,该数据下降到2300万)。
2007年9月, 艾滋病(AIDS)疫苗研究遭受了灾难性打击, 一个最有希望的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宣布失败。图为美国默克公司艾滋病疫苗临床试验的海报。 默克公司花了10年时间研制这种名为V520的艾滋病疫苗 , 人们曾对它抱有很高期望
毫无疑问,那2300万艾滋病感染者实际上都已经死了。就是现在,大部分HIV感染者也没有得到救助———只有十分之一的感染者得到救助。
直到现在,我们知道那些沦陷区都是处于感染流行的尖端。虽然在那时,情况改善很缓慢,但是这么多人死于艾滋病的事实却使许多非洲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目前仍然不清楚为什么南非是HIV传染的重灾区,可能是频繁流动的采矿工人、极少施行包皮环割术,也许还有基因的易感性等。然而,南非的艾滋病大爆发并没有在人口众多的亚洲重演,只是在易感地带流行,如印度的加尔各答红灯区,而且似乎就停留在此。
UNAIDS负责监测和制定政策的保尔·德雷(Paul De Lay)博士说:“在上世纪90年代我们认为,如果有迹象显示一个国家有高危性行为的蔓延,像妓院和拒用安全套,那么这个国家的艾滋病将进入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的大流行阶段。但现在,这个观点不再正确。我们再不会说中国可能具有非洲模式的流行趋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HIV感染人数减少是必然的。艾滋病仍然在新的集中地带生根,感染人数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还在增加。德雷强调,艾滋病还能诱使其宿主再去做愚蠢的事,这已经在旧金山和德国发生过:当年轻的男同性恋重温20世纪80年代酒吧风景的时候,新的感染又开始增加。况且变异的病毒非常容易传递的基因特征或者多重抗药性的出现,很可能激发新一轮的流行。
无论如何,新的统计数据表明,沙利文先生曾经对美国艾滋病前景所作的预见现在可能适用于全球的艾滋病感染:终有一天,艾滋病可被视为一种慢性疾病,它只捕食人群中那些粗心或弱小的成员,就如同肺炎总是进攻年老体衰的人一样。
毕竟,黑死病也不再致命并已被控制住,每年大约有2000病例,而且青霉素就可以灭杀它。尽管目前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可以杀灭艾滋病病毒,当那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流行病的历史将会被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