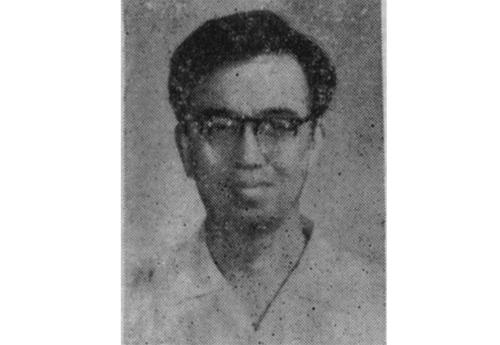今年四月下旬,我和同事朱泽民专程到北京,采访几位科学家,其中一位便是赵红州教授。与其说采访赵先生是我们此次之行的任务之一,不如说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一件乐事。对我国的科学学研究稍加关注的人士可能都会注意到他的名字。赵先生现在是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所所长、研究员。早在1983 ~ 84年,我就在上海听过赵先生讲课,那时他刚四十岁出头,他在讲课和私下交谈中显算出的过人才智、对事物的深刻洞察力、极强的概括能力以及相当准确并不时带有幽默感的表达能力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后,我和许多关注他的朋友一起经常在报刊上、出版社的出书栏目看到他的作品,了解他的工作,此番有机会直接向赵老师请教,倾听他的见解,能不令我们振奋?
采访在赵先生的寓所进行。坐定后我们得知,赵先生这两天正患病在家。我们首先感谢赵老师抱病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决定将采访提纲缩减,重在请赵先生谈下一步的工作。“我非常乐于谈我下一步的工作打算,我有一个十年的梦。以前的事过去就算了,现在还不到评价的时候,做的也只是逻辑上的言之成理,至于能不能经受实践检验还得经受时间的考验。也许我要给您们谈的这个梦根本做不到头,也许这个梦根本是错误的,这是我最近的学术兴奋点。”赵老师的话音的正宗京味再加上他特有的中音音频,令我们这些上海来客顿觉听觉感官的享受。“这一梦起源于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这样一个问题,马克思说过,社会是特殊的自然界,自然界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把这一原理用于科学学上,我认为科学确确实实只有两个载体,一个是非生命载体,如报刊、磁带等;另一个是生命载体,如细胞。人的创造能力常常是这两种载体分合的过程,每一次分合都有新的闪光点。在我看来,创造性的过程就如同三极管模式,是分 - 合、分 - 合的过程。由此就引出这样一个题目:‘关于知识的波谱结构’,或称‘知识结晶学’。如果上述猜测是对的,那我就有一个推论,即知识在大脑 - 生命载体上的分布和在非生命载体的分布方面有同构性。所谓创造过程就是它们通过非常复杂过程进行同态同构,进行多种复杂作用后产生的新知识。如何证明这两种知识载体的同构性很不容易,即要找出这两个领域的共同物质。”说到这里,赵教授停顿了一下,看得出,他是让我们的记录速度能跟上他的讲话速度。“你们可能知道基尔番夫的故事吧?100多年前,基尔霍夫试图用波谱确定元素的值,经过几年极其枯燥的分析工作,他完全利用波谱分析的方法确定任一单质元素都有特定谱线,从而也证明了太阳上的物质和地球物质的同构性,这一工作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最高奖,有一天,基尔霍夫拿着金灿灿的奖章,跑到当年曾笑话他的房东屋里说:‘看呀,我果然从太阳里取到了金子。’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很大,我总感到,人脑假如是一个小太阳的话,很可能其知识的同构同书刊、磁带等有同构性。这就是上述题目的由来。如果这一题目能做通,其意义很大,第一,今后在知识的分类上就不是如现在图书馆里的那种分类法,你认为科学学是自然科学,他则认为是社会科学,争论不休。对今后任何一种特定的知识可以像特定元素那样用谱线分析,通过计算机仿其可以做到这一点。反过来,经过综合训练,先天遗传下来的人脑结构作为活载体负载一定的知识后,通过一定的手段也可以取样,来发现人的大脑特别适于某种知识。如能达到这一步,则第二点,将来对于人的专业方向和科学家战略的专业方向判断是极其有价值的。”我注意到,赵教授在讲这番话时,伴有极大的自信心。措词严谨的他用了一些肯定用语。“我们大家都可能有类似的经历,如某一个学生选择高校专业,向您请教。你往往是根据该学生的记忆、推理判断能力等条件作出咨询。这样,你实际上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用同构原理或生物、数学方法给孩子作咨询,即从孩子大脑中选取某种样品,经过你自己的经验,再根据你了解的在非生命载体上的专业的情况,进行分析比较,然后得出意见。我的想法是试图将这种经验(也许是含有一定其理成分的想法)科学化,如果这两种载体的确是自然界的产物,或社会是自然界的产物,那么这种地球上最高级的思维火花与低级运动形式之间一定有某种相互作用——同构同态属性的同构性。找出载体之间的关系就要看各种参数的关系,用以描述同态性和同构性。我的想法基本上从波谱分析入手,从小太阳想到知识之间的同态结构,这一想法类似于基尔霍夫的工作”。望着正娓娓道出其“十年之梦”的赵先生,此刻的我突然想起当年恩格斯称颂马克思的一段话;他的头脑(思想)像一艘时刻准备升火待发的舰船,随时准备驶向任何思想彼岸。赵先生确有那种素质,坚实的知识根基、加之敏锐的科学眼光使他能和一批杰出科学家拥有那种不断开拓科学探索领域的本领、能力。这可能也是人们称之为“科学家”的那些人的共同素质吧。赵先生此刻向我们介绍的对知识结构的波谱分析终将作为一个严肃课题登上科学殿堂。很高兴,我们已经得知,周光召任主编的上海的《科学》杂志,作为一份严肃的科学杂志在去年10月号登出了赵教授及其同事的这一梦。赵先生的想法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知识结晶学是我左科学学领域打的第一钻,初步结果使我很兴奋,因此我现在很乐于同你们讨论这一题目。现在,我有勇气将此作为一个严肃课题带几个学生一起来做”。稍稍歇息后,我们的采访继续进行。“我们先从化合物着手,先从知识化合物着手。已故的普赖斯教授发现了知识的指数增长规律,即人类得到的重大科学成果在历史上的分布呈现指数增长规律。这一规律是一个统计规律,在指数曲线上下跳动,在一定的相关系数内成立。人们一旦在认识到指数规律后,往往将原先的在背后产生知识规律的东西——指数波动忘掉了。而我觉得这被人遗忘的矿渣里面很可能保留很宝贵的东西。要提取这种东西很像当年居里夫人从沥青中提取镭。现在如果把指数规律那部分的内容刨掉,剩下的东西看似噪声背景。目前对此有两种猜测,一种认为这完全是白噪声,毫无提取知识的可能,无任何有意义的信息;另一种认为,这里面肯定有某种颜色、东西或某种波可能在其中起作用。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开始了大批量的数据处理工作、由于计算量太大,我先整整用了四年,接着由我的学生郑文艺做。他用了四个月零19天,在计算机上日夜不停地做,扫出了22940多条曲线,历史跨度为474年,一年扫一遍,一条曲线就是一个波,一个跨度窗就是一个波。起初用简单的跨度来做容易跨在盲区上,导致信息遗漏,后来我们做了改进,改用统计的傅立叶分析法。经分析后,再考虑到应该出现倍频数而未出现的概率,(如64的倍频数32就可能埋到噪声堆中去)。我们作各不同跨度的基频扫描,在期望出现的地方出现的概率提出一个权重,将2万多条曲线一一处理掉,结果提示上述第二种猜测可能是对的。从曲线图上看,一条曲线差不多有1700多个数据,分成11年一群、16年一群,32年一群、64年一群。这些是利用普赖斯当年很严肃的工作数据来做的,但我们恐其中有误(因为科学史上、数据的选取有很大的随意性),后特再用上海几十位科学家在文革中所进行的一项工作的数据(即《自然科学大事年表》,我始终认为,这一工作是上海的科学家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科学史研究的独特贡献)。数据处理的结果惊人地发现了两者的相似性,而这两种数据是完全独立的,两者的同一性有惊人的相似,64、32周期埋没不掉。在人们常常忽略的地方发现、找到了东西,我们的心情之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别人即使再说风凉话,我们心中也有底了。指数规律是普赖斯发现的,我们的工作是发展、推进了普赖斯当年的工作。我们通过仔细扫描发现,如果降低相关系数,统一指数的描述是可能的。在仔细扫描的基础上,我们发现,1670 ~ 1740年间有一个破坏指数规律时期,这一结论已为世界承认。按知识结晶分析(或波谱结构分析)的观点,这一时期人的知识好像不再按知识积累的方向走,其知识的结构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我们所谓的知识结晶过程。假定知识是一个游离态的知识,相互碰撞、组合可以导出一个指数。如果不是这一模式,而是某种结晶模式(如盐),那就会发现这一模式立刻会产生饱和的非指数模式,这就是知识结晶学的基本推测。即按照波谱分析,在非常时期,知识呈非指数性增长,是一结晶过程。结晶过程的自由能较低,不如游离态过程。从化合物的各种知识中(数理化、天地生诸学科),把五种硬科学的各种知识从白噪声中分析,发现知识不以国籍、个人选择的年表等为转移,而有一个确定的波谱群;其二,这一波谱群在历史的不同时期是不同的:在非常时期,其能量下降,检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乘录音机换磁带的机会,赵先生建议休息几分钟。赵先生为我们放了一盘克里德曼演奏的现代钢琴曲《命运》磁带,然后自己到阳台上去活动活动。听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激昂奋进的乐曲,我想起了有关赵先生的一些经历:赵先生是南开大学60年代初的理论物理专业毕业生,曾先后在中科院物理所、高能所从事研究工作。他一直在很困难的条件下从事科学计量学研究。他在十年前就预测到,凝聚态物理学将有突破性进展。这一点已被前两年高临界低温超导研究的重大突破证实。今年第1期的《科技导报》上刊出了他就我国凝聚态物理发展的一些看法致周光召院长的公开依。他的专著《科学能力引论》1984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科学界著名的“三钱”——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科学家都对该书有积极的评价。美国1988年出版的《世界人录》称赵先生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在我所接触到的一些从事软科学研究的人士都很熟悉、关注赵先生的工作。
称赵先生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位始终坚持软科学基础研究并不断有新的创见的学者。此刻,我们坐在赵老师的书房里,有幸直接听赵先生讲他最近的学术兴奋点,对上述评价,我们深感这是对赵先生工作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采访继续在进行中,话题依旧是知识波谱结构。“这个梦想的第一钻打下去后,发觉这一领域有油,当然是贫矿富矿尚不知道。由此增强了我们的两个信心,第一,可以提炼化合物中的单质,可以把物理学、化学中的知识单元分开来做。这方面的实践中,又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既然科学现象可以作波谱结构分析,那么文学、经济学有无这种结构?进而再有战争等,即人类的一切文化活动有无类似于科学的结构?这一钻打下去使我觉得两个方向都可能有东西。最近我们已经做了历史现象的波谱结构分析,果然发现有类似情况。当然与科学现象相比,其周期长短不同,但波谱群结构同构。目前,我们正在做战争,把有史以来的战争事例作扫描分析。这些工作的目的是试图将对人类的文化结构的研究引出一个严肃的方向。以前的文化研究偏重于意识形态、政治学方面,而忽略了文化的自然本质研究。而如从文化的自然本质分析研究着手,来揭示文化自身的结构,可能有助于了解各个民族的文化之能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其特殊存在的理由。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还正在做。目前还没有结论性的意见。对历史学、战争的波谱结构的成功分析使我和我的同事们都很兴奋,认为在软科学中确有东西可做。下一步最难的是从微观方向做”。赵教授的兴致很高,这是种经过艰辛耕耘后终有收获后的喜悦心情,我们真想说几句祝贺的话,但不便打断赵先生的思路。“另外一个工作是,我和唐敬年等从自己最熟悉的专业领域下手,做物理学知识单元的波谱分析,因为物理学是最成熟的学科,它的公式、量纲、测量数据的精度都已为其他学科所公认,其成果会影响其他学科,并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这方面具体的工作见刊于《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杂志今年1 ~ 3月号上。文章主要讨论知识单元的静荷值的确定。”赵教授在不紧不慢的言谈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我们即请赵先生解释一下何谓“静荷值”。“所谓静荷值是指某一定理的组成部分、相关单元,如牛顿定理中,力、质量、加速度是三个单元。单元是一个能用数学严格表示的科学概念。譬如‘力’在墨子时代的概念与今天就大不相同了。‘力’在开始有了大小、方向、着力点后才从概念上升为单元。这些单元作为知识一定有自己的权重。按照科学惯例,荷值确定一般有两类:一是逻辑构成,一是历史构成。所谓逻辑构成是指某一单元包含的其他单元或隐参数的关系越复杂,其逻辑构成也越复杂。为了表示这一关系,我们找到物理学的量纲作为最基本的尺度。一个量所包含的量纲的多寡很可能是确定其逻辑复杂性的标志。如‘力’包含时间、长度、质量三个单元,有两个长度、两个时间、一个质量共5个量纲。把所有单元都化在这一单元上,再用它来比,如此来确定静荷值。现在我们基本上把物理学上四大力学中的91个重要公式(包括机械力学、热力学、电磁力学,量子力学另当别论)的静荷值确定下来了。确定后发现里面又有东西,把静荷值在三个轴上投影(即在知识空间上投影),可以发现它的分布是一个很有趣的线性,这一线性也是沿着圆周振动的。这一振动又为我们进行波谱分析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由于这些物理参数是大家公认的,具有很大的权威性。这一工作为我们下一步确立单质的波谱分析提供了物质基础。其中唯一的不确定性或者说现在的困难在于,物理学家对于一些基本定理的发明年代各执一词,这是因为一个公式的提出往往是在某一篇文章中。尽管有不确定性,但这种方法毕竟比泛泛而谈科学分类重要。严格地讲,不再以形态分类,其意义可能远远超出现在的估计,对今后国家计量标准的严密化都有意义,至少对于科学家研究方向的选择;教育专业的选择、确定两方面是有价值的。”说着,赵教授从桌上拿起一份手稿,他让我们边看,边给我们解释道:“现在我们尚未发表的一篇文章涉及数学中的单元。数学中的单元相当于粒子物理学中的胶子。你们知道,一个正确思路往往是以错误思路为背景的。这一概念就是熵的概念,即猜中某一正确思路的概率。确定知识熵时,肯定还要做大量计算工作,我们现在正在做知识熵。熵做出后同样发现有熵谱结构。知识的核谱结构、熵谱结构、知识的数量结构。这些结构我相信它们彼此之间可能有严格的关系,这种关系如确定下来可能有重要的意义。我估计2 ~ 3年内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的工作是活载体方面的,我们试图跟踪孩子的智力发展,孩子的考试也是一种成绩。随着分数的波动,记录孩子一周一周的考试成绩。根据波谱分析,人脑可能有几种类型:有的是长波型,有的是短波形。确定某一类大脑波形和哪一种知识的相关性最大,可以确定某一学生是文科或理科人才。目前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数据积累。这部分工作和人工智能有关。人工智能专家是从认知科学和脑科学角度,研究生命载体上的东西。他们的成果我们要借鉴、继承。我们上述的工作可以归结为是做社会大脑,也可称为“社会大脑脑科学”,下一步我们还想做社会脑。”采访至此,已大大超出原定的时间,我们立意向赵老师告辞,并再次感谢他抱病接受我们的采访。
回上海后,我在整理这篇采访稿时,一再想起赵老师给我们讲的基尔霍夫从太阳里得到金子的故事,我想,赵老师和他的同事们正在从事的研究工作也是在获取着某种“黄金”。不过,这是一种比自然界中金元素更有价值的“知识黄金”。赵老师称自己的工作是一种“梦”,是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是经常在做着某种“梦”的,然而更可幸的是,赵教授的这一“梦”已经或正将被更多的事实所证实。我们衷心预祝赵教授及其同事伟业早成。
(本刊记者江世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