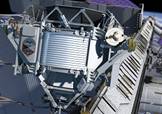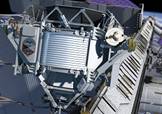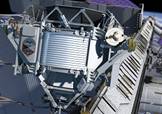
2011年5月15日,美国“奋进”号航天飞机运载着重达7吨的宇宙射线探测器――阿尔法磁谱仪2号(AMS―02),飞抵国际空间站。这是“奋进”号的“绝唱之旅”,也是放在国际空间站上惟一的大型科学实验装置。8月中旬,领导AMS项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特邀请本文作者前往AMS项目的研究基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采访。丁肇中高兴地阅读了刊登介绍AMS文章的《世界科学》杂志,并向作者详细介绍这一科研项目启动17年来的艰难历程和探索的重大意义。
●历时17年,由丁肇中领衔组织的有16个国家、地区60所大学、研究所共6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参加的国际团队,成功地把重达七吨的AMS-02探测器送抵国际空间站,迈出了探索未知宇宙的第一步。
天空飘来两朵新的乌云

在位于欧洲核子中心的AMS实验楼里,丁肇中教授向本文作者介绍AMS-02在国际空间站的工作状况
摄影/黄 蔼
当20世纪的钟声刚敲响时,英国的一位著名物理学家开尔文爵士(即威廉·汤姆逊)在他发表的《新年献词》中说:物理学大厦已经落成,所剩的只是一些修饰工作;但晴朗的天空仍有两朵乌云,第一朵即迈克耳逊-莫雷实验结果与当时的以太漂移说相矛盾;第二朵乌云是发现黑体辐射的能量不是连续的,导致了所谓的“紫外灾难”。开尔文没有料到的是,正是这两朵“乌云”迎来了物理学天空的一场暴风雨,倾覆了整个经典物理学大厦。待到雨过天晴,云蒸霞蔚,迎来的是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组成的两幅灿烂的新图景。
100多年来,物理学的发展又奠造了一座更为雄伟壮观的大厦。随着高能加速器和天体观测手段的不断进步,我们对微观的物质结构和宇观的天体物理的认识,再次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然而,新的发现让天空再次飘浮起新的“乌云”:尤其是宇宙是否存在着一个反物质的世界,以及暗物质、暗能量究竟是什么?
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宇宙开始的一瞬间,产生的物质与反物质应该是等量的。但是,为什么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世界,都是由正物质构成的,那些反物质到什么地方去了?现在的理论为了解释反物质的缺失,认为在宇宙诞生的最初一秒钟之内,反物质和正物质就彼此发生了湮灭,由于正物质略多于反物质,于是少量正物质幸存了下来,组成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按照这个假说,能够幸存下来的正物质应该非常少,而大部分在与反物质的湮灭反应中变成了光。那么,宇宙中光子与物质的比率,光子应该高出许多。但是天文观测的事实,证明这个比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可见反物质并没有完全湮灭。那么,这些反物质究竟到何处去了?
这个“宇宙之谜”吸引了许多科学家,其中一位就是曾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丁肇中。作为一位实验物理学家,丁肇中构思了一个大胆的实验:设计制造一台能放置到太空的粒子探测器,在地球大气层的上空,探测有否来自宇宙深处的反物质粒子。这就是国际合作的大科学项目――阿尔法磁谱仪(AMS)实验。
将高能物理实验中使用的粒子探测器搬上太空,丁肇中面临的是巨大的难题和挑战。首先,它们必须能在太空中经受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长期运行而不发生任何故障。其次,它们能否在升空时经受住火箭发射时的剧烈震动和加速的冲击。这些都对仪器的可靠性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其技术的先进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譬如,AMS-02上有650个微处理器、30万个电子感应元件,它们都要无故障地在太空工作10至20年。国际空间站每90分钟要经历一次昼夜变化,导致温度在零下40摄氏度和零上60摄氏度之间波动,但探测器的工作温度必须在热控制系统的保护下稳定在1摄氏度的变化范围内。丁肇中组织了一个国际团队,有16个国家、地区的60所大学、研究所共6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参加,历时17年,终于成功地把这台重七吨的探测器送抵了国际空间站,迈出了探索未知宇宙的第一步。
●物理学实验往往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新的发现可能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甚至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于AMS-02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现在很难预见……
宇宙是一座最大的加速器

志在物理学前沿领域探索的丁肇中教授,同时也很关心国内的科普传媒事业,图为他在书房内仔细阅读《世界科学》杂志 摄影/黄 蔼
自从望远镜发明以来,我们对宇宙的认识达到了当年哥白尼、伽利略无法想象的程度;但所有这些对宇宙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测量电磁波获得的(光子也是一种电磁波)。从伽利略自制的第一架天文望远镜,到今天的哈勃望远镜,都是测量光子的仪器。射电望远镜接收的也是电磁波。然而,来自宇宙的粒子中,除了光子等电磁波外,还有宇宙射线。宇宙线是各种天体演化过程的产物,特别是各种高能天体物理过程的产物,主要是高能的带电粒子。地球上每分每秒都有大量的宇宙射线进入,它们带来了丰富的宇宙信息,对这些宇宙射线的测量和分析,必将极大地扩充我们对宇宙的既有认识。然而,由于这些粒子在进入地球大气层后,被大气吸收或相互作用,从地面上测得的宇宙射线已不是“原生态”的宇宙粒子了,而是它们与大气作用后的次生粒子。要直接了解来自宇宙的带电粒子,必须到大气层外面的太空进行测量。
回顾科学史,宇宙射线的研究对粒子物理学做出过重大的贡献,第一个反物质――反电子就是1932年在宇宙射线中发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粒子的研究转移到了加速器。于是,加速器越造越大,CERN的大型加速器,周长已经做到27公里了。再要做更大的,没那么容易,而且要采用新的加速技术。美国原要建造周长81公里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最后也放弃了。所以,粒子物理学欲再向前发展,寻找到新的粒子,越来越困难。通过高速粒子的对撞,人类的视野已能深入到比原子核要小一万倍的范围,如果还要再提高对撞粒子的能量,已近极限;而宇宙射线的粒子能量远远高于加速器的粒子能量。加速器产生的粒子,最高能量是1012电子伏,即1万亿电子伏;而宇宙射线的粒子能量,最高可达到1020电子伏,比大型加速器产生的最高能量粒子高一亿倍。
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于宇宙这座能量更高的粒子加速器,是粒子物理研究的一种新途径。可见,人类创造的技术再多么高明,都比不上大自然高超。在宇宙深处,大自然已经创建了可以把亚原子粒子加速到CERN梦想不到的速度和能量,这又一次证明了大自然的伟大和睿智。AMS把探测器搬上太空,借助于“宇宙加速器”,获得地面上难以得到的新知识,是人类第一次有系统、有计划地测量来自宇宙的带电粒子,包括反物质和暗物质粒子。因此,AMS-02被称为“观测带电粒子的哈勃望远镜”和“太空版的CERN”。这是前所未有的探索,丁肇中勇敢地跨出了第一步,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锋,“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科学家认为,在未来的50年、100年,这很可能成为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学研究的主导方向。
丁肇中说,AMS-02收集到的宇宙射线数据,比原来预想的高了5倍,目前获得的宇宙射线数据,已超过了过去50年所收集到的宇宙射线数据的总和。但他不会轻易发表文章。他说:决不能提前发表文章,越是往后发表文章越好,做得对比发表早更为重要。一切都要做到最精确可靠。任何错误都会对国际上这一领域的长期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丁肇中向我透露,文章至少得一年以后才会发表。一方面是没有人和我们竞争,更重要的是一定要正确。严格地说,现在仪器还处于校准阶段,你要发表一篇文章,别人又不能检查,如果有误差,就可能对今后产生长远影响。所以一定要小心和谨慎。正确的数据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丁肇中对这项花费了20亿美元的研究充满信心。他说,无论是否发现反物质粒子,都会有很大的意义。至于AMS-02还会有什么新的发现,现在很难预见。物理学实验往往会“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而新的发现可能和原来想象的完全不同,甚至一点关系也没有。因为这是在科学的最前沿做探索,面对的都是新的、未知的东西,是预先不可能推测到的。
●17年的艰辛,才只是刚迈出了第一步。丁肇中曾把当年发现新夸克的实验,形象地比喻为在100亿颗雨滴中寻找一颗彩色雨滴。而今天寻找宇宙的反物质粒子,发现率或许更低于百亿分之一。
兴趣是科学家的原动力
没有亲身体验,理解不了科学研究的枯燥和辛劳。任何一项成果和发现,都是对意志和耐心的巨大考验。丁肇中曾把当年发现新夸克的实验,形象地比喻为在100亿颗雨滴中寻找一颗彩色雨滴。而今天寻找宇宙的反物质粒子,发现率或许更低于百亿分之一。17年的艰辛,才只是刚迈出了第一步。今后,他们将守望着浩瀚的宇空,10年、20年,在上千亿的雨滴中,寻觅那不同色彩的异常雨滴。这股能持久坚持的动力,来自什么?
“是兴趣。”丁肇中说。“兴趣是科学家从事基础研究的原动力。”
“您从事研究已几十年了,难道这股兴趣心就不会减退吗?”我问道。
“因为我不断地在做新的实验,因此就不断产生新的兴趣。”他的回答很简单。
“但每项实验,都要经历好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漫长过程,您是如何保持这一兴趣呢?”我又问。
“过程确实是艰辛的、枯燥的,但结果是令人兴奋的。”丁肇中说。
这使人不禁想起了爱因斯坦的话:“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的乐趣,是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曾说:“只有那些对发现抱有真正兴趣和热情的人才会成功。”
丁肇中回忆说:我开始学物理学,我母亲非常反对。因为当时学物理的人,不容易找到事情做。我父亲虽然没有发表意见,但从来往的信件中看出,他当时也并不赞成。我就对母亲说:我的兴趣和前途,是我的事情,让我自己决定吧。母亲说:既然你有如此看法,我就支持你吧。我母亲是从事教育的,父亲是学土木工程的。他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能理解我的想法,所以支持了我的兴趣和选择。
我说,AMS-01是一项有再次获诺贝尔奖希望的工作,丁肇中摇了摇头说:科学研究不能想为得奖而工作,尤其是老想拿诺贝尔奖,这是很可怕的。我问:您当年发现新的夸克粒子时,想到过会得奖吗?他说:根本没有想到。那天,我正在实验室,接到从瑞典打来的电话时,还以为是在开玩笑呐。后来,得知真的是获诺贝尔奖了。我还在想,肯定是评委们一时糊涂了。他笑了一下又说:物理学的发展太快了。一个人再有名,只能代表过去的贡献;你没有做出新的事情,很快就会被人忘掉。如果50年、100年后,人们还能记得我们这项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
确实,过去几百年人们对物理世界的了解,大多来自实验物理。正如丁肇中所说:实验是科学的基础。理论没有实验的证明,是没有意义的;实验可以推翻旧理论,创建新的理论。为此,他十分崇敬实验物理学的开拓者――伽利略。他说:当年,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就是第一例加速器实验;他又第一个用自制的望远镜观察天体,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开辟了天文学的新时代。
伽利略曾说:真理不在蒙满灰尘的权威著作中,而是在宇宙、自然界这部伟大的无字书中。今天,面对着浩瀚的宇宙,伽利略的后人们正在继续探索着自然的真理。他们传承了伽利略不畏权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他们是当代“伽利略”。
●丁肇中说: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神舟”系列的发射,但航天不能长期停留于为国争光,要与发展基础科学结合起来。
希望中国对基础科学有更大贡献
丁肇中希望中国能为基础科学研究有更大的贡献。他将基础科学与应用的关系比喻为一座金字塔,塔底部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依托于这个底部,不断向上延伸和生长。由于新的应用不断扩大,金字塔的高度在不断增高,底部则向微观和宏观这两个方向不断拓展。在微观层次,从原子、原子核到粒子、夸克,由此产生了半导体、激光、超导、核能、核医学等一系列的应用领域。而在大尺度的宏观层次,随着人类的视野由行星、恒星、银河系向更广阔的宇宙伸展,一系列过去无法预料的应用领域也随之而生,如气象卫星、通信卫星、精确定时、卫星导航等。AMS对宇宙射线的探测,在微观和宏观两个方向上都处于金字塔底部的最外沿。

在丁宅庭院的草坪上,丁肇中教授与本文作者夫妇合影
丁肇中说:我们常听到这样的争议,是支持无用的基础科学,还是将资源集中于技术的转化和应用研究?从历史的观点看,后一种观点是目光短浅的。如果没有对基础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投入,发展经济的实用主义途径,是不可能持久的。从发现一个科学新现象到这一科学成果的市场化,大约需要二十年至三十年时间。对政治家和企业家来说,这一时间显得过于漫长了。他们更愿意在自己的任期内看到科学研究带来的效益。但基础性研究常常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尤其当研究工作深入到未知领域时,科学家很难做出短期的预言和展望。你很难保证某一项研究一定会获得成功。实际上,在科学研究领域,错误常常是成功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对于基础研究,需要给予充分的自由空间和长期的展望。需要有一批痴情于科学的人,长年累月、坚持不渝、皓首穷经,才不断地有所突破和发现。
许多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在技术和经济方面具有竞争力,必须集中于能立即有市场效益的实用型技术的发展。然而,如果一个社会将自己局限于技术转化,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当基础研究不能发现新的知识和新的现象后,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了。为此,丁肇中说,他始终记着1977年8月邓小平对他说的话:对科技工作要想得远一些,看的宽一些。
丁肇中说:中国的航天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尤其是“神舟”系列的发射,但航天不能长期停留于为国争光,要与发展基础科学结合起来。当年,我1948年离开上海时,到处是难民,民不聊生;而今天中国已成为航天大国,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中国要开展这样的实验,技术上的困难会很多,AMS用的都是国际最先进的技术,但你不去做,就永远学不到。这次国际合作,大家也已看到了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中山大学的恒温系统,做得非常不错;山东大学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做散热系统,也做得非常不错。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实力大为提高,希望中国能对基础研究有更多的投入和支持。
责任编辑 则 鸣
――――――
题图为安装在国际空间站外部金属托架上的AMS-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