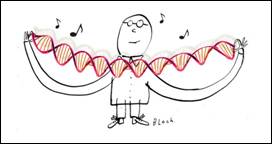
“自然之母”的眷顾
当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他和他的同事创造了世界上第一个“人造细胞”(亦称人造生命)时,他的表现就如同接受奥斯卡奖的演员那般,极有风度。
文特尔博士,著名生物学家和基因学家,他对他的研究团队大加赞赏,并介绍了他们成功背后多年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他还提到了出席这次招待会的一些对他事业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的人物,同时也感谢“自然之母”和“时间之父”对他的眷顾。
毕竟是大自然的造化和漫长岁月的进化才逐步完善了细胞,包括文特尔团队的“人造细胞”也得以问世。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生命能够超越细胞而存在。在生命之树上,古往今来的所有生命都无一例外地由细胞构成,每一个细胞都是生命的微观世界。无论是文特尔团队,还是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无中生有”地重新创建细胞,生物学家们仍然离不开细胞强大的“封装”力量。
5月20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利用培养皿中的化学物质,文特尔团队成功地创建了某个细菌的完整基因代码,并将创建出来的基因组完整地移植到另一个相近物种内。移植完成之后,合成DNA就像真正的DNA那样,反复地复制着新移植的合成DNA,而不是宿主原来的DNA。
如今,研究人员已经在冰箱里储存了这种微生物的后代。它们与自然方式培养的移植细菌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只有在仔细查看细胞的遗传序列时,才会发现研究人员打上的用以区别的“水印”――插入移植细菌100多万个DNA字母中的一段简短化学信息。插入的无害核酸包括加密版本的研究人员的姓名以及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和费曼等的三段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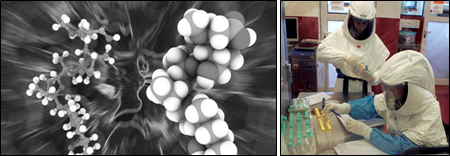
早在10多年前,文特尔团队就开始合成基因组的研究工作
它是人造生命吗?
“人造细胞”的诞生令其他研究人员大为惊叹。然而,丹麦南方大学的物理学教授斯蒂恩·拉斯穆森(Steen Rasmussen)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成就,但它是人造生命吗?当然还不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微生物学家邦尼·L·巴斯勒(Bonnie L. Bassler)说,这实际上是从已知的、大自然所赋予的一组基因组开始,并与活细胞中其他所有复杂成份一起创造出来的东西。
文特尔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的研究小组利用了35亿年生命进化的有利条件,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大自然逐渐地完善着构成所有地球生命的细胞体。虽然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之下,在合成除基因组之外的细胞的一些基本成份上取得了一些初步进展,但不要奢望在不久的未来能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大自然总是令我心生敬畏,”巴斯勒博士说,“大自然运作又是如此的完美。”
为何生命都是由细胞构建而成?为何大多数的细胞都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这并非没有原因。只有在很小的空间里,酶等重要成份才能挤压、聚集在一起,并及时地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细胞并不像水族馆里的游鱼,时不时地游来游去,”巴斯勒说,“它们紧紧地挤成一团,其中充斥着各种物质,就像堆满了各种杂乱而又不可缺少东西的屋子,或像摆满了各种食物的感恩节餐桌,你都找不到空隙再挤进一个盘子。”
多位生物学家观察到,细胞内部的大部分空间由细胞质占领,虽然其表面看似像一团无固定形态的糊状结构,但这只是一个欺骗性的外表。“细胞质有着美丽的结构,”巴斯勒说,“它们互相碰撞,但各就各位,细胞膜将它们结合在一起,不会互相分离。”
丝状支原体基因组
当文特尔团队将合成版的丝状支原体基因组植入山羊支原体细胞内时,前者充分利用了后者的细胞质――使用成千上万被称为核糖体的生物装置将氨基酸结合到一起――形成新的蛋白质。丝状支原体基因组依赖于复杂的分子组合,保持其DNA的正常工作秩序,并分裂复制DNA。细胞内的脂质细胞膜及其他一些物质,在其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进化到现代的细胞,其复杂程度十分惊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合成生物学这一年轻领域内,研究人员一次只能集中研究其中的一两个问题。去年,哈佛医学院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和他的同事曾报告说,他们创造了一个人造核糖体,以及美国波士顿大学生物力学研究中心主任詹姆斯·柯林斯(James J. Collins),现正研究一种可按意愿“开启”或“关闭”合成DNA的切换开关。
包括拉斯穆森现正在寻求设计能正常运作的最精简的细胞。在他看来,一个活细胞应拥有3种基本能力:首先,必须拥有自由吸收环境中能量的途径以满足其需要――某种形式的代谢功能;其次,必须有某种形式的“围栏”――细胞膜;再次,必须拥有获得复制自身的信息来源――基因组。
拉斯穆森和他的同事设计模拟了这样的细胞,多次成功实验了拥有其中两种功能的细胞,有一次甚至成功模拟了全部的三种功能。但设计能够自我复制和自主代谢原细胞的目标,目前还一直无法达到。他说,这就好像我们已经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乐器,但还无法组成一个管弦乐队一样。
资料来源 Economi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