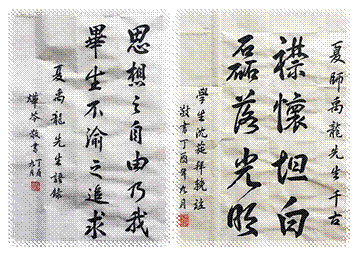
沈葹教授为悼念夏禹龙先生所书
噩耗传来,夏师禹龙先生离我们而去,不禁泫然伤感!在我的印象里,夏老师是一位擅长哲学思考,既热情开朗又谦虚平易的可敬长者。自与夏老师相识以来,我一直对他敬同师尊;从一开始我就称其为“夏老师”,这并非不经意的泛泛称呼,而是实实在在的师生之“师”的意思。
我自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上海科技出版社工作,1974年夏老师被调任到上海市出版局下属的所谓出版革命组的科技(分)组担任工科书的一般编辑工作。当时听人说,他原来在市委宣传部担任要职,来科技组当编辑似有被贬之意;但他的神情泰然自若,看不出有一点沮丧之态。他与科技组内众同事全都坦诚相处,对我这个从五七干校锻炼后返城、刚刚接触业务不久的小编辑(实为小学徒)也是一见如故、平等待之。科技组时而有一些须由编辑自己动笔的写作任务,夏老师和我往往被组领导委派承担,于是就共事得多了,彼此也了解得多了;我对夏老师的人品和学识肃然起敬,虽然专业不同,却对他如同对本专业老师一样的尊重。
夏老师后来较长时间担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主要领导职务,之前曾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当过哲学编辑室主任,又从1980年起在其参与创建的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兼任副所长。他是一位十分著名的社会科学学者,特别是对政治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颇有深入研究,除了撰写过许多有突出造诣的政治经济理论著作外,也作过一系列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科学哲学、软科学和科学学等方面的独到撰述;他可谓中国科学学和领导科学的重要开拓者之一。夏老师说过:“我的研究虽然也配合形势,但它是独立的学术研究。”的确,夏老师堪称真正的学者,毕生追求思想之自由、专心致志于中国政治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立研究。我跟先父曾经谈起夏老师,老人家说这样的秉性和研究风格对于从事政治理论工作而言,乃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我是搞理论物理的,所以本文着重就夏老师在科学哲学方面对我的指教,记述一些相关的点滴往事。或许出于父亲和恩师卢鹤绂先生的长期教导,也由于受了夏老师的影响,我在进行相对论以及量子理论等领域的专业研究和专业教学的同时,还注重理论物理的方法论探讨。当年在科技组时,夏老师曾主动与我讨论过爱因斯坦创建相对论时所联系到的哲学思想;他离开科技组后在其所做的一次以科学哲学为主题的报告中专门论述了相对论的前提假设和科学推论,从而使我感觉到这位哲学家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思考,他确实知识渊博、善于哲理思辨。与夏老师的交往促使我进一步精读了《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哲学名著。几年后《科学画报》编辑部约我写“相对论浅说”连载文章,夏老师告诫我一定要把相对论的基本思想及其科学哲学意义写清楚。他见我对科学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渐见起色,介绍我认识了李宝恒先生。李先生正在主编《自然辩证法通讯》,让我参与了少许涉及物理学的编辑工作。大概是20世纪80年代初,《通讯》编辑部凭倚国家科委在桂林召开了一次“粒子物理基本思想研讨会”,李先生让我也参加了会议,并要我写一篇报道文章,刊载在《通讯》上。我请教夏老师,他说:不要写成纯粹的会议报道;我受到启发,于是用夹叙夹议的形式,既报道了研讨会的概况,又比较详尽地论说了粒子物理的科学思想和研究方法。
夏老师是《世界科学》的主编,他出于对该杂志性质的考虑,并也诚恳地为了对我理论物理研究、教学工作有所助益起见,鼓励我为该杂志多写一些自然科学的进展、科学理论创造的哲学思想基础以及方法论探讨等题材的文章;夏老师的诚意敦促和编辑部江世亮、朱泽民等先生的大力支持,几十年来,我一直是《世界科学》的忠诚读者和认真撰稿人,所撰文章内容中占比例最高的就是夏老师所建议和敦促我涉足的科学哲学领域里所获得的认识和体会。因此,夏老师可谓我治学生涯的一位热心指路人,他的适当点拨使我终身受益。科学美学是科学哲学的升华,在探讨理论物理方法论的过程中,我因领略相对论和量子理论之美学意蕴而感到愉悦。这种醉心的快感融入撰述之中,故而在为《世界科学》撰写的理论物理之哲学讨论的系列文章里,都反映了浓重的撷美心理、集聚了分量不菲的论美言辞。这些文章经过修改和补充,结集为《美哉物理》一书出版;所幸者,夏老师欣然为其作序。他的点睛之笔,为拙著明显地添彩增色(纵然,我在书中所画之“龙”并不很像样)。我由衷感激夏老师一贯以来对我的提携和帮助。
就我所知,夏老师关于科学哲学研讨、即关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及其哲学讨论的主要观点,或可归结为三个方面:其一,我国“必须进行高水平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才能有效地赶上科技发达的先进国家”;搞好基础研究,尤其必须提倡创新。科研工作(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有价值创新,“不是依靠政府的指令,更非凭借功利主义刺激,而是源之于研究者强烈的科学兴趣以及对于创新应当持有的严谨态度”。(所以,夏老师对既富有创新精神,又严谨踏实地进行探索和研究的科学家,诸如丁肇中等,是倍加赞誉的。)其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需要结合以对其哲学涵义和科学方法论的探讨。具体言之,凡优秀的科学家,往往是高明的哲学家,牛顿、爱因斯坦便是典型的例子;前者的思想观念和研究方法带有机械论哲学色彩,故牛顿力学属于机械论科学范畴,而爱因斯坦从观念到方法都突破了机械论哲学的羁绊,才得以创建了更符合自然辩证法精髓的相对论。(夏老师与我关于牛顿和爱因斯坦的一次讨论,集中反映了他对科学哲学研讨之重大作用的深刻认识。)其三,要将科学哲学研讨进一步延拓为对自然科学理论之美学意蕴的精深探究。因为科学探索真理,即“科学追求真”,同时“对美的热烈向往大有助益于对真的追求”;实际上,在创建新的科学理论时,“对美的向往,既是提出理论假设的主要动力之一,又为形成理论假设的具体论述提供重要的灵感和启迪”。并且,“要倡导基础理论研究,就要在保证研究者得到适当的外部物质报酬之外,增添其内部的精神报酬;这内部的精神报酬就是指探究科学基础理论之美学意蕴所尝到的心灵愉悦”。所以,“许多有成就的基础理论研究者都重视内部的精神报酬,把美的向往与真的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
其实,上述这些观点虽然是针对科学哲学而论的,但在夏老师本人的主要研究领域,即其政治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中,也常常显示出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念的精湛理解和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精神。例如,夏老师与其诸同事提出通过技术的梯度转移以发展区域经济的理论,后经充实和完善,一般就称之为经济梯度发展理论。这个理论是强烈创新意识的结晶,在国内,尤其在经济学界引起较大反响,我堂兄是经济学家,对此颇有好评。夏老师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研究者,要求自己必须有创新见解;他在其不少研究项目里都有开创性贡献。他指出: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也应当、或者说更应当注重基础理论,即“不仅要重视自然科学的、科技的创新,更要注重制度创新;而只有理论自信,才能建立制度自信和远大理想”。这实在是一个十分精辟的论断,唯有追求思想自由、坚持独立研究的政治理论工作者,才能做出如此胆识过人的结论。
夏老师虽然成就卓著,然而待人总是非常谦逊。且举一两个我亲身经历中的事例说明之。1979年,夏老师与其他领导和学者筹建科学学研究所,他热情地推荐我进该所从事软科学研究。与此同时,有一位已调往国家科委的长者,却想荐我到北京工作;而本专业导师卢鹤绂先生等则认为我可调往高校的理论物理教研室。于是,我考虑后对夏老师说:卢先生要我“还是专业归队,去高校专修物理理论吧”;夏老师听了毫不介意、无些许不悦之色,并说:“卢先生考虑得很有道理,搞理论物理可能对你更合适。”他的谦虚态度以及替人着想的善意和大度,表现出为人的厚道,令我至今不忘。而在合作撰写文章时,对于署名之先后,夏老师亦一点都不在乎。例如由他主编的《科林小史》一书,其中有一篇是写麦克斯韦创建电磁场理论的,由夏老师和我合撰,按撰作比重理当我的署名在后,书出版前该文先在报刊上登载时,正是这样的署名次序;可是待到书出版,发现责任编辑误倒了署名次序,使我犹感不安,而夏老师对此毫不在意。由这件小事又觉察到他的豁达大度。
在科学学研究所里,夏老师等四位学者有“四君子”之称。我祗认识夏老师,他可真是有君子风度,襟怀坦白、磊落光明,为学界所推崇。本文中所载的两幅字乃十数日之前所写,聊表对夏老师的景仰和缅怀之情。
(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物理系教授)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