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丹·琼斯比对了三本揭示人类创造力之源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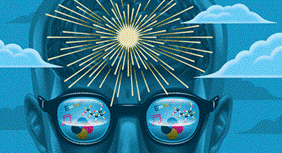
人类创造力之源在哪里
《创造力的起源》是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Wilson)的第30本书。在该书中,他指出人类作为一个特殊的物种,“对新奇事物有本能的热爱”。这一观点与《迅速崛起的物种:人类的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一书的观点一致。而这本书是由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和神经生物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联合撰写,作者通过某种软件探索大脑,以寻找人类发明创造的本源。与此同时,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Mario Livio)等在《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好奇?》一书中探讨了天才们的好奇心。
为什么只有人类有这样的创造潜力?在创造力产生的过程中大脑和思想会发生哪些改变?为什么有些人非常有创造力?实际上,《创造力的起源》这本书并没有从进化起源、认知神经科学和创造心理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展开叙述,而是用了更多的笔墨描述我们遗传和文化本质如何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以及这种体验是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创造力产出的形式和内容。本书充满轶闻趣事和个人回忆方面的内容。威尔逊考虑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并呼吁展开“第三次启蒙”运动,这样可以把前两次的经验与此后阶段人类积累的创造性方式融合在一起。
威尔逊认为,人文学科以探索人类状况为前提,需要与他推崇的五大学科结盟,包括人类学、进化生物学、神经生物学、古生物学和心理学。威尔逊表示,创造性的冲动并不是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出现在1万年前,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即现代人类诞生的时期。经过300万年的进化,智人的脑容量增加了3倍,促使其能产生更多的社交智慧和同理心,这又为符号语言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威尔逊将人文科学的起源追溯到“早期智人聚居在一起时,夜里聚集地亮起的星星点点的火光”,在这个时期,人类的祖先们聚集在一起谈天说地,分化出不同阶层并结成同盟。威尔逊坚持认为,由于缺乏对人类状况充分的因果解释,除非史前史得到更好地描述,人文学科将会继续在一个拟人化的“感官经验泡沫”之中前行。
威尔逊试图通过探索五大学科是如何丰富我们对文化的理解来寻求答案。显然威尔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影迷,他使用电影来说明文学和戏剧的原型其实就是反映人类进化过程以及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情感。所以我们会爱慕英雄,因为他扮演的角色需要克服重大挑战或战胜强大敌人,而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情绪就是“无休止的人类原始战争的本能产物”。同样,我们对“双重关系”原型的偏爱会使我们常常想起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1991年执导的《末路狂花》或者黑泽明1949年执导的《野良犬》,这些都源于我们对“利他主义和合作”的本能欣赏。威尔逊认为,进化塑造了许多文化审美的偏好,“无论是来自日本东京庙宇还是英格兰皇家庄园的园丁”都会选择长在非洲热带草原上的金合欢类似的树木,因为这种树木能够为食肉动物提供庇护,同时也是食肉动物用来观察草原万物的瞭望塔。
威尔逊的文章涉及一些“基因-文化”共同进化的内容,并且捍卫他有争议的群体选择观点。他坚信,“整体适应度”理论是有缺陷的,没有亲缘选择,也没有援引它来解释社会行为,当然也没有明确创造力的起源。
从书的名称来看,勃兰特和伊格曼的《迅速崛起的物种:人类的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一书也许反映了一些内容。对于迅速崛起的物种,这本书实现了完美描述和阐释,甚至用插图的方式进行说明。作者通过工程学、科学、产品设计、音乐和视觉艺术的实例引领读者探索创造力的来源,并把创造性思维落实到3个关键技能上:变形、重组和混搭。
“变形”通常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来表现某些元素。例如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将建筑的线条和平面弯曲形成波浪和曲线;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利用相对论解释了宇宙的时空弯曲。
“重组”涉及碎片化和重新组装。我们在巴勃罗·毕加索1937年的画《格尔尼卡》以及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神曲――《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这首神曲中,一个既定的主题一部分被剪切,却以变奏曲的方式重复。
“混搭”即融合各种元素,比如嘻哈音乐中节奏和旋律的混搭。
具有创造力的人会“变形、重组和混搭”已经固化的世界文化。具有创造性的人会对一个已有作品进行创造性改变来扩大创作范围:欧内斯特·海明威为他1929年的小说《告别武器》起草了47个版本的结局;毕加索由于受到迭戈·委拉斯开兹(Diego Velaquez)1656年创作的《宫娥》一画启发,一口气画了58件作品。有创意的人往往也是大胆的,正如企业家所知,创新是一项冒险的事业。
布兰特和伊格曼同时也探索了如何从“会议室到教室”全方位培养创造力,即在“非结构化游戏与模仿模式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像威尔逊一样,作者认为,创造力之源是因为单调的输入使大脑觉得很无聊所致。作者认为,与其他物种相比,人类在感觉(环境中有什么)和行动(我可以做什么)之间分布着更多的脑细胞,这使我们能够考虑现有各种情况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并从反思转向创造。这本书几乎没有涉及认知神经科学知识,以解释以上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也没有从进化角度认真解释为什么大脑会发生这些事情。因此,《迅速崛起的物种:人类的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这本书没有确认创造力的来源,也没有说明为什么独有人类获得了这种能力的恩赐。
不过,这两本书的新颖之处还在于揭示了公司会不断推出新的智能手机的关键,但是它是否揭示了创新驱动的本质?至少利维奥认为同样重要的是好奇心,在《为什么?是什么让我们好奇?》这本书中,作者从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角度积极地看待好奇心。
利维奥认为,天才们对于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常常好奇不已。他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的生平和作品的研究,以及对现代科学家和跨界名人的采访,包括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和吉他手兼天体物理学家布莱恩·梅(Brian May)。利维奥发现,尽管好奇心可以被新奇的东西激发出来,但之后一样也会面临困难,包括如何解释复杂现象(如何揭示工作机制),不确定性(需要思考进行哪些选择才能得到期望的结果)和冲突(这些新知如何与已形成的认知相匹配)。
有时候,好奇心会促使我们思考“自然是如何运行”这类重大抽象问题,就像艾萨克·牛顿的万有引力,或者查尔斯·达尔文的进化论。还会促使我们思考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些方法,例如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雷德里克·桑格尔(Frederick Sanger)发明蛋白质和DNA测序方法。而多数情况下,同一个人将在这些角色之间转换,正如《迅速崛起的物种:人类的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这本书所揭示的那样,爱因斯坦还从事过冰箱、照相机和麦克风的设计工作,同时还为一件衬衫申请过专利。
这三本书一起提醒人们,尽管人类创造力涵盖的范围和丰富程度令人惊叹,但我们仍然缺乏一个普适的科学框架来思考人类创造力的认知和进化的源泉。虽然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在加快,但下结论这提供了改变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还为时尚早。可以肯定的是,在极端气候频发、发展不平等和地缘政治不稳定的时代,亟须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游 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