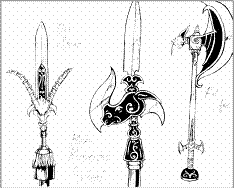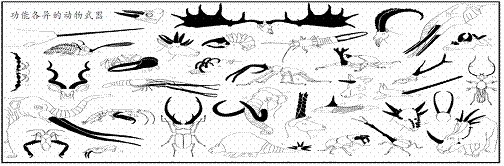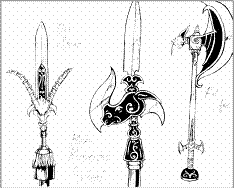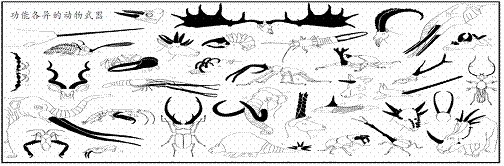在大自然生存的一些动物,其锋利的牙齿、利爪或其他“装备”看似具有攻击性;然而在动物王国里,很多“军备竞赛”的特点,即游戏规则是克制而不是互相残杀。

竞争导致形态诸多变化
雄性动物间的竞争常常体现为由骨骼、触角或甲壳质精心打造的“武器”。这些武器刚开始时往往较小,然而在竞争的压力下,经过漫长的岁月逐渐进化到巨大的尺寸。如现已灭绝的爱尔兰麋鹿(Irish elk,又名大角鹿,生活在300万年~1.2万年前,亚欧大陆广泛分布――译者注),两个鹿角的宽度竟有12英尺!不过,在这个貌似华丽的装饰品的背后,可怜的大角鹿不得不承受着超过80磅的重量。
根据一个新的对性选择(性选择是自然选择的一种特殊形式,它导致动物身上出现了一些奇异的武器或装饰品)的综述,美国蒙大拿大学的生物学家道格拉斯·J·埃姆伦(Douglas J.Emlen)汇集了关于进化动因的各种学术观点后认为,进化促使动物的武器如此多样化。
许多动物喜欢炫耀其装备以及一些艺术装饰品,性选择是查尔斯·R·达尔文(Charles R.Darwin)对这一问题的解答。然而在为生存的竞争中,这些进化而来的武器和装饰品似乎与他的自然选择学说相悖,成了一个“积极的障碍”(positive handicap)。为了解释这些奢侈品,达尔文提出:动物的武器和装饰品一定是在求偶竞争中形成的。
在达尔文看来,雄性动物间为得到雌性动物青睐而进行的竞争,驱动了动物武器的进化;而装饰品(主要是雌性动物)的产生则出于它们奖赏雄性动物的特征的选择。对雌性选择是如何导致动物界呈现高雅流行的缤纷色彩的,现代生物学家已经投入了相当多的关注,从鸟类羽毛到蝴蝶的颜色等。但是,对同样丰富的动物武器的多样性关注则较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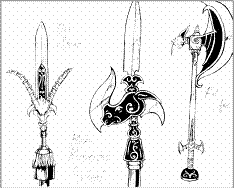
美国生物化学家大卫·伍德沃提出“动物武器”的概念
埃姆伦博士说,在研究了巴拿马的一种专门靠猴子粪便生活的蜣螂(题图)后,他对动物的武器产生了兴趣,并将目光扩展到了全世界的蜣螂。追踪溯源,蜣螂最早可能是从吃恐龙的排泄物开始它们的“职业”生涯,然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哺乳动物的粪便。在“吞食”过程中,它们会采用两种策略:一些蜣螂,如圣甲虫(scarab)把粪便切成小块,然后慢慢移走供自己享用;而其他的一些蜣螂则在粪便的下方挖坑,然后把粪便拖进挖好的坑内。
埃姆伦注意到,只有挖坑的那些雄性蜣螂才进化出了触角,它们用触角来保护坑内的“食物”免受其他雄性蜣螂的侵犯。尽管那些推粪球的蜣螂也一直在与其他的雄蜣螂争斗,但是它们没有触角。
进化促使武器功能各异
“我被这些有奇异形态的动物迷住了,而这些奇异的形态又促使你想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交配的。”埃姆伦说。在收集了相关论文后,他开始明白了雄性动物间发展武器的一个模式关系,即雄性动物用武器来捍卫甚至击败其他的雄性动物,以垄断繁殖优势确保某种资源的延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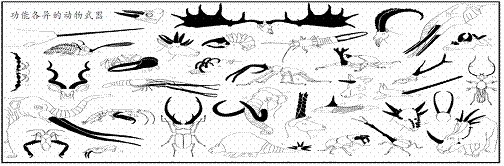
除了发展武器外,埃姆伦还推断,雄性动物通过拥有财产,如食物来源或利用雌性动物在坑内的机会接近它们,以此繁衍后代,这可能要比动物发展武器本身更为重要。
埃姆伦注意到动物武器发展的一个趋势,开始时都较小,仅仅是局部的微微突起,直至进化出更华丽的形式。这些武器实际上很有破坏性,因为它们唯一的功能就是攻击来犯的雄性动物。这些颇具艺术性的武器尽管看似吓人,然而造成的生命的损失似乎却很少。
其中的原因是,更具威胁性的武器往往承担着一个发送信号的作用。雄性动物并不会在致命的争斗中冒生命危险,它们能估量对手的武器以判断彼此的力量。如果对手远胜于自己,一方会拒绝争斗。华丽的武器也使双方的争斗仪式化,在这种仪式化的争斗中,雄性动物可以抵角相斗并判定彼此的力量,而不会彼此伤害。
“最精心制作的武器很少给对手施以真正的损伤,这些结构在揭示雄性动物间在大小、地位或身体状况的微妙差别方面非常有效。”埃姆伦在最近的一期《生态学进化与系统学年评》上写道。
既然这些武器仍不时被使用,它们因此成为雄性动物健康状况的一个现实信号。雌性动物对这个信息是最感兴趣的,它们总是在寻找反映雄性动物真实的身体信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同时也是研究软体动物“军备竞赛”专家的吉拉特·韦梅耶(Geerat Vermeij,世界著名的贝类分类学家)说,他同意埃姆伦其中的一个观点,即一旦有防御需要,这些武器就会被使用。但是韦梅耶博士说,他“怀疑这个结论,即最初能造成伤害的武器变成了展示的武器”。他说,例如螃蟹,在争斗进行到四分之一时就失去了它的钳子。
人类是否与动物相似?
美国犹他州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恐龙专家兼馆长斯科特·桑普森(Scott Sampson)说,在有蹄类动物中,当这些动物开始成群生活时,武器常常变得危险性较小,雄性动物会合力保护雌性动物以抵御捕食者。
那么,雄性武器的理论有多少不在埃姆伦调查的群体范围内,如灵长类动物,特别是人类?
跟其他优势物种(dominant species)相比,人类看似很悲哀,只有微不足道的牙齿和四肢。然而,这没成为和平意图的符号,而是他们制造武器的事实。人们制造的武器,就像生物的武器一样,也承担了一种展示功能――想想日本武士头盔或装甲骑士可怕的模样,或前苏联时代在莫斯科红场展示的坦克和火箭。
其他灵长类动物在竞争中也时常展示它们的武器,这些武器“的确在没有发生实际身体暴力行为的情况下解决了争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灵长类行为研究专家罗伯特·赛法思(Robert Seyfarth)说。特别是在狒狒中,这种展示通常采用打哈欠的方式,即雄性狒狒利用打哈欠展现其锋利的犬牙,以此唬住对手。
狒狒威胁对手的另一个展示手段是发出“哇胡”(wahoo)的叫声,它们的叫声在几公里之外都能听到,是地球上哺乳动物发出的最大叫声之一。
对人类而言,在吸引女性和给其他男性留下深刻印象方面,演讲和武器可能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非常合理地假定,随着人类进化和我们的文化变得日益复杂,制造工具的技能或其他的文化取代了作为男性竞争‘标记’的结构特征。”赛法思博士说。
但是,仍有较少的理由认为,随着人类开发的武器变得日益精细化,在其精准度提高的同时,破坏性也随之变小。埃姆伦认为这与动物武器的情况一样。偶尔地,一件新式武器对于一般用途来说似乎很可怕,如弩弓。当时教会裁定,它只能部署针对撒拉逊人(Saracens,狭义的撒拉逊人指中世纪时期地中海的阿拉伯海盗,广义的则指中古时代所有的阿拉伯人),而不能对同道的基督徒使用。不过随着大众对弩弓越来越熟悉,这些限制不久就消失了。在现代,尽管人们生产出了化学、生物和核武器,但在使用时都是犹豫不决的。
“我们没有降低武器的杀伤力,事实上我们的确夸口并用它们作为展示,这与其他动物并没有两样。”韦梅耶说。
埃姆伦的兴趣不在于他的武器进化规则怎样才能适用于人类,而是在于动物中的武器为何如此多样,从独角仙(rhinoceros beetle)巨大的触角到甲龙(ankylosaur)的狼牙棒般的尾巴,再到锯鳐(sawfish)嘴上的“长锯”。他的回答是,多种进化过程同时也驱动了武器的进化,从雄性之间的竞争到展示功能,再到性选择。至少对动物来说,例如,从一场军备竞赛开始的一只象鼻虫(weevil,一种甲虫。在美国,它是对棉花危害最大的一种昆虫。灰色成年的象鼻虫约有0.4厘米长,其中鼻子占了一半――译者注)可能以产生出装备了武器的后代而结束生命,就像一只独角仙那样。
资料来源 The New York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