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DNA双螺旋结构发现50周年,《科学美国人》杂志主编约翰 · 瑞尼(John Rennie)不久前在位于纽约长岛冷泉港实验室詹姆斯 · 沃森的办公室,对这位著名科学家作了访谈(沃森曾任该实验室主任达25年之久)。沃森把分子生物学的现状以及围绕遗传学的争论归于双螺旋的发现——
科学预测往往不准确
Scientific American(以下简作SA):如今,DNA已不再仅仅是科学的象征,它还并发出大量的文化现象。你是什么时候起致力于双螺旋研究的?你是否预见到DNA会成为尽人皆知的科学事件?
图为詹姆斯·沃森
James D. Watson(以下简作JW):没有,没有。我们不可能预见到这些进展,因为没有人想到为DNA测序或扩增DNA。结果证明所有的一些预测都是搞错了的。但是一位有名的澳大利亚免疫学家波尼特(Burnet)在1961~62年的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只有在人们读懂DNA后,DNA和分子生物学才会影响医学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基因组计划那么重要的原因。
无论克里克还是我现在都被描绘成非常科幻化的人物,似乎我们总是在思考DNA双螺旋的存在。科学预测的价值在5年后就差不多丧失了。1953年,我们想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试图知道DNA是如何提供信息、产生蛋白质的细胞机制是什么?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我们并没有去想基因治疗的问题,这件事是在15年以后,即到了1968年,限制性内切酶被发现后才成为可能。并且很快的,DNA测序也就开始了。
何以成为DNA最早的研究者之一
SA:你曾经说过,你之所以成为DNA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是因为你对进化和信息有兴趣?
JW:我不能肯定物理学家埃尔文 · 薛定谔是不是第一人,但在我所接触过的读物中,他是第一个表达图为詹姆斯 · 沃森对“必定存在着某种密码,允许细胞中的分子携带信息”这一思想的学者。在他于1944年出版的那本《生命是什么?》的书中,薛定谔就差没有说“甚至包括了蛋白质的信息”这句话,但他还是传达出了这样的思想,即存在一种能携带信息的分子。
那时,薛定谔的书已出版,但有些科学家如生物学家霍尔丹(Haldane)当时正在做连接基因和蛋白质的课题。那时,蛋白质的氨基酸序列并没有人做,你知道尽管这只是某种顺序,但那是事情的全部。那时只有我们得到了DNA结构,化学家弗雷德里克 · 桑格则测了首个多肽蛋白质链。
SA:你们的工作更多地是受那个说法的吸引而非野心所驱动?
JW:我这个人生来好奇。譬如我更多地是读经济史而非历史书,因为我喜欢解释。如果你希望得到关于生命的解释,那就必须了解生命的分子基础。我从未想到存在一种生命的心灵基础。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的是我是由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父亲领大的,我也没有那种精神上的烦恼。我母亲曾经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教徒,但那是很早以前的事。
罗莎琳德、威尔金斯和DNA
SA: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围绕双螺旋的竞争。显然,个人的人格强烈地影响到了事情的细节,包括谁是第一个发现者和如何作出发现的。这一发现至少从时间上讲似乎是可以预料到的?曾经有许多人和你们的工作非常接近,包括加州理工学院的林奈斯 · 鲍林(Linus Pauling)、国王学院的莫里斯 · 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和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
JW:我们并不知道罗莎琳德 · 富兰克林在二月底已经递交了B型,因为她那时已经离开了国王学院。我们当时确实不知其事。直到我在1968年写《双螺旋》一书时仍然不知道这件事。
SA:关于莫里斯 · 威尔金斯未经富兰克林许可给了你们她的结晶图像一事,外界一直有争论。
JW:人们也说过,为什么你们后来不去与富兰克林沟通一下,感谢她提供的图像。她并不希望讨论这件事,她也没有同她的合作者谈论这件事。当她快临终时,她曾有一次与弗朗西斯在一起,这应该是一个可以回溯过往事情的机会,但她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她错失了这次机会。可能她希望有下一次机会。
SA:回想起来,当年的诺贝尔奖如果授予富兰克林和你们比授予威尔金斯是否更合适些?
JW:我不这样认为。威尔金斯给了我们A型结晶图像,富兰克林给了我们B型的,于是可能会有人认为他俩应该得到诺贝尔化学奖,而我和克里克应该得到生物学奖。这似乎是奖励我们四个人的好办法,但没有人会真正想到这一方案。
我们之所以出名是因为DNA本身非常有名。如果罗莎琳德与弗朗西斯从1951年起就讨论关注DNA,将她的研究数据与弗朗西斯一起分享,那她就有可能解决这一结构,那她也就会非常出名。
在那个周六的早晨(1953年2月28日,当天沃森和克里克设想出了双螺旋结构),我们在提出一个新的并认为是正确的模型。我们考虑到了X射线的数据,当时这些数据被认为是决定性的。由于这一模型使人联想到某种复制方案,这样所有的生物学家都希望相信这是独立于X射线数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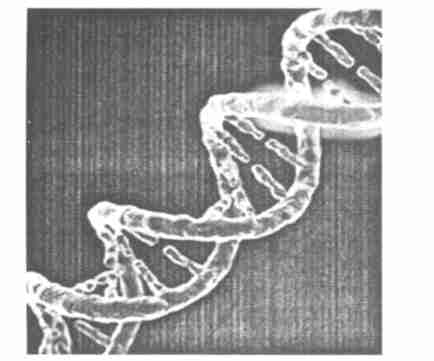
还有多少秘密可待揭示?
SA:由于核苷酸碱基“A-T-G-C”的互补性,使得双螺旋结构复制了其自身?
JW:你知道吗,我们曾想到过我们可能只能得到一半的结构,日后等其他人再来给出结构,那时你可能会问如何复制。
SA:在一个世纪里,人类完成了从对孟德尔定律的重新发现、确认染色体是遗传介质,到对人类基因组大体上的解读,而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差不多是在百年周期的中间。就DNA而言,还有多少秘密可待揭示?是否还可能作出大的发现,抑或只能是作些修修补补的工作?
JW:我想一个主要问题是染色质(包括DNA的动态复合体和构成染色体的组蛋白),在被组蛋白覆盖后,染色体上哪一段DNA是有功能的?这是由什么决定的?在甲基化作用和渐成论(epigenetics,用化学方法修饰DNA以影响基因表达)方法作用下会发生什么?人们是否可以超越DNA序列遗传某些东西?这些是当今遗传学有可能作出激动人心发现的领域。
现在的进展相当快,很难作出推测。但我的推测是再过10年,分子生物学领域将发生极大改观。现在有大量非常优秀的人在这一领域工作,我们也有了必要的手段。从某种程度上看,遗传学的基本原理有可能按照基因功能重新确立。这方面的进展将使我们应对更多的问题,如理解大脑是怎样工作的。
SA:RNA正在从DNA的阴影里走出来。人们现在正在关注如RNA干扰之类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RNA分子能反作用于基因。我们是否还需要破解RNA动态复杂性的难题?这一问题是否能与组蛋白相提并论?
JW:是的,这是一个比我们在1953年想得更为复杂的问题。人们以前只想到RNA的一种类型,但要制成RNA,你必须要修饰组蛋白。我想在染色质方面它们是一样的。
理解大脑将是更大的挑战
SA:在最近一期的Nature上,哈佛大学的瓦尔特 · 吉尔伯特(Walter Gilbert)写道:“分子生物学已经死了”,他的主要理由是,现在DNA这一学科已经可以归到任何其他领域。
JW:我同意这一说法。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DNA已经成为一种工具,什么事情都来自DNA。例如,你可以说你从金丝雀的行为来研究DNA。我想我们确实需要研究金丝雀的行为!有一个比DNA更大、更难的问题是,要理解大脑是如何储存、检索、利用信息的。
SA:如果你作为一个研究者,你将着手做哪些事?JW:我会致力于研究基因与行为之间的关联性。
即使你有可能发现行为基因,但也不可能知道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首要的科学兴趣是研究鸟类是如何迁徙的。而在你知道鸟类脑的工作原理前,就不可能了解基因是怎样告诉鸟可以迁徙到哪里去。因为要知道,母鸟是不会告诉雏鸟飞到何处的,这种本领来自遗传!
当然还有大量的鸟类行为有待认识。有人说对男人喜欢男人不可理解,但我要说,这实际上就同为什么男人喜欢女人一样不可思议。
要真正理解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弗朗西斯致力于大脑研究(超过了对DNA分子的兴趣)。现在(科学)上已经不可能有一种所有东西都为之旋转的中心了。
和弗朗西斯仍是好朋友
SA:半个世纪来,你和弗朗西斯 · 克里克已被历史和公众的联想连在一起。事实上你俩现在并没有合作,并且已有几十年未再合作了,你俩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吗?你俩还是朋友吗?
JW:是的。我想我俩仍是朋友。他总是像一位兄长,毕竟我们有12岁的差距。我们往往会非常快地交换信息,就是说我俩想以同样方式交换信息。我俩都会很理智地抵制那些所谓的天才发现。弗朗西斯对政治没有兴趣,我不知道他以往是否这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朗西斯思考科学的时间超过我,我比较容易分心。
治疗性克隆没有什么不对
SA:讲到政治这个话题,近一段时间来许多与基因有关的话题在公众中反响强烈,如基因改良食品、克隆、DNA指纹等,你认为对这些技术的政治监督有大多的可信度?
JW:这些问题争议确实非常大,以致国家很难插手其中。是的,我也只能置身局外,等到出了事再去处理。至于是否同意复制婴儿的决定应该由当事妇女自己作出,而不是由国家作出。
我认为,克隆现在是一个问题,但第一个克隆人的问世不会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样,他不会危及任何人!如果你的健康不佳,你的太太身体也不好,而你们想要一个健康的孩子,我知道一位有名的法国科学家他一直没有孩子是因为其家族中有人患过精神失常,而克隆可能意味着不会有任何这类精神失常患儿。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认为相对于国家权力而言,最值得关注的是家庭的权利。有人会说,那会导致定制婴儿的出现。但我要说,定制的服装错在哪里?如果你想要一个不会患哮喘的孩子,那不是很好吗?治疗性克隆有何不对?这会损害谁的利益?
重在改变是科学的本质
JW:人类对于生命一直有某种神秘感,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你不是科学家,你就很难完全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些都是分子,很难理解从分子开始的人类的意识及其复杂性。由于我们尚不理解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并不能断定细菌没有精神。
我记得物理学家狄克 · 费曼(Dick Feynman)和我在1964年收到来自加州——犹太教牧师相同的来信,询问我们的宗教信仰。我想狄克可能会在复信中写他没有宗教信仰。我的回信非常礼貌,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但我想狄克会说出他所想的。美国的问题是,不信仰上帝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宗教到底是否有意义,这在美国是不能讨论的,而在欧洲可以。
SA:公众对于遗传方面的知识知之越多是否会导致决策更谨慎?你是否担忧公众在辩论基因改良食品及其他方面的辨别能力?
JW:如果你认为每一植物都是神的产物,是有某种意图的,那你就不能改变它。但美国人并不是那种清教徒。我们可以改变一切,我们并不一味遵从历史,而更重在改变。我想任何试图停止改善人民生活的想法都是同人类的精神相悖的。
[Scientific American,2003年3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