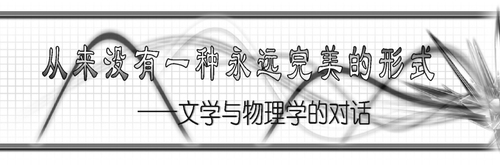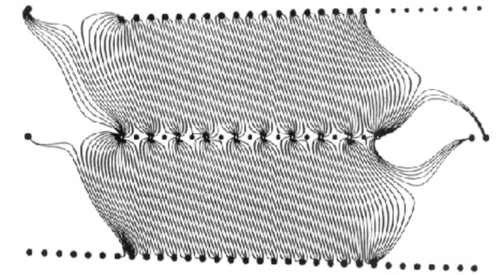在科学上,一切探索最终都要经受实验的考验;在艺术上,则是经受时间的考验。如果它们确是挖掘到世界的一个新的方面,就能够深入人心,那它们是美的。20世纪数学大师外尔曾说:“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当必须在两者中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
演讲者:
王蒙(作家、原文化部部长)
冼鼎昌(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
文学和科学,实际面对的是一个统一的世界。科学和文学都力图对这个世界有所发现、有所了解、有所感悟
王蒙:在文学中,数学与几何图形都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例如,古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既有数字,又有几何的远近透视的对比;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具几何图形。
中国诗人喜欢写风花雪月。风和雪是属于气象的东西,花可以属于植物学,当然还有其他的属性;其中又特别喜欢写月,“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样的诗句实在太多了。记得30年代左翼的文学工作者,曾在上海发起过一个宣言,就是不写月亮;认为写月亮太多了,对于老百姓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使我联想到在1949年以后,最早受到批判的小说是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丈夫是一个知识分子,妻子是工农干部。有一次他们发生了矛盾,丈夫说:月亮多美啊!妻子则说:月亮美有什么好处,还不如一张大饼呢,可以解决我们的饥饿问题。这在当时是很有名的。
气象更是文学最关心的对象。“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和季节有关系的,实际是按照地球和月亮之间的互相关系确定的24节气。至于那个“雨纷纷”所带来的韵味,太深层了。实际上,中国文人对于雨雪的感觉不亚于月亮。
时间和空间是科学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文学所关心的问题。对于时间的安排,对于昨日、今日,在王羲之的《兰亭集序》里都有发挥,每一个过程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从现在看,我们觉得是过去,但是从未来看现在,又成了他们后来说的过去。这是人的一个大悲哀,但这也是人生的一大滋味。如果没有这样的时间变动,人生又有什么酸甜苦辣,又有什么东西可以写?所以这是诗人对时间和空间的一个感受。比如说植物,“去年今日此门中,桃花依旧笑春风”,其实中国的文学和诗人,他们对于植物的理解和感受,很合乎科学的道理,合乎生物学的道理。总是把对于春天和花的感受,包括落花的感受和一个人的青春期的心理,或者是说和性心理联系在一起,使你惘然,又使你在期待着什么。在《红楼梦》里写春天,林黛玉的感受就更多了,把春天,把季节,把植物,把花朵和人的生命、爱情,甚至是性的萌动和要求都连接起来了。
当然,文学家没有解决任何科学的问题,它既不能解决地球的自转和公转,也不能解决植物的分科、分系,细胞的繁殖问题,但它作为一个观察者,一个感受者,我觉得科学和文学都力图对这个世界有所发现,有所了解,有所感悟。所以这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有价值的精神活动。科学为人类缔造了一个智慧的世界,文学则缔造了一个既有智慧,更多的是感情方面的世界。
冼鼎昌:我很赞成王蒙先生的观点。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科学和艺术是严格有别的,要不然为什么从中学开始,就有文科班和理科班之分呢。可是我认为这不是很妥当的说法。有一些人说科学追求的是严,艺术追求的是美;一个是理性的演绎,另外一个是灵感的发挥,两者是南辕北辙——这个论点是很不幸的误解。
西方有一位很有名的文艺评论家叫丹纳,他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艺术家,是因为他知道辨别事物的根本性质和特色,别人只看到了部分,而他看到了全部,抓住了其中的精髓。我们不妨把话中的“艺术”换成“科学”,便可得到如下论点: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科学家,是因为他能辨别事物的根本性质和特色,别人只看到了部分,他却看到了全部,并且抓住了精髓。我想在座的科学工作者会同意这样的观点。科学和艺术,在创造性方面是有共性的。
看来开普勒后来的发现,完全偏离了最初的关于美的想法——关于和谐的简单的想象。但谁能够说开普勒的发现,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赞叹的和谐的现象呢
冼鼎昌:有共性的东西就可以进行比较了。关于美的讨论,西方认为是从柏拉图开始的。柏拉图曾经说过,美是难以定义的。20世纪的大物理学家狄拉克也说,数学美和艺术美一样是无法定义的。他接着又说,研究数学的人要鉴赏数学美,并不会觉得困难。他的后一句话是说,美是存在的,并且是可以感知的。承认了美的存在和可感知性,我们就可以讨论下去了。
人们用什么感知美呢?大哲学家柏拉图说是灵魂,大数学家庞加莱说是纯理智。灵魂也罢,纯理智也罢,反正是思维,人的思维是随着时代发展的,因而,美的感知和美的观点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古代的思想家把美与和谐划上等号。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整个宇宙是和谐的,就是一种数,在数字之间有着能够产生和谐的比例。他提出一个后来被柏拉图称为黄金分割的比例,就是把一根线,在某一点分割成一长一短两段,比例为0.618和0.382(正好是短段和长段的比例),这就叫黄金分割,那个点叫做黄金分割点。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学家,就是根据这个比例来构思他们的作品的。有一个非常美的雕像——维纳斯雕像,有人说其中有好些黄金分割,例如,从它的头顶到肚脐,黄金分割点在喉头;另外,肚脐又是整个雕像高度的黄金分割点。这的确是个非常完美的比例。即使在今天,那些残存下来的,在长、宽、高三方面遵循这种比例构成的希腊雕像和神庙,还在现代人的心里引起巨大的美的战栗。
美与和谐的等号告诉人们:自然是美的,自然的规律也是美的。所以亚里士多德说,完美的天上物质构成的天体,它的运动轨道,必定是完美的曲线。完美的曲线就是圆。所以所有的天体运动轨道,应该是圆。千百年来,这种观点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包括现代科学的两位奠基人哥白尼和开普勒。
哥白尼提出的日心体系理论,带动了近代科学思想的一场革命。在哥白尼的理论中,地球和另外当时知道的五个星体——土星、木星、火星、金星和水星绕着太阳转。它们的轨道都是圆,而且都作匀速运动。
开普勒则进一步想从和谐对称的原理来确定这六个行星的轨道。在几何学中,除了球体外,有着最大对称的几何体是正多面体。几何学中只有五个正多面体——正四面体、正六面体、正八面体、正十二面体和正二十面体。开普勒认为,六个行星的运行轨道应当由球面和五个正多面体决定,而且由于和谐原理,天体在圆形轨道上作匀速运动,由此可以定出六个行星的公转周期。他的计算结果,据说能够和当时的天文观察吻合。
于是,他在1596年写了一本《论自然的和谐及相似》专著,送给当时最负盛名的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第谷给作者的忠告是:“首先要通过实际观测来为自己的观点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提高,才能深究事物的根由。”
幸亏听从了这个忠告,并得到第谷以毕生努力累积下来的系统的、极为精确的观测数据,使得开普勒得以做出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三大发现。其中第一个发现是行星的轨道并不是完美的圆曲线,而是椭圆曲线,并且行星的运行也不是匀速运动的。
看起来,开普勒后来的发现,完全偏离了最初的关于美的想法——关于和谐的简单的想象。但是,谁能够说开普勒的发现,不是一个非常令人赞叹的和谐的现象呢?在他的三大发现的基础上形成的牛顿力学中,他的发现是如此令人震惊的和谐。
和谐与对称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们又是和美密切地相联系。我们每个到北京参观过故宫的人,谁不被这组巨大建筑群的和谐与对称所震慑呢?有一年我去米兰参观一个大教堂,就觉得好像我来过,好像看到老朋友一样。到快参观完时我才恍然大悟,这是巴赫伟大的《恰空舞曲》给我的联想。曲中32个变奏组成的对称非常严谨,音乐的洪流和谐流畅,音乐的形象庄严雄伟、气势磅礴,就如这座教堂一样,直入云霄,欲与天齐。这就是建筑的美,音乐的美,就是它们之间的互通,给予我似曾相识的感觉。有人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此话有道理。
如果只有对称,那是很遗憾的事情——美学中只剩下图案,科学中也没有了许多学科。大家小时候想必看过万花筒,每摇一下,就会出现不同的完美对称的图形,但这只是图案,不能成为深刻的艺术,因为它无法融入艺术家的创作思维。在物理学中,只剩下完美晶体的物理而没有表面物理,没有界面物理,没有半导体物理,这太遗憾了!现代人怎么能够想象没有半导体晶体管,没有集成电路芯片,没有移动电话的生活呢?芯片就是用有掺杂的不完美晶体造成的。无论是科学还是艺术,总要有对比,通过从和谐到不和谐的发展,引至突破,达到在一个新高度上的和谐。
20世纪的科学经历了令人目眩的发展。从美的角度来说,一个重要的特点是远离了古典的对称与和谐。用科学术语说,引入的不对称与不和谐的量越来越大。
在1957年,两位科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说,不是所有的对称都是被自然尊重的。他们提出这个理论时,许多大物理学家不相信,诺贝尔奖得主泡利就说,他不相信上帝是个左撇子!可是另外一位美国的物理学家,一位很伟大的华裔女性,叫做吴健雄的,用实验证明了他们两位是对的:上帝有时是100%的左撇子。这样在科学领域就开辟了关于对称性破坏的分析,研究的成果非常深刻,使科学家对自然有了一个更深的理解:规定世间物体运动的方程是由对称性确定的,而物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则是由对称的破缺决定的。对称有道理,不对称也有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一些物理学的基本的概念——电磁现象和弱作用现象的理论、广义相对论等等——把对称和不对称统统归纳在一起,将科学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显示出空前的、惊人的美。
我从来不认为科学技术会威胁文学作品,我愿意我们的审美体系不断向前发展
王蒙:说到发展,我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科幻小说这么不发达。在世界各国,科幻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科幻电影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美国的《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虽然这里面科学的含量有限。又比如说法国作家凡尔纳的作品,影响有多大。但是中国的幻想,老是放在人体自身上,就是人体自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比如说《封神演义》中的土行孙只要脚一抬,自己就可以从土里出来;又比如说《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这么多的本领,但是它并不是借助工具,不是借助科学,而是凭借自身的特殊本领,有七十二变,他可以变成动物,也可以变成庙宇。
还有中国的武侠小说是很好看的。有一年,我在青岛参加科学家和文学家的对话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们说自己很喜欢文学,喜欢看小说,我说你们看些什么小说,他们回答我是看金庸的小说。金庸的小说有科学吗?也可以说有科学,因为他也很关注人是怎样练内功和气功的,包括怎样练各种古怪的功,怎样把我的功转移到你的身上。其实我也很喜欢看金庸的小说,但是这里面表达的,算不算是对人体科学的兴趣呢?就是希望人进行了一种特殊的锻炼后,他的力气和感受与别人不一样。有一位大侠眼瞎了,但瞎了以后仍然可以与人搏斗,因为他有非常好的感觉,可以感受常人所感受不到的感觉。所以中国的武侠小说实际上也提出了一个课题,就是人应该怎么样发展自己?人体的功能究竟有多大的余地和空间?有一阵,对于人体科学,甚至一些大的科学家也说了很多话。人的确有很多的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当然对人体的发掘,也有不少是走火入魔的。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西方特别重视工具,特别重视利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发展人。而中国呢,更多地是侧重人的本身的功夫和锻炼,或者是技巧,这种思路与西方不大一样。
也许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审美力还是建立在科学技术并不十分发达的基础上的。有一次,我对医生开玩笑说,诗人要是写你们“动刀无影灯下,悠然白细胞病变”,这肯定是不美的。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看到一首歌颂电脑的诗,没有看到一首歌颂核电站的诗。
也许有人因为受了西方新左翼思想的影响,或是受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科学的影响,认为科学把人的怀古情结都给破坏了。比如说月亮,我们对于月亮有多少的幻想啊!有嫦娥奔月,还有吴刚和小兔,可当我们还在“文革”时,美国人就已经去了月亮。而我们在新疆收听半导体广播时,老农民就说,这是不可能的,上月亮的话,要骑马走多少多少天啊!一次登月,就把人们对月亮的很多幻想给破灭了。
这种意见我个人并不赞成,因为我相信,当科学技术给了我们精确结论时,也带来了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这些不知道的东西,仍然有文学艺术奇思妙想的余地。所以我从来不认为科学技术会威胁文学作品,我更愿意向科学家或者是新的技术学一点知识,使我们的审美体系不断向前发展。
我向大家坦白一件事,对新造的国家大剧院我投了赞成票。我其实也参加过评审的,虽然起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我知道这种事肯定有反对意见的——埃菲尔铁塔到现在也还有反对意见。在古老的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和国家博物馆旁边突然冒出了一个大“鸭蛋”,会有怎么样的效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美不能先验地规定:在科学上,一切探索最终都要经受实验的考验;而在艺术上,则是时间的考验
冼鼎昌:王蒙先生说得很有意思。其实在艺术中,相应的变革来得比科学的变革还要早。但画家们并不像科学家这么走运,所有走过印象派作品展馆的人,都可以嘲笑画家们一番??在音乐领域中,音乐印象派在很多结构发展的原则上也偏离了传统,但其美妙的新和声与旋律征服了传统的听众。这只是开始,随后的艺术,越来越不对称,新的东西越来越多。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初艺术家莫奈、德加、德彪西等人的开创,无非从一个新的角度描写了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东西。和谐-不和谐、对称-不对称本来在自然就是存在的,何况最初时的不和谐与不对称是作为小量引入对称与和谐之中的;而当时所引起的轩然大波,倒是有些难以理解了。不过这种思想骚动不只是在艺术界才有,在科学界也有。
在19世纪即将结束前,英国杰出的大科学家开尔文勋爵认为:物理学的天空里一片晴朗,除了两朵小小的乌云之外。当时所有已知的物理现象,放到力学、电磁学、热力学等高度完美的理论框架里面,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解释。但是进入20世纪,那两朵小小的乌云竟导致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
在量子力学里,有一点很叫人奇怪:传统的美不存在了。传统的理论美起码要完整、要清晰、要确定。可是在这个理论中存有不确定的因素,在基本概念中有朦胧的地方。这个不确定性,到底是新理论的毛病呢,还是大自然本来就是这样的?有很多人质疑新理论,说它不会成为真正的理论。爱因斯坦就是其中一个。他一生中提出过种种极为尖锐的质疑,尽管都没有难倒这个理论,但他还是认为“上帝是不掷骰子的。”
我认为量子力学还是很美的。美在什么地方?是朦胧美。光到底是波动,还是粒子,在牛顿的时代就发生过严重争论,因为两种性质相悖,不能并存;但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大自然本来就是这样,光既是波动,又是粒子,有不确定性,只是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而已。
诗人对此认识得比科学家早。唐朝李商隐的朦胧诗《锦瑟》迷住了多少人,但又有多少人说得清诗中的两联到底应当作何解释?有人去问非常聪明博学的苏东坡,他解释为锦瑟之声,“适怨清和”。我读此故事后对诗中用典似乎有点明白了,不过对诗人把两对相悖的形象放在一起在读者内心世界产生如此复杂微妙的效果的天才创造,是我在学了量子力学后才领悟到的。大自然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以前只是看到了一面,但也要注意观察与它相悖的不同方面。
我们在晚上仰望星空,往往会想起“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名句,觉得这个宇宙是多么宁静。可惜这只是一个错觉,因为宇宙中充满了纷乱。最早发现这一现象的是中国的一位司天监,并详细记录在《宋会要》中,时间是在宋仁宗时代的1054年。当时天上出现了一颗非常亮的“客星”,甚至白天也可以看到它。现在过了快1000年,我们已经弄清楚这不是什么客星,而是一颗恒星死亡,一次超新星的大爆发事件。这种事件,只是宇宙中诸多纷乱的一种。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不久前发表的一个消息说,去年发现的一次非常激烈的超新星大爆发,死亡恒星的质量相当于150个太阳,是迄今观测到的最亮的一次超新星爆发。
宇宙本来就是从大混乱里产生的,也可能会在大混乱中结束,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知道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但是,想到在这1000年间宇宙学的巨大进步,我们就不能不为人类在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
那么我们如何来看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和变迁呢?就物理学而言,上世纪物理学大师劳厄说过一番很有见地的话:“物理学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观察量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
如果我们在这段话中改动几个字,把“物理学”改成“艺术”,把“观察量”改成“艺术对象”,我们就会得出一个对于艺术发展的说法:“艺术从来不具有一种对一切时代都是完美的、完满的形式;而且它也不可能具有完美的、完满的形式,因为它的内容的有限性总是和艺术对象的无限丰富的多样性相对立的。”
这番话,不是同样有见地的吗!是不是一切新的探索最终都归结到美呢?
在科学上,一切探索最终都要经受实验的考验;在艺术上,则是经受时间的考验。如果它们确是被挖掘到的世界的一个新的方面,而且还多一点:能够深入人心,那它们是美的。
美不能先验地规定,就像毕达哥拉斯和开普勒那样。大师也会犯错误的,有时还是大错误。爱因斯坦认为,美是探求理论物理学中重要结果的一个指导原则。20世纪的一位数学大师外尔也说过:“我的工作总是尽力把真和美统一起来,但当我必须在两者中选一个时,我通常选择美。”但正是他关于美的先验的标准,使他相信左和右在宇宙中是对称的,从而扬弃了他发现的一个重要理论——中微子的两分量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左和右是完全不对称的。然而上面提到的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工作证明,这个被发现者扬弃的理论其实是正确的。
在平衡美学的追求与科学的探索时,我想,当年第谷对开普勒的忠告——首先要通过实际观测来为自己的观点打下坚实的基础——是非常值得记取的。
本文为王蒙和冼鼎昌在2007上海国际科学与艺术展“科学与艺术”讲坛上的演讲,本刊作了删节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