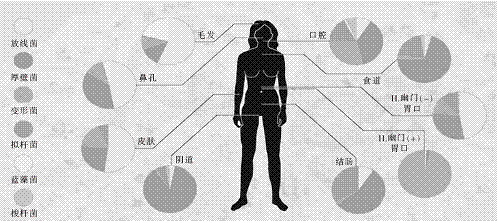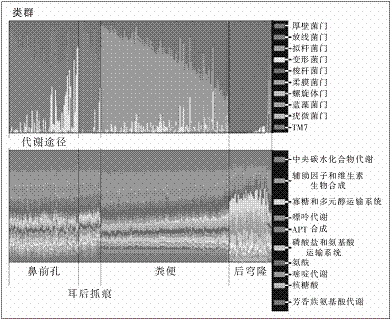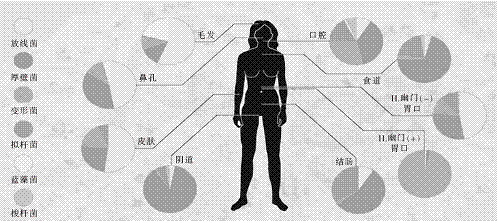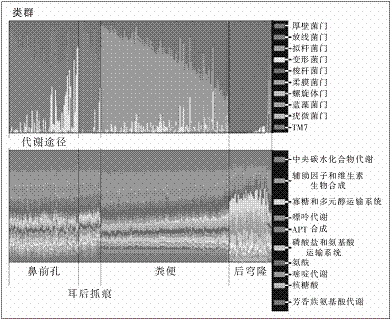事实上,超越人类感官能力之外的生物世界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但直到最近,医学界对微生物的态度仍在善意的忽视、怀疑或不信任间摇摆不定。从好的方面理解,寄生于人体内的微生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从坏的角度考虑,微生物是致人类各种疾患的病原体……

安东尼·凡·列文虎克
“雨水”中的“小动物”
1676年,荷兰布商和业余博物学家的安东尼·凡·列文虎克(Antoni van Leeuwenhoek)用自己设计的显微镜观察到被他称之为“小动物”的微生物世界,然而,他的描述却被后人误解了整整300年。其实,列文虎克观察到的是人类首次对微生物的已知描述:“这么的微小,要是将100个微生物一个一个地积聚在一起,它们连一粒沙子的长度都不到。”但同时代的科学家却很难相信它们的真实性。
当列文虎克将自己的观察记录提交给伦敦皇家学会后,得到的回复与其将此记录编入拒纳信年鉴中,或许还不如不回复的好:
“在您所描绘的无数‘小动物’的报告中,我们好像看到它们正在雨水中游泳,借助您所称之为‘显微镜’的东西,引起了学会成员们的相当兴趣……您对这些看不到的各种躯体生物及其活动的精细描述让我们的成员联想到,在你的‘雨水’中可能含有充足的蒸馏酒成分,而且研究人员都曾喝过。现在,皇家学会成员们已经完成了投票,但我们不无遗憾地通知你,根据大家发出的咯咯大笑声显示,他们已经决定不准备在如此受人尊敬的学刊上发表贵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祝福‘小动物’们在您所具有的独创性发现和照料下,能够健康成长,不断壮大,并得到良好的饲养。”
事实上,超越人类感官能力之外的生物世界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最近,医学界对微生物的态度仍在善意的忽视、怀疑或不信任间摇摆不定。从好的方面理解,寄生于人体内的微生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从坏的角度考虑,微生物是致人类各种疾患的病原体。无论出于何种考量,微生物要么被忽略,否则,就应将其灭绝。
然而,自列文虎克发现“小动物”350年后的今天,科学界给予了微生物应有的评价――它是构成复杂人类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列文虎克发现的基础上,科学界通过一系列技术突破,包括DNA测序,开始认识到,我们的生物身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存在。
或许,科学才刚刚开始了解微生物在人体内的多度性和丰富性。重要的是,这些微生物不只是简单的蜷伏生物,更是贯穿于整个微生物世界,它们不仅对我们的健康状况、消化能力、代谢程度及药物反应产生影响,更不用说影响人类的生存和进化全过程。微生物几乎根植于人体的表里内外,从出生到坟墓,伴随于我们的一生,一直在塑造着人体的生态学范畴。微生物是人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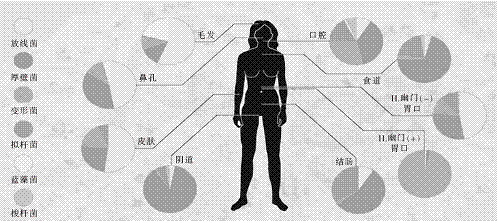
菌种的存在和数量在相同个体内的解剖位置上会出现很大差异
人体生态系统
在21世纪,生命科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分支――微生物组学。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100万亿个微生物存在于我们的肠道中。与此同时,人类承载的多个微生物系统居然让沉寂已久的生态学原理重新焕发生机。面对难以理解的序列数据,分子生物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对进化论进行了梳理,微生物学家似乎同时契合了生态学的方法和原理,多种生态系统得到开发,涉及范围从热带雨林到太平洋潮间带等。
20世纪下半叶,通过建模、观察和一系列实验,逐渐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理论,分别对陆地生物和水生生态系统的分布、多度和稳定性进行了解释。然而,得益于测序的发明,在新的微生物组范式下,热带雨林和珊瑚礁生态系统之说支持人体内部生态系统理论。从细菌的培养到识别,现在已经基本描绘出微生物组生态学的大致轮廓。
当然,科学家还需从机理上对这些描述进行探讨,包括现有的生态学规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微生物组规模的背后机制。人体微生物学的发现,为测试生态模型的普适性提供了机会,包括很多微生物的发现,在时间尺度和生命规模上将促使我们重新评估,究竟与先前的研究有什么根本的不同。若要提高这种可能性,生态学原理或还要进行重新修订。
就人体微生物组而言,它不只是一个单一连续的生态系统,它已经进化并占据人体五个不同的栖息地:皮肤、鼻腔、口腔、下胃肠道和阴道。进而,还要依次对这些栖息地再进一步细分。比如,栖息在脸颊部位的微生物群落显著不同于牙垢上的菌斑。
迄今,生物学家仍然不能确定人体栖息地究竟有多少微生物构成。虽热如此,早期研究报告认为:下胃肠道可容纳超过3万种不同的微生物,口腔排名紧随其后。或者,像妈妈们唠叨的那样,耳朵后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人体内的微生物甚至超过了热带雨林(在一英亩土地上,或许能找到1.5万种不同的微生物)。
上述初略估计,仅仅初始反映了人体微生物组的复杂性,更细致的分析应专注于构成这些群落的微生物细胞的数量上。在这里,一个通用的模式,即少数微生物数量有时会非常庞大,有着惊人的长尾分布效应,其中既有方法论的影子,也有生态学的意蕴。
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对微生物采样研究既要有深度也要协调一致,以反映多样性的真实情况。若根据定义判断,稀有物种很容易被错过,但只按一般采样原则行事,则有可能导致误导性的结论。而长尾理论的生态学意蕴同样意义深远:“罕见”并不意味着“不重要”。这些物种数量最多,在相同个体中,个体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即使是具体的某一部分,也会随着个体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稳定性与多样性
一般而言,在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中,其多样化效果更大。这种想法无疑是诱人的。但种类越繁多,可能意味着其冗余性、连通性和吸收扰动也大。对此,部分生态学家认为,更多样化的生态系统也可能更脆弱,它们所具有的复杂性会将一些小扰动放大,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在过去五年中,为了解人体微生物组的动力学原理,联合实验项目做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证明抗生素的滥用已经严重扰乱了人体微生物组群,并造成了附加损害,即不加选择地灭杀非致病性微生物,而让没有机会建立自己领地的病原体在人体内大行其道。最明显的例证便是艰难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因为长期使用抗生素造成了微生物组群难以恢复到原始组分状态,而受到扰动的生态系统形成了新的组合,产生抗药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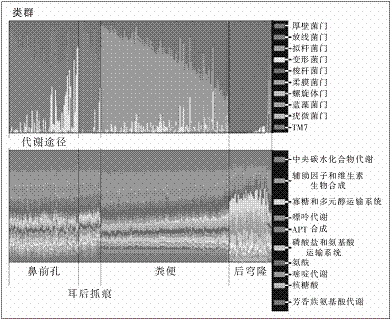
微生物演替的结果显示了生态系统的可预测模式,即后来者替换掉早期的微生物群落,形成新的群落。例如,在1980年5月,当圣海伦火山爆发后,早期的微生物伴随着火山灰被吹散消失殆尽,沉寂在火山灰土层下,在等待后来物种的光顾。
人体微生物组也是如此,尤其在最初的24到36个月期间。我们现在知道,产道能播下新生儿的人体微生物组,而剖腹产降生的婴儿其微生物组更像是母亲皮肤的成分。这些最初的微生物在婴儿肠道内留下了清晰的痕迹,就是这一痕迹,会持续若干月,几年,甚至一生。
基于生物学过程和历史经验,某种程度上婴儿肠道微生物群的变化可预见一些配置方式,其中有很多因素,包括孕妇产前健康状况、饮食(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和接触其他微生物的情况,致使微生物渐变成形。因为肠道微生物组的均匀度和其构成每天都在变化,显然与人体免疫系统的成熟度有关。而微生物组在构成的同时也塑造了宿主,反之,宿主的生物学体系也促进了微生物组的构建。
长尾分布效应
按照生物学的一般规律,有些物种十分多度,但在单个群落中相对稀少。在显示物种多度排名曲线图上,它们往往在数学上表现不错,近似对数正态或呈几何分布。然而,如果坚持将这一多度分布作为微生物组既定的生态法则,恐怕为时过早。
正如前面提到的微生物组尾部排列,即,有时仅仅几个细胞,却能代表数以百计的微生物种类。考虑到微生物组是动态的,尾部上的成员很多可能是短暂的过路客。由于微生物具有快速生长的能力,在适宜的条件下,某些菌种几小时在微生物组内呈爆发性增长也不是件罕见的事。
生态学家早就知道,一个物种对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言,并不总是反映在它的多度上。某些微生物之所以罕见,是因为它对一个群落的稳定性和多样性至关重要。事实上,这样的关键物种一旦遭到删除,则会引发整个生态系统的崩溃。虽然某些研究试图确定一些重点物种,但人类微生物组计划(HMP)却有着不同的选择,认为弄清楚整个生态系统能起到坐实基石的效果。
具体到人体生态系统,某些代谢任务必须在功能微生物组内展开,其物种之间的互换性或许可以解释每个人掌控、协调微生物的差异,或表明没有单一的物种必须始终存在于肠道或身体其他部位,以确保微生物在起作用。
如果我们只关注功能角色而非物种身份的识别,人体内部环境以及微生物之间的差异或会消失――只有当个体向群落提供特定生态服务时才会发生,或向每个构成物种提供代谢产物、营养和原料。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微生物在一个平衡的环境中生长,必须有效去除其他具有潜在毒副作用的代谢物。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根据了解,微生物参与了广泛的水平基因转移工作,尤其在跨越物种界限上,均主动或被动地参与了遗传信息功能模块的交换。让人吃惊地是,这种交易既不遵循种系理念,也不按照祖先遗训行事,在对环境变化产生应答时,无需重新开始,就能让微生物获得功能基因信息。实际上,微生物群落是其信息库演进的创建者和管理者,每个微生物成员可以从中分享。
水平基因转移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因为它既是抗生素耐药性传播的基础,同时也强化了微生物群落应对各种扰动的反应能力,包括宿主健康的变化。现在知道,人体肠道内的微生物宏基因组遗传信息库,可能比在真核细胞中发现的要高出100倍,而且还在不断的进化之中。事实上,人体内的大部分遗传信息并不是真正的“你”。这个信息库,经历了30亿年的演变和数以亿计的实验,已然成为一个连贯性的进化实体,与传统的只关注个体生物为选择目标和进化单元不同,微生物群落中的遗传信息本身就是一个进化过程中的产物。
“广谱”或让位“窄谱”
传统观点认为,生态学与进化时间之间存有明显的差异。比如,当我们在谈及热带雨林或太平洋西北沿岸潮间带时,发现环境变化在个体的一生中会引发不同的生理反应,诸如一些微生物会改变特征表达予以应对,以及由扰动引发的多度反应,直至种群遗传成分的改变。又如,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大了动植物的基因型变化,大多数物种只能通过改变地理分布,以应对环境破坏带来的影响。
表面看,生态学与进化时间的区别看似重要,但在对微生物处理上可能不适用。对很多人而言,如果不是人类微生物区系的成员,增代时间只能以小时或分钟来计。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加之微生物庞大的种群规模,可能混淆了生态学和进化时间之间的界线。
一个人的一生可能包含数百万个微生物后代,个别物种和微生物本身可以在一个宿主内部得到进化,在这样一个无缝环境下,微生物的转录在有利突变的调控中逐渐实现应对。很难想象的是,渐进性变革在我们人类身上得到了演变。
当科学家重新定义生物识别概念时,意识到每个人从早期发育直至死亡,都与他或她的微生物群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交织的证据来自许多方面,包括医学界从来没有想到的诸如牛皮癣、哮喘、结肠炎、肥胖、心血管疾病等,其中都有微生物的影子。就肠道微生物而言,生物学家现在意识到,同卵双胞胎其宿主基因组中的物种构成差异率超过50%以上,高于异卵双胞胎的比例。包括每个人的成长对微生物的依赖是不可或缺的,而衰老问题则变得越来越清晰了。
过去,微生物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疾患的代言词,往好里说,在人体内搭乘了免费的顺风车。现在,微生物的形象逐渐被有趣的细胞肖像替代,即在人体中与真核细胞形成交互的过程所替代。这些新颖的、不再隐形的伙伴正在向人类身份的界线定义发起了挑战。于是,一场革命性的超个体的人类概念正在形成,即每个人的体内聚集有与300万亿个细菌细胞共存的37万亿个真核细胞,真核基因组的2万个蛋白编码基因辅以200万个微生物基因。
可以这样讲,现代医学(概念)需要彻底的修订了。广谱抗生素可能不得不让位于窄谱和靶向治疗法了,许多疾病的根源或将需要考虑微生物群落的状态了――由于微生物群落遭到了破坏,其发病机理则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由于与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针对这些复杂且动态的生态系统,微生物学家和医生将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建立的群落生态学原理。生态学是一个野外试验、实地观察和理论探讨的过程,而上述这些描述为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新落脚点。现在,微生物学家、医生、社会和理论生态学家,可以聚在一起来研究相同的数据了。
这些结果是初步的,但结论是明确的,因为数学和物理靠规则可以得到贯彻,但把控生命过程的生物学规则有所不同:我们人类是规模最大、寿命最长的生物,最终,我们会掌握开启万物之灵的钥匙。
资料来源 American Scientist
责任编辑 则 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