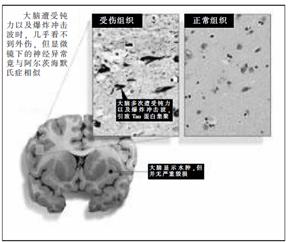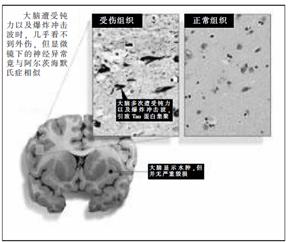战时的爆炸可能会导致流行性的脑部损伤,这给科学家们带来巨大的挑战。

对于波特来说,他在阿富汗所经受到的炸弹冲击波最后演变成了一种音乐:引爆C4塑胶炸药和其他战争中所使用的爆炸物就像是超高音――痛苦,然而瞬间即逝。但是阿富汗叛军酷爱使用的用化肥制成的炸弹所产生的冲击波就像是听众站在摇滚演唱会的音箱旁:沉闷的低音砰击声不一定会直接伤害到听众,但会像波浪一样在他的体内回响,并在此后很长时间内挥之不去。
波特(要求不要使用真实姓名)就是这个情况。他作为一名战术顾问在美军驻阿富汗的一个炸弹处理部队工作了4个月。在此期间,他有18次以上距离引爆简易爆炸装置(IED)的现场不足50米。在他离开阿富汗之前,开始出现睡眠困难、头痛和恶心等症状。还出现健忘的现象,并在他回到家里之后变得愈发严重。波特时常会发现自己身处家中某个房间,但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在那里。一次,他对他的妻子说他们应该去镇上新开的一家饭店尝尝鲜,而他的妻子回答,他们前几天才和几位朋友光顾过那里。
早在两年前,这些病症会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即可能由于在战斗期间长期处于压力之中所导致的心理病症。但仍在休病假的波特认为低音声波是罪魁祸首。他深信使人全身发抖的冲击波对他的脑部造成了一些损害。许多医生、医学研究人员和军官们开始相信他所言非虚。
创伤性脑损伤
目前已知的由叛乱分子制造的IED所造成的人员伤亡数字触目惊心。在针对阿富汗和随后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后的10年里,由于IED导致美军和盟军阵亡人数超过3000,伤员人数逾10倍。但更多的作战部队人员经受过多种冲击波的冲击,身体并未受到显性伤害。与波特的情况类似,他们所反映的一系列病症包括失眠、注意力无法集中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持续的震荡导致他们的大脑受到隐性的亚细胞水平的创伤性脑损伤(TBI),不仅造成身体日常功能紊乱,而且增加了在长时间内发展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的可能性。
哈佛大学的一名生物医学工程师凯文·凯特·帕克(Kevin Kit Parker)一直从事TBI研究。他说,很多大约30岁左右的人有过受十几次爆炸物冲击的经历,这些人患上老年性痴呆症或帕金森综合症的风险在大大增加。
根据华盛顿特区国防部老兵脑部损伤中心的数据,受到这种隐蔽性TBI影响的部队人员已经超过20万。兰德公司是位于加州圣塔摩尼卡的一家非营利性研究机构,他们的调查表明这一数字可能高达32万。五角大楼和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分别负责现役和退役军人的保健工作,他们对于这些病症可能会发展成流行性伤残和痴呆症而深表担忧。这一病症对于研究人员来说也具有非常大的挑战。
美国国家神经系统疾病和中风研究学院(位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副院长沃特·克洛谢茨(Walter Koroshetz)解释道,现在还没有人可以完全明白冲击波对于大脑造成怎样的损害。长期以来,借助于从职业体育运动所获取到的大量数据,人们都知道头部反复受到损害会引发慢性的退化性疾病。更糟糕的是,不仅仅是减轻病症,要找到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则需要数年之久。仅在过去30年中进行的50多次测试中,使用的合成物和干扰素超过了20种。在这一领域,大家只是浅尝辄止,却没有取得过实质性的进展。
奋起直追
让人欣慰的是,五角大楼终于开始把理解、诊断和治疗这些病症摆在首要、优先的位置。但正如国防部的一些官员所承认得那样,由于多年来这一问题并没有得到重视,他们正在奋起直追。
参谋联席会主席麦克·马伦上将(Admiral Michael Mullen)的医学顾问,陆军军医克里斯汀·马其顿上校(Colonel Christian Macedonia)说:“医疗体系对此长期以来采取的是漠视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陆军的一种文化。因为大部分被爆炸冲击波震得头晕目眩的士兵从表面上看恢复得很快。大家对此的态度就是,“嗨,身体晃一晃就没事了。”
他接着说道,病症开始显现的时候,患有TBI的士兵经常被误诊为具有类似病症的PTSD。从伊拉克和阿富汗回来的老兵经常也受到到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并进而发展成以上两种病症。
但是马其顿认为最重要的是人们不愿意承认隐蔽性TBI的存在是受到“海湾战争幽灵”――海湾战争综合症的影响。围绕着1991年海湾战争服役人员所描述的普遍存在的这一病症,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科学争论。人们反复进行研究,仍然无法确定海湾战争综合症的主要病因。所以,当有人开始提出TBI病症――又一个被普遍提出但又无法与某一病因联系在一起的症状,这是已经深深受挫的军医管理阶层所不愿意听到的。
在军队高级首领察觉到他们收到的正式报告与他们探访伤员所了解到的情况不符之前,这种态度并无任何变化。海军陆战队司令詹姆斯·阿莫斯上将(General James Amos)2009年到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市里德医院巡访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一位病人。这位病人很费力地说:“将军,我有一张你和我在伊拉克的合影。”
阿莫斯的确也有这张照片。照片是两年前刚照的,当时他与一群刚从车辆底部遭到IED直接引爆袭击中幸免于难的海军陆战队队员拍了这张照片。幸好车辆的装甲非常先进,所有的人看起来毫发未损。但这位年轻人――一位炸弹处理专家,直接返回继续工作,很快又经受过几次炸弹冲击波。他的身体情况迅速恶化,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由于无法得到军队医疗机构对其患有TBI的认可,他以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为由被收入里德医院。
阿莫斯把那次见面描述为具有开创性的一刻。他回忆到,他当时的反应是,“TBI是确实存在的,我们必须一改过去对此漠视的做法,必须有所作为。”
马伦得到与此基本相同的结论。考虑到对脑部损伤问题并不完全了解,他请马其顿帮忙组织一些具有战斗经验的研究人员和医务人员(称为“灰队”)到战场上了解TBI的真实情况。
马其顿介绍:灰队(名字取义于大脑的灰物质)在2009年第一次来到了阿富汗,并迅速得出结论认为马伦的疑问是非常有根据的。正式报告里说90%脑部受到震荡的士兵根据“士兵急性震荡评估13条注意事项(MACE)”接受了病情评估。而当灰队来到阿富汗,他们发现绝大部分的医务人员――包括大型军队医院和边远哨所,甚至不知道MACE是怎么回事。马其顿说,尽管他们具备所有的培训材料,军医们无法说出实质性的内容;也没有人对伤员进行任何筛选。
与灰队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一项得到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和海军研究中心资助的研究,该研究首次将重点放在了解冲击波是如何对大脑产生影响。冲击波可以造成由在体育比赛常见的钝力伤而导致的各种伤害。研究的焦点在爆破手――专门使用爆炸物冲进建筑物的陆战队员。研究所形成的第一份文件正在进行审核,但研究人员称他们已经找到长期暴露于低级别冲击波中的教官神经功能受到损害的证据。
2010年6月21日,根据对爆破手的研究成果,五角大楼宣布了首批针对鉴别和治疗患有TBI人员的政策,其中包括在军队内全面推行对士兵进行强制性检查的条件,其中有一项规定是:凡是在距离冲击波50米范围以内的人员均需进行脑部损伤检查。
研究逐步展开
五角大楼也开始对其长期忽视对大脑损伤的研究采取弥补措施。1999年至2005年期间,国防部的“国会直接指导医疗研究计划”作为医疗研究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没有为TBI或PTSD的研究拨过一分钱的经费。在2006财政年度,拨给了PTSD研究的仅有370万美金,而TBI根本就没有被列为研究课题。然而,2007年面对发生在战场上的大脑损伤的大量报告,使得国会同意拨款1.5亿美金用于TBI的研究,同时再拨款1.5亿美金用于PTSD的研究工作。

美国军队实验在对士兵进行服役前的基准测试中使用电子脑电图仪
充足的资金为像帕克这样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帕克是为数不多在进行TBI研究的医学研究人员中的一员,又具有作战经验。他的研究重点曾经是心脏细胞力学。但是在2002年,他以步兵军官的身份在阿富汗服役(这是他两次服兵役经历中的第一次)。也就是在那里,他开始注意到TBI对他的战友所造成的影响。那时,炸弹相对较小,比较简单――比如说,也就是炮弹与车库门遥控器配合使用。但他在2009年第二次服兵役时,士兵们遭遇到的重达200公斤的化肥炸弹,足以把没有装甲的车辆炸得粉碎。他半开玩笑地说,一旦有人想用IED送他去见上帝的话,“我想我还是赶紧改行去做神经系统科学家吧。”
事实上,帕克首次正式参与大脑损伤研究开始于2005年,那一年,他加入了DARPA有关这个课题的研讨会。在那里,他了解到研究面临的挑战之一是了解爆炸冲击波会对大脑产生何种影响。由于本身具有细胞动力学的专业背景,帕克很快开始想到了整合蛋白――调节细胞核周围组织附着力的受体。爆炸冲击波所造成的损害是否足以破坏蛋白质的功能呢?
帕克现在已经是“灰队”的成员,他说:“人们一开始对这一设想的反应很冷淡。在学术界没有既研究神经系统学,又了解细胞动力学的人。这就好比,你习惯于阅读英文,而我却递给你一份中文文件,那样会有些困难。”不过从DARPA得到的一笔拨款使得帕克和他的小组可以进行一次体外模拟实验,从而对他的构想进行验证。当年7月,他的小组发表了一份报告,表明这个构想是完全正确的:由冲击波引发的脑部损伤引发了细胞链反应,中断了整合蛋白的信号发出,破坏了脑部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不断增加的资金保证了研究,通过血液检测来诊断隐蔽性TBI方面也取得了进展。目前,临床医师只能够通过认知功能缺损测试来判断脑部是否受损。这意味着,因为一些症状与其他功能紊乱病症有重叠,大脑损伤研究人员无法最终确定他们所取得的测量值――病人也可能无法得到最适合的治疗。现在,经过对各种在脑部受过损伤后在血流中增高的蛋白质的研究,得到陆军资助的研究人员对其中特别有可能的两种进行了小规模测试,即第二期临床试验。这两种蛋白质被称为泛素C-级水解酶(UCH-L1)和胶质原纤维酸性蛋白(GFAP),而且将很快会进行大规模测试,即第三阶段试验。
贝尼特·奥马鲁(Bennet Omalu)是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法医病理学家、加州圣华金河郡主任法医,专门为五角大楼工作。他已经开始对退伍老兵的大脑进行慢性创伤性脑部疾病的研究。这种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首个病例发现于从事有身体接触性体育项目的职业运动员,病因据信是由于脑部受到多次震荡。11月,奥马鲁计划发表可能是首个病例研究报告,揭示一位患有隐蔽性TBI退伍老兵的慢性创伤性脑部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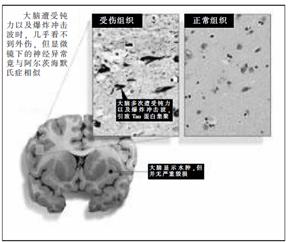
脑部创伤
奥马鲁在2005年根据他从一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的解剖样本中得到的研究,发表了首个慢性创伤性脑部疾病的病例。他对此解释道:那个年轻的退伍老兵在伊拉克的两次军事行动中受到过多次爆炸冲击震荡。回到家后,他出现记忆受损,情绪紊乱和自控力下降的问题。接着,在27岁那年,他自杀了。奥马鲁说,他在获得其家属的许可后,对其大脑进行了检验,发现了有慢性创伤性脑部疾病(CTE)的病变――与老年性痴呆和其他痴呆症有关系的蛋白聚集量超出正常水平(见“脑部创伤”)。
期待信息开放
很少有脑部创伤医疗研究人员能够轻松地与五角大楼打交道。由于其独有的官僚主义,加上出于对国家安全考虑的特点,使得那些对研究人员非常有用的许多数据和脑组织样本都无法接触到。比如说,五角大楼的联合战区外伤注册――汇集了所有与军队创伤有关的数据,是高度机密的,唯恐敌人利用这些信息提高他们击伤美国士兵的能力。“公开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资料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非常、非常困难。”马里兰州迪特里克港美国陆军医疗研究和器材司令部负责人詹姆斯·吉尔曼中将(Major General James Gilman)说。
现在有了一些变化的迹象。由位于贝塞斯达的NIH和军队卫生服务大学共同发起的一项计划最近招入一名神经病理学家,专门研究士兵遗体的脑部组织――尽管不保证一定可以接触到脑组织。五角大楼和NIH在8月份也达成一致,共同开发TBI数据库,与用于老年性痴呆症、孤独症和癌症研究的数据库类似。这个构想的目的是要将研究工作中的数据搜集标准化,更易于研究人员对研究结果进行比较。
另外,这些比较应可以帮助调查人员更加清楚地了解TBI的治疗疗效。克洛谢茨说:“他们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帮助。在已经取得的关于了解病因和隐蔽性TBI形成方面的进展中,治疗手段还显得很难把握。在过去的20年中进行了数十次的临床试验,从抗氧化物到高压氧所有的手段都行了研究,但没有人可以提出其中的区别。就病人的疗效而言,尚无证据可以表明某单一手段具有效果。”
与三年前TBI几乎被忽视的状况相比,五角大楼的工作进展明显。从1月份开始,部队必须强制性地追踪震荡损伤的情况;士兵在服役之前要接受认知性测试,用作他们以后如果受到震荡损伤的比较基准。脑波测量的试验也在进行之中。根据新的情况汇报要求,部队正在建立最大的TBI数据库。
问题是,如何将这股势头保持下去。鉴于美国的预算一直遭人诟病,事实证明这可能会比较困难,经过2007年的最初增长,TBI的研究资金水平已经大幅下降。在2011年财政年度,国会给五角大楼脑部损伤研究的专门拨款预计仅为4500万美元。迪特里克港陆军战斗伤病护理研究计划主任达拉斯·海克上校(Colonel Dallas Hack)质问道:“对谁有利?谁给予支持?国家付出的努力体现在哪里?”
陆军卫生局副局长罗伯特·托马斯准将(Brigadier General Robert Thomas)希望军队现在的参与能够对脑部损伤的研究和治疗起到作用,就像他们过去在黄热病、创伤治疗和紧急运送就医方面所作的努力一样。他说:“不管怎样,不断争取是医疗创新的最大催化剂。”
但与此同时,波特和成千上万的脑部疾病患者只能希望研究所取得的进展能够及时地帮助到他们。波特曾经雄心勃勃,可以一心多用,而他现在连完成基本的任务都有困难。最近,他可以在房子周围走一走,甚至可以做到去商店购物――只要他事先列出购物清单或使用其他的提醒方式。“但我永远都不是以前的我了。”波特说。
资料来源 Nature
责任编辑 彦 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