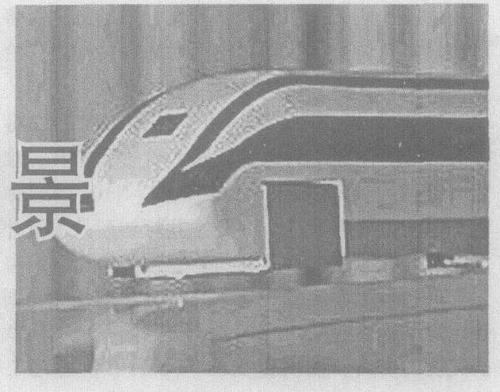
从我开始能够阅读有关科学内容书籍的时候起,我就希望将来可以成为一名科学家。由于对数学方面有着特殊的爱好,使我最终转向了理论物理学的学习。研究金属电子的性质听起来有些平常,但这是真事。事实上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对量子理论知识有着很高的要求,因此我始终将这些原理当作从未被发现过那样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在这方面获得更为深入的理解。而我坚信物理学家们一直以来所从事的研究,都是在尝试揭示出一套包罗万象的理论。
由科学所描绘的世界图像虽然令人着迷,但是否都绝对真实?事实上,我一直对哲学感兴趣:20世纪50年代末我便开始阅读有关科学知识方面的论述。我所看到的着实令人不安,少有例外的是,科学研究似乎被认为是由丧失个性的鲁宾逊 · 克鲁索所苦苦思索和开展的一系列逻辑学练习。根据我个人的经验,科学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情,人以及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在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我曾经作为作者、编辑、裁判参与过一个十分复杂的同行互评活动。这确实也是构成解开科学真相的秘诀的最主要成分。所以我开始撰写文章和著书来解释当时还较为新颖的一个概念:即科学是社会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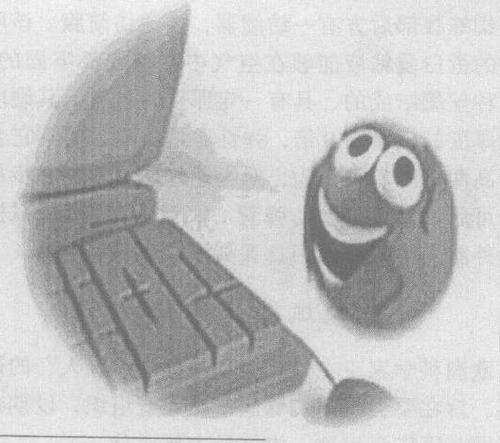
此后,科研的社会学发展十分迅速。社会因素在导致和形成科学研究及其成果方面所起到了的显而易见的作用已得到了广泛的认同。然而这种热衷于从社会学上对我所说的“公众知识”进行解释的方法表现的往往有些过头。在我的《真科学:它是什么,它指什么》一书中,我尝试了重建发现与构建之间、个体认知与团体模式之间、富于想象的洞察力与冷静的怀疑论之间、社会性实践与特殊变量之间、进化的不确定性与可靠的发展进程之间的辩证平衡关系。而这些相辅相成的事物全都是构成影响知识生产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这片令人困惑的纯理论家认识论大森林中穿行很久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多元化的大草原中,在这里有无数的品种繁茂地共生在一起。可是,到底是什么将科学结合在一起的呢?看看所有的那些学科,每个似乎都在各行其是。可是我年轻时所梦想的科学怎会成一个一元化的普遍一致的领域呢?回顾这些梦想,我发现它们正沿着一条不同的河在流动,一条真正的思想和行动之河。
说科学具有社会性是从一般的社会秩序角度来体现它的。结果,我就像一个STS公司的非正式演员赶场那样,将我的大部分生涯花费在官方学术界之外的那些受到科学、技术、社会学互相作用影响下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神学等领域。所以有人将科学定义为一个联系紧密的多维社会研究院,尽管它的活动领域要比我所在的学院研究单位宽广得多。
然而到了80年代末,我开始意识到这个社会研究院正经历着一场彻底的、大规模的并且是无法逆转的改变。这场以二号知识生产模型为代表的向“后学院科学"的转变,最初似乎是由于无法抗拒的社会需求、仪器的完善、应用科学的进步以及财政预算的紧缩等原因所造成的。但是现在,我更倾向于将这次转变看成是发生在当今世界更为先进的部门之间的,一次普遍的信息全球化过程的集中反映。所以,例如跨国科学研究网络可以与连接其他全球性机构如跨国公司的电子信息流共同存在,而这些公司本身,正变得越来越主导着科学研究的计划日程。
可是,正像一些进步的政治思想家现在所指出的那样,全球融合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整齐划一。不同的秩序仍然可以和平共处,他们可以通过宽带信息网和贸易伙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仍保持着各自不同的文化特色和独立性。换言之,科学领域的多元化与联合统一的世界经济政治多元化一样,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在对这些有深入的了解之后,我便可以自由地对许多科学领域之间,典型的例如在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类科学之间已经存在的交叉领域进行详尽的观察了。我的推论是,这些科学领域之间的分水岭并不仅仅是在社会因素影响下所形成的,从进化的角度来讲,它们代表着宇宙中自然产生的不同自然法则之间的真实差异。因此,希望包含我们对所有特殊事物的理解的超弦论(包罗万象的理论T. O. E)实在是一种幻想:在自然界的每个领域,不论是夸克、湿地还是半官方机构,可靠的科学研究都同样重要,也都同样值得探索。
即使是认识论也只能走向细化。一种概括性的观点是无法揭示出科学的全部本质的。因为这只有通过在各个学科领域及相关的技术领域中进行辛勤艰苦的劳动才能获得。我们必须学会尊重每种具体的知识对其自身领域的探索,而不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更为概括的理论中的特例。从事应用科学的研究人员关于这一点有着非常充分的理解,他们很快就注意到概括性的理论知识在解决许多特殊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局限性。实际上,以二号研究模型为代表的后学院式科学一直将目光高度集中在卫生保健、制造业、行政管理等应用领域中出现的问题。这些细部问题又促使更多的概括性模式得以充分发展,有时甚至很多模式被返回到上层重新进行理论研究。而在实际问题当中通常也会涉及到许多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均需正视的一些因素和概念。例如全球变化问题当中出现的几乎每个细部问题,实际上都是涉及到了物理、生物、社会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而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则必须是在每个这样的知识领域里都存在相对应的概念含意。
就这样,在对科学的本质思考了近50年后,我最后决定打出“科学是社会性的"这个口号。科学并不就是社会的动力因数,而社会却是科学的一个动力因子。这在社会学界早就成为了公认的事实。技术变革并非只是科学进步的结果,而科学进步却恰恰离不开技术的变革。但是全球时代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革新与社会和经济变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直接。我们现在拥有在局域范围内明确运行着的交互式综合网络,而其开放程度比在一般性社会理论基础运行机制所预想的情形要好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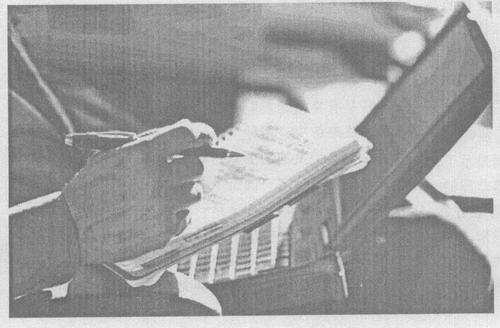
几年前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国际性、多学科的研究小组,并且出过一本名为《将技术革新视为进化过程》的书。我们发现物质产品、设计理念、经济组织并非是独立发展的。可是仅仅将它们看作是一种平行、独立的达尔文式的变异与选择过程又是完全不够的。这些过程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它们的结果甚至可以被描述成为联合式进化,并且其中还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生态学特征。
但是我们仍然有可能会失败,而这样的事实我也不得不接受。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将生物学上的比喻用来解释这样一个人类意志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系统的行为呢?
而在自然生命中有意义的逻辑性,在一个记忆与想象的世界里是否同样起着支配作用呢?或许我应该去了解一些全局性的东西,而不是在这儿跟这些“细部”困难纠缠。
__________________
*约翰·齐曼(Jodm Ziman)世界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布里斯托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学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