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毓麟教授获奖留影
作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出色成果,卞毓麟教授的《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获得了201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作品获得国家科技奖非常少见。本刊近日对卞毓麟进行了专访,期望通过本文,公众可以对一部科普佳作的产生过程有所了解,也对一位科普专家的风采有所了解。
创作的缘起:长久的积累与偶然的契机
与一般科研项目大约相同,卞毓麟创作《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以下简称《追星》)的缘起,既有偶然性因素也有必然性因素。说其偶然,是因为他曾经的同事匡志强和洪星范向其约稿。而言其必然,则是他早就想写一本有份量的科学文化类型的读物,只是一直未有时间动笔,匡、洪二位的约稿恰好促进了他原本想法的落实。
卞毓麟从事科普创作30余年,主持或参与编著、翻译的科普图书有百余种,发表的科普文章逾500篇。早在1996年的首届全国科普工作会议上,他就被授予了“全国先进科普工作者”的称号。关于天文学的科普图书,如《星星离我们多远》、《挑战火星》、《宇宙风采》、《群星灿烂》等,是他30多年来的主要创作内容。不过,卞毓麟说,他虽然写过不少科普书,但创作像《追星》这样科学文化色彩浓郁的长篇作品却还是第一次。
创作这样一部作品的愿望,或许可以追溯到卞毓麟从小就受到的科学文化影响。少年时代的他最喜欢伊林;而30来岁开始,他又迷上了阿西莫夫。房龙、伽莫夫、萨根、马丁·加德纳、保罗·戴维斯、斯蒂芬·霍金等等,也都是卞毓麟心仪的大家。而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国际上兼具科学情结与人文关怀的科普大家。
科普作品能够“创造显著社会效益”,关键在于能否让尽可能多的读者尽可能容易地获取尽可能多的科学养分。与往往以青少年或者天文爱好者为读者对象的天文科普图书不同的是,《追星》一开始设定的读者对象,就是一般的社会公众――大凡乐意浏览《新民晚报》、《南方周末》等的人士,都可望是它的读者。也可以宽泛地说,这本书的对象是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广义的社会公众。对于创作《追星》的目的,卞毓麟说,我们非常希望有更多的读者通过这次愉快的追星之旅,体会到科学非但并不神秘,而且还相当有趣,它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边。当然,科学爱好者们也会从本书中获得充分的乐趣和收益。这些,就是科普作品所要追求的“社会效益”吧。
写作的内容:人类“追星”的历程
《追星》所展现的内容,是人类对星空认识的历程。在《追星》全书的开始,是一篇“小引”,其中提到了书名“追星”一词的来历:“就这样,人类成了天生的‘追星族’――追那天上的星。其实,天上的星星也是千差万别的。它们的明暗、颜色――有时甚至外形――都各不相同。”“小引”中继续说道,“对于上古的初民来说,还有什么比天空中突然出现‘一把闪闪发光的大扫帚’更令人惊骇的呢?”由此引入早期天文学中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如何解释彗星。
在“小引”引入彗星之后,全书分五篇,依次为“不速之客天外来”、“传承古人的智慧”、“注视宇宙的巨眼”、“远离太阳的地方”和“未来家园的憧憬”,步步深入地展现了人类“追星”的历程。而在以往的天文科普读物中,同样的话题,往往会采用“谈彗星”、“宇宙观的发展”、“天文望远镜的历史”、“太阳系的新发现”、“空间时代和火星探测”之类很“天文”的标题。
事实上,在每一个议题中,古人的理解,按照今天的分类,都既有天文的、也有艺术的甚至宗教的。有一些媒体曾经在采访卞毓麟时问:“这本书讲天文,却时而谈到历史,时而谈到艺术,时而又谈到宗教。您是怎么把这么多东西捏到一块儿的?”而科学界也有老友打趣卞毓麟说:“你居然把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全都弄到了一起,好本事!”卞毓麟却说:“并不是我把它们捏到一块或者弄到一起,而是它们本来就是一个整体,我只是努力地反映事情的本来面貌而已。”
古人本来就没有条块严格分割的“天文学”,“追星”的过程自然就不仅仅是现代的天文学发展过程。卞毓麟说,《追星》力求从文化的高度,将天文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内容熔于一炉,以利开阔读者的视野,多方位地领略科学之美。因此,它不是简单地罗列有关的天文知识,而是把描述对象从“星”本身扩展到人类如何“追星”,将几千年来人类对宇宙的不断探索和思考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融为一体,并贯穿始终。如此,与其说《追星》是一本“天文”书,不如说是一本“人文”书。
“追星”是地球上人类的共同爱好,在“地球村”时代之前,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天文学。虽然“同一片天空”但却有着“不同的天文学”。因此《追星》很注重中西文化的观照与比较。就宏观的历史时期而言,欧洲古代马其顿王国瓦解后的“希腊化”时代与中国西汉后期的观照,中国清代康熙朝与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联系等,《追星》中各有言简意赅的叙说。就微观的人物事件而言,书中既介绍了牛顿、哈雷、赫歇尔等诸多国外科学家的成就以及与之相关的人文素材,也刻画了中国著名天文学家郭守敬、张钰哲、李珩等人的科学贡献和社会生活背景,还引证了屈原《九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晋书·天文志》等中国传统文献。如此中西融合的讨论,在当前的天文科普图书中并不多见。
科普图书不仅要介绍已定型的科学基本知识,而且要及时反映科学的最新进展。在《追星》的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天文学和航天技术领域的新成就层出不穷,书中必须择其精要及时反映。为此,卞毓麟尽了很大努力将新近的知识补入。例如2006年8月国际天文学联合会通过决议,将原先称为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的冥王星重新分类、归入“矮行星”之列,《追星》及时补述,成为了中国率先反映这一重大科学事件的科普图书之一。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资深研究员李竞教授因此曾评价《追星》说:“你(卞毓麟)搜集的资料很新,很及时、到位。很好。”
技巧的运用:历史感与画面感

1988年8月13日卞毓麟在阿西莫夫家中做客,与阿西莫夫夫妇合影
卞毓麟所喜欢的美国科普泰斗阿西莫夫,在其百万言巨著《最新科学指南》的序言中写道:“没有人认为,要欣赏莎士比亚,自己必须能够写一部伟大的作品;要欣赏贝多芬的交响乐,自己必须能够作一部同等的交响曲。同样地,要欣赏或享受科学的成果,也不一定要具备科学创造的能力。”可是,科学之于大众深不可测的外表,总是让人没有办法像接触交响乐那样去接触。卞毓麟说他创作《追星》,就是希望能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沟通方面做一点新的尝试。
卞毓麟认为,另一位他所喜欢的科普作家伊林的作品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总是将人类今天掌握的科学知识融于科学认识和科学实践的历史过程之中。 世上许多的科普经典,通常也都具有相当鲜明的历史感,能够钩玄提要地回顾人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本来面目。
在科普作品和科学人文作品中多多地谈论历史,有助于人们高屋建瓴地领悟科学的作用。伽莫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不只是“达到改善人类生产条件的实际目的”,科学“当然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但这个目的是次要的,难道你认为搞音乐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吹号叫士兵早上起床,按时吃饭,或者催促他们去冲锋?” 伽莫夫认为,科学的来源就是人类追求对于自然和自身的理解。
除了历史感,卞毓麟写作《追星》时对自己提出的另一希望是:即使全书连一幅插图也没有,读者也能随时在正文中读出图来。也就是说,《追星》的画面感要直接体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随时都能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在某种程度上,他希望《追星》能够宛如一个电影文学脚本,本身并没有图,但是只需再往前跨出一步,就可以转化为分镜头脚本并拍摄成影片。事实上,读过《追星》的人都知道,他完全达到了这一目标。
“火神星”个案:科学的、人文的、历史的、画面的、中国的、西方的
在1846年海王星被发现之后,有8颗大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环绕太阳运行,逐渐变得家喻户晓。但是,人们曾无数次地发问:太阳系中难道就没有更多的大行星吗?为了解答这一问题,人们做了大量的计算和观测工作,其中除了最终发现冥王星外,还有所谓发现“火神星”的误会一场。这段故事,在《追星》中有着非常有趣的说明。
卞毓麟就此问题,首先解释了“进动”的概念。“如果只有唯一的一颗行星环绕太阳公转,那么它的轨道就会是一个严格的椭圆。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行星都在绕着太阳转,它们彼此间的引力相互作用错综复杂,致使每颗行星的公转轨道都不再是一个严格的椭圆。事实上,行星轨道的近日点总是在不断地缓缓前移――这称为行星轨道近日点的‘进动’。”如此解释,对于具备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而言,是不难理解的。
接着,卞毓麟对由于“进动”而产生的现象进行了说明。“在各大行星中,水星离太阳最近,而且质量又小,所以其轨道近日点的进动最为显著。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可以准确地推算出水星近日点进动的数值。然而,令人费解的是,推算得出的结果却比天文观测得出的实际数值小。”这里牵涉到的知识,属于高中物理教科书的范畴。
从这一问题出发,卞毓麟解释了19世纪40年代的西方科学家是如何解答的。他提到,“阿拉戈就在巴黎告诉勒威耶,应该仔细分析水星的运动。后来勒威耶对此所作的精密计算表明,即使考虑到所有行星的摄动,水星近日点的进动量也比牛顿理论所能解释的更大。他深受发现海王星的鼓舞,于1859年宣称上述差异可以解释为在水星轨道以内存在着一颗未知行星,正是它的引力造成了水星运动的异常。”而当时发生的另一历史事件,卞毓麟也给以了说明,“恰好在这一年的3月,有一位法国乡村医生、天文爱好者勒卡尔博宣称观测到有一个小黑点从日面上经过,人们认为这正是那颗‘水内行星’凌日的表现。”这样的说明,自然会让读者产生很清晰的画面感。
而针对这一“水内行星”的“发现”,勒威耶也特别地进行了命名――可以算作是人文的内容了。“勒威耶将尚在想象中的水内行星命名为‘武尔坎’(Vulcan)。该词由意大利语的Vulcano或Volcano简化而来,这两个名词都源自古罗马神话中火神的名字武尔坎努斯(Vulcanus)。在希腊神话中,与武尔坎努斯相当的是火神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那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将火神看作一位了不起的锻工――因为必须用火冶炼矿物才能获得金属,然后再使金属熔化或软化并铸造成型。在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赫淮斯托斯的形象正是如此。”
从西方用神名命名星名出发,卞毓麟又转入了中国古代的星名命名。他举例说,正如汉语中将行星“纳普丘”定名为“海王星”、“普鲁托”定名为“冥王星”那样,“武尔坎”在汉语中常被称为“火神星”。有趣的是,我国的前辈天文学家们早先还曾赋予它一个更富于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名称:祝融星。传说中“祝融”乃是楚国君主的祖先,名重黎,是上古时代帝喾高辛氏的“火正”,即掌火官,以光明四海而被称为祝融。祝融是中国的火神,所以后世才称火灾为“祝融之灾”。当然这一切,都源自一个想象中的“发现”。
最终,“水内行星”在物理学中得到了解释。卞毓麟对最后的结果如是说,“20世纪初,‘水星轨道近日点的反常进动’依然是漂浮在牛顿力学体系上空的一朵乌云,它确实暴露了万有引力定律还有缺陷。直到1916年,爱因斯坦建立了广义相对论,才相当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这一番的历史梳理中,卞毓麟像是拉家常那样,把人类探索水内行星的故事讲解得栩栩如生,一点也看不到冷冰冰的科学的影子。这样的例子,在《追星》一书中,比比皆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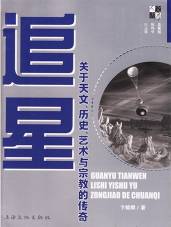
《追星》封面
写在最后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授予在应用推广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完成重大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其涵盖的具体项目包括“在实施社会公益项目中,长期从事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经过实践检验,创造显著社会效益的”。而在 自2009年2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令(第13号)”中,又将“社会公益项目”,具体定义为了“在标准、计量、科技信息、科技档案、科学技术普及等科学技术基础性工作和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自然资源调查和合理利用、自然灾害监测预报和防治等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及其应用推广”。
近年来,科普作品正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科技奖评委们的青睐。而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是科普作品目前所获得的最高奖项。
在《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一书的封底上,有着这样的一段话:“太阳早已落山,大地一片寂静。这是一个无月的晴夜,远处,近处,没有一丝灯光――那时根本就没有灯,没有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灯。在漆黑的天幕上,群星璀璨。星星为什么如此明亮,为什么高悬天际,为什么不会熄灭,为什么不会落下……星星必定从一开始就强烈地吸引了早期人类的注意力,引起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天长日久,斗转星移,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渐渐发展成了一门科学,它就是研究天体运动、探索宇宙奥秘的天文学。”如果硬要说的话,这应当算是人类有关“追星”的科研历程的说明。
而在这本《追星》的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卞毓麟教授,从小时候对伊林的喜爱,到中年起对阿西莫夫的心仪;从他对天文学前沿的跟踪,到对科普作品的持续创作。一点一滴的积累,为他最终写出《追星》这样里程碑意义的科普作品,打下了一段段坚实的基础。通过这本书,卞毓麟教授或移步换景、或一镜到底,带领读者参观了人类历史上“追星”历程中的一个个重要科研成果,一次次关键思想实验。如此的科普创作历程,虽然不像一般科研项目那样,需要理论假设,需要实验判断,但却需要消化科学知识,需要谋篇造句遣词。这样的工作,不是和成功的科研项目一样,拥有动人的风采吗?